初识张秋
文 / 赵勇豪
文章节选自《聊城风物记——聊城地域代表性文化符码的社会审视》,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勇豪著。
在我关于阳谷的板块划分里,张秋是“东阳谷”,是运河上的阳谷,也是富庶的阳谷。运河流经阳谷的张秋、阿城、七级三个乡镇,古称“运河三镇”,这三个镇是整个阳谷县历史文化的重要源地和承载体,也是阳谷的骄傲。
聊城去阳谷,走东线,出凤凰工业园,经东昌府于集镇,过阳谷七级和阿城,就看到了景阳冈。出聊城不久,便看到了周店的指示牌,那里有著名的周店闸。不觉间,我们一行路线倒似行船沿运河南下,经周店,过七级、阿城,到张秋。
这次张秋行我们约定去那里吃早饭,因为很早就听说过张秋街上还有老铺炸香油馃子。提起香油馃子,凡老饕,估计内心肯定有东西被扯动,那便是记忆最深处的温暖与幸福了。很多年轻人认为香油馃子就是油条,其实不然。香油馃子完全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油条和八批儿,虽然从大类上也完全可以把它们笼统归为一族,但倘若从形制和符号意义上说,那就差太大了。
凡面粉膨发,热油炸制,勤劳的中国人历来擅长,且有无穷的智慧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意。稀松平常的日子里拿最平凡不过的东西创生出“千姿百态”,令程式化的生活有起伏、有意义,是初心,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必须讴歌。中国传统的油炸类食品也是这样,你看,炸薄面团叫油炸饼;面团揉扯成长方布袋形灌入蛋液再炸叫炸荷包,好多地方形象地称“炸蛤蟆”,那是因为膨化面团遇热鼓胀起来似青蛙;面团来回扯成很细的丝条下油锅那叫馓子;只有宽窄厚薄适中的扯条下油锅的才是油条;而香油馃子则是连带双条,如果继续翻倍地改刀,就弄成了八批儿,口感彻底改变。
行至南街,在王姓老者的摊位前坐下,对着一碗颇有卖相的甜沫、焦黄烫手的吊炉烧饼和刚出锅的“炸蛤蟆”,我不再纠结因时令错过的香油馃子,开始全神贯注于眼前的美味,不闻言语声,只听唇齿相击。“炸蛤蟆”可谓集中了基层老百姓对美好生活里食物的主要向往。虽然没肉,但油足,够香;好面,好油,还有鸡蛋。蛋液严实地裹在油面里下了锅,瞬间凝固成型,软嫩异常而又不至于诳口,与外面的焦酥配合,舌齿至极舒服,口感绝佳,再约来甜沫灌缝,极谐。甜沫来自小米面,兑和新收的玉米面,大大的耐性慢慢地熬,再添加豆类、粉条、菠菜、花生米等段儿末儿,整体以咸香涤荡隔夜亏空的口腔和胃腹,殷实而热烈,身体就此被唤醒,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去了张秋街上的关帝庙,关帝庙现已修葺一新,且有专人打理。这座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建筑物是张秋历史上经济繁荣的重要物证,时由山陕商人会同山东本地的商人联合修建。关帝庙虽然体量不大,但格局中正巧纳。后正殿为三座大殿,中间是关公,东面龙王殿,西面财神殿,关帝庙的两侧偏房还供奉着元始天君和紫薇星君。大殿前面是一个戏楼子,再前面是庙门,嵌入石匾上题书“乾坤正气”,字饱满刚劲,据说是南京的一个道台所题。张秋关帝庙的结构令人不禁想起东昌府古运河旁的山陕会馆(其实也是关帝庙)。商人希望国泰民安,生意才好做,常年行走水道,左拜龙王爷,右供财神爷,中得关老爷护佑,既有心理上的精神大能量,又有行动上忠义勇武诚信的正能量,于家、于国自是尊荣,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纵观近三千年历史,真正改变张秋命运的是元代的寿张县尹韩仲辉。1286年,他向元世祖建议开挖安山(今梁山县城北三点五公里处的安山镇)至临清的这段运河。《元史》中载,“起东平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卷六十四)。三年后的六月,这段长二百五十余里的运河开凿完成,接通并取直了京杭大运河,张秋镇设都水分监衙门,元世祖赐名会通河。的确,这条河道成为以后几百年全中国物资最聚集、人口最集中、商贸最发达、文化最昌明的黄金航道,我们聊城历史上的繁荣也由此揭开帷幕。
史料记载,繁荣时期的张秋有周长达八里的城池,城垣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镇内设有工部分司、捕务管河厅、都察院、布政司、巡检司、税课局、户部分司、按察司、演武厅、武衙门、药局、东阿衙、寿张衙、阳谷衙、问水堂、申明亭等公署;曹州、曹县、定陶、郓城、寿张、范县、濮州、朝城、观城水次仓,阳谷、东阿预备仓等行政机构;牌坊、庙宇多繁,俗称“百步一庙宇,半里两牌坊”;会馆、书院、津口处处“云帆樯林,商贾云集,贸易纷错”(明代陈守愚撰编《安平城记》)。这种行政级别的高配大大提升了张秋镇的规格,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社会,行政对商贸、文化的集聚辐射是强大的,物流配套服务功能又衍生出颇多的副业和从属。今天,我们甚至可以从张秋的地名上依稀可辨往日的景象,金堤下的那一溜营子(颜营、窦营、董营、五里营、王营)里住着各色官吏、兵卒、夫役、医师等,单是役夫,就有专业分工细密的闸夫(启闭闸板的)、溜夫(导引船只过闸的)、浅夫(导引船只渡浅滩的)、泉夫(挑浚泉道的)。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特别是在历经几乎一冬的深霾之后,明晃晃的阳光照在脸上、身上,特别舒服。阳光下,大街上商贩走卒簇拥,人车如流,零摊儿、门店俱是买卖红火,我恍若穿越到几百年前的大商埠张秋。
历史悠远的张秋、风生水起的张秋,可能是聊城人文历史资源最丰足的地方了。很显然,五体十三碑是张秋历史上经济文化繁盛的最重量级的明证了。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时任张秋工部分司管理河道官的杨淳修建季子祠,树碑刻诗,后历经隆庆、万历,过往张秋的文人官员纷纷题咏镌碑,并续修季子祠,五体十三碑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十三块诗碑,除一块碎裂仅存残字外,其余十二碑基本清晰可辨,碑刻十三位作者二十六首诗,楷行草隶篆五体兼备,其中不乏大家,如元代诗人萨天锡、明代文学家李东阳、屠隆、傅光宅。
季子何人?春秋时期的吴国大贤。其先祖太伯系周王朝继承人,后贤让远去荆蛮创建了吴国,数代后的吴王寿梦少子季札在兄弟四人中最有德行,吴王有意传位于他,下边也争相拥戴,但季札坚辞,遂退隐山水间。季札是历史上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也被称为“南方第一圣人”,素有“南季北孔”之称,是先秦时代最伟大的预言家、美学家、艺术评论家,中华文明史上礼仪和诚信的代表人物。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出使鲁、齐、郑、卫、晋五国,有一次经徐国,过张秋,留下今日季札挂剑之故事。
风生水起的张秋镇是运河古镇,是历史名镇,自然也是文物大镇。张秋拥有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占阳谷县的三分之一(全县共五十四处,张秋镇占十八处,镇驻地就有八处);1968年以后,全县征集、出土、入藏的文物两千余件,绝大部分出自张秋;明清时期就建有文庙和安平书院,还有专门刻印、经营书籍的保华书局。张秋木版年画依稀可见当年与山陕的往来,粗犷写意的门神和活灵活现的童子花篮年画上京津、下东北,可见张秋的影响之大。
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地方自然民间故事、传说也多。此次的张秋行,我们还去了陈家大院、任疯子墓和黑龙潭。黄河金堤下的黑龙潭面积不大,故事却多。在临近中午的阳光下,黑龙潭波光粼粼,潭边枯草丛密,不远处就是高高的金堤了。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站在黄河的金堤上,心旷神怡,极目滩地阔处,一行白鹭与灰鹭的混合编队正好起飞。
(初稿于2017年1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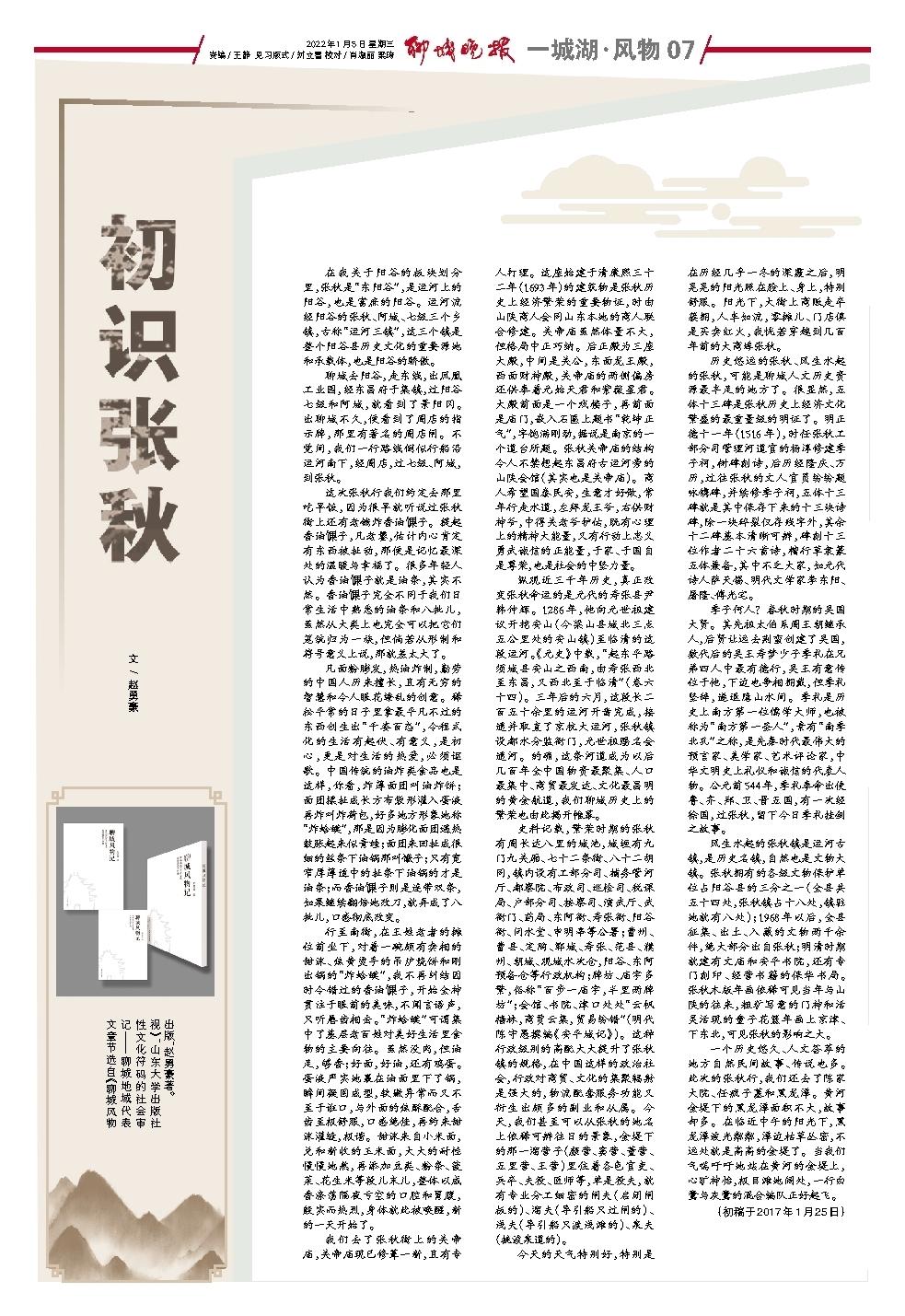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