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庙胡同:蜿蜒曲折里几多向往与乡愁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从临清先锋路街道太平街居委会办公楼东行,经过一排平房,就能看到一条约2米宽、百余米长、南北走向的胡同,因东邻曾有一座娘娘庙,这条胡同得名娘娘庙胡同。
临清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先有娘娘庙,再有临清城”,斗转星移,庙宇已不复存在,但娘娘庙胡同仿佛仍在述说着娘娘庙与临清千丝万缕的联系。
曾经
承载着乡愁与向往
在临清民间有一种说法,很久之前的娘娘庙是妈祖娘娘庙,即庙里供奉的是“海神”妈祖娘娘。但细细想来,地处内陆的北方小城临清供奉“海神”妈祖娘娘,似乎并不是偶然。
“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临清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悠悠运河,不仅是当时重要的黄金经济带,也是一条承载着文化底蕴的文化大动脉。
妈祖文化伴水而生,依水而兴。明清时期,得益于会通河的开通和疏浚,临清成为南北水陆要冲、漕船必经之地。“贾舶漕艘,帆影不绝。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临清出现了航运兴旺、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的景象,来往的舟船、过往的客商昼夜不息,地方特产琳琅满目,临清也因此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都会。临清城内的商贩日渐增多,活跃于临清市场的有本地商人,也有从南方顺水而来的外地客商。无数商船沿着运河往来穿梭,把妈祖文化从南方带到了临清这座北方小城,也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彼时,临清不仅拥有运河上的第一大码头,还有明朝三大造船厂之一的卫河船厂,“天下能工巧匠皆聚于斯”。另有资料记载,明代在临清任职的闽浙籍官员有近百位,仅临清钞关的官员就有20余位是福建人,而福建正是妈祖的故乡。在异乡待久了,会把异乡当家乡,在临清建造妈祖娘娘庙也顺理成章。其实,历史上临清有数座官庙供奉妈祖娘娘,如卫河东岸的三元阁、元运河北岸的娘娘庙等。对这些在异乡谋生计的人而言,供奉妈祖不仅是信仰和精神的寄托,更是深切而浓郁的乡愁,这座庙宇,让他们的乡愁有了归处。
关于娘娘庙,明代临清名人方元焕的《重修碧霞宫记》云:“娘娘庙即碧霞宫,在广积门外,原有旧宇,明正统四年,守御千户所吴刚置地扩之,前为广生殿,有门,有坊。”之后,娘娘庙再扩,“嘉靖十九年,道士刘守祥募众附建三清阁于后,曰玉虚真境,下为真武行祠”。“清末以来,一直延续‘废庙兴学’,娘娘庙逐渐走向衰落,部分房舍辟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娘娘庙被改造成临清搬运队和搬运职工诊所。”9月3日,临清胡同游发起人刘英顺说。
运河文化,依水绵延,这条胡同是临清这座运河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娘娘庙胡同曾收藏了异乡人浓郁的乡愁,也承载了人们对美好和幸福的向往。
现在
隐匿于市的烟火人间
随着时代变迁,娘娘庙渐行渐远。20世纪末,临清城填坑造地,娘娘庙旁边的大水坑被填埋,人们在上面建起民房。21世纪初,临清城市改造,娘娘庙遗址彻底消失,原址建起了小区住宅楼。
走出胡同,平坦的马路上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胡同,曲折蜿蜒的石板路旁是绿荫如盖的梧桐树和坐在家门口摇着蒲扇、逗狗乘凉的老人。小小的老胡同,喧嚣城市里的一隅,自然、宁静而又富有人情味,仿佛是躲在胡同背后的隐士,静静地看着这座小城的喧嚣与繁华。
68岁的赵全福是这条胡同的老居民,胡同里生,胡同里长,在赵全福的记忆里,小时候的胡同比现在宽,胡同的东边有很多大坑,“听老人说,水坑旁边曾有座娘娘庙,”赵全福对娘娘庙的记忆来自长者的描述,而娘娘庙旁边的大水坑是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小时候住的都是土房子,一大家子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也不分院,有很多小孩子,吃完饭就跑到大坑里玩儿,一直玩儿到天黑还不愿意回家,夏天,各家人吃完饭都会出来遛弯儿、聊天。”赵全福说,他娶妻时,家里把胡同里的老院子进行了翻修,再后来,赵全福的孩子长大成人,赵全福把院子进行了修整。现在,赵全福的孩子从胡同里搬了出去,住进了楼房,但赵全福觉得在老胡同里住着更舒服,“我哪也不去,这辈子就在这条胡同里。”
在赵全福的院子里,曲折而向上的老枣树独撑一枝,上面挂满了椭圆形半青半红的枣子。枣树下,三只小狗乖巧地卧在赵全福的脚边,赵全福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与记者聊起他在这个胡同里的往事,这只是这个老胡同里最为平常的一幕。在胡同里居住了将近70年,赵全福把胡同的变迁都看在了眼里。
今年67岁的陈桂玲是这个老胡同的新居民,两年前,她和老伴卖掉市区的商品房,在胡同里买了一处小院儿。记者遇到她时,她刚买菜回来,三轮车里装着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到了家门口,陈桂玲一边推门而入,一边热情地招呼记者“进家喝口水”。胡同人家最闲情,养花养鸟种树,陈桂玲也不例外,她把有限的空间都利用了起来,进入大门,迎面而来的就是斑驳的墙上爬满了绿油油的丝瓜藤和院落里的各种花草。陈桂玲说,她打小在村子里长大,觉得在院子里才是过日子,这条胡同让她找到了归属感。说话间,有人在门口停下与陈桂玲寒暄,那是她搬来之后熟稔的街坊。
有人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胡同里的寻常百姓家,充满了烟火气,鲜活而生动,或许,这是很多人依恋胡同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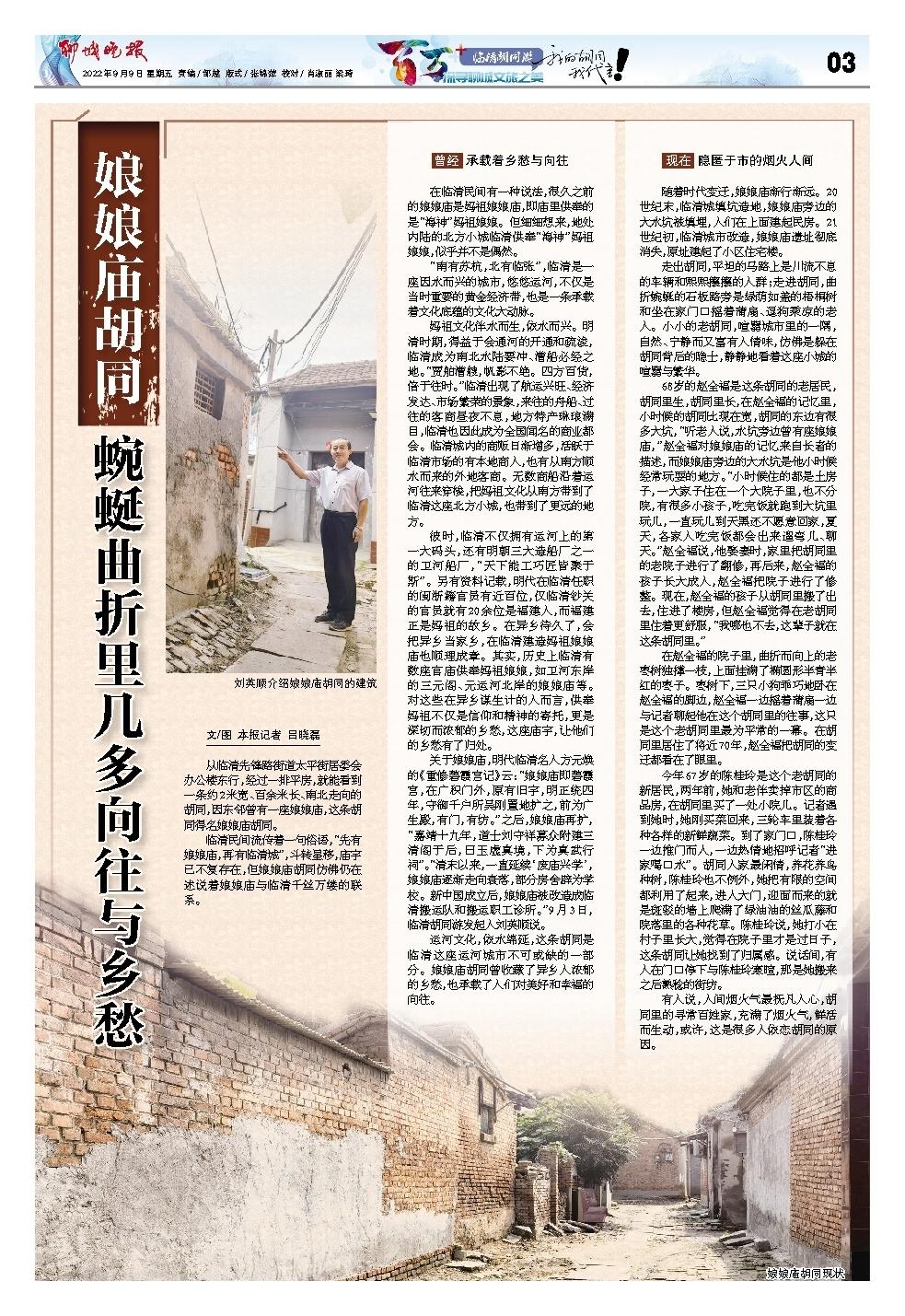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