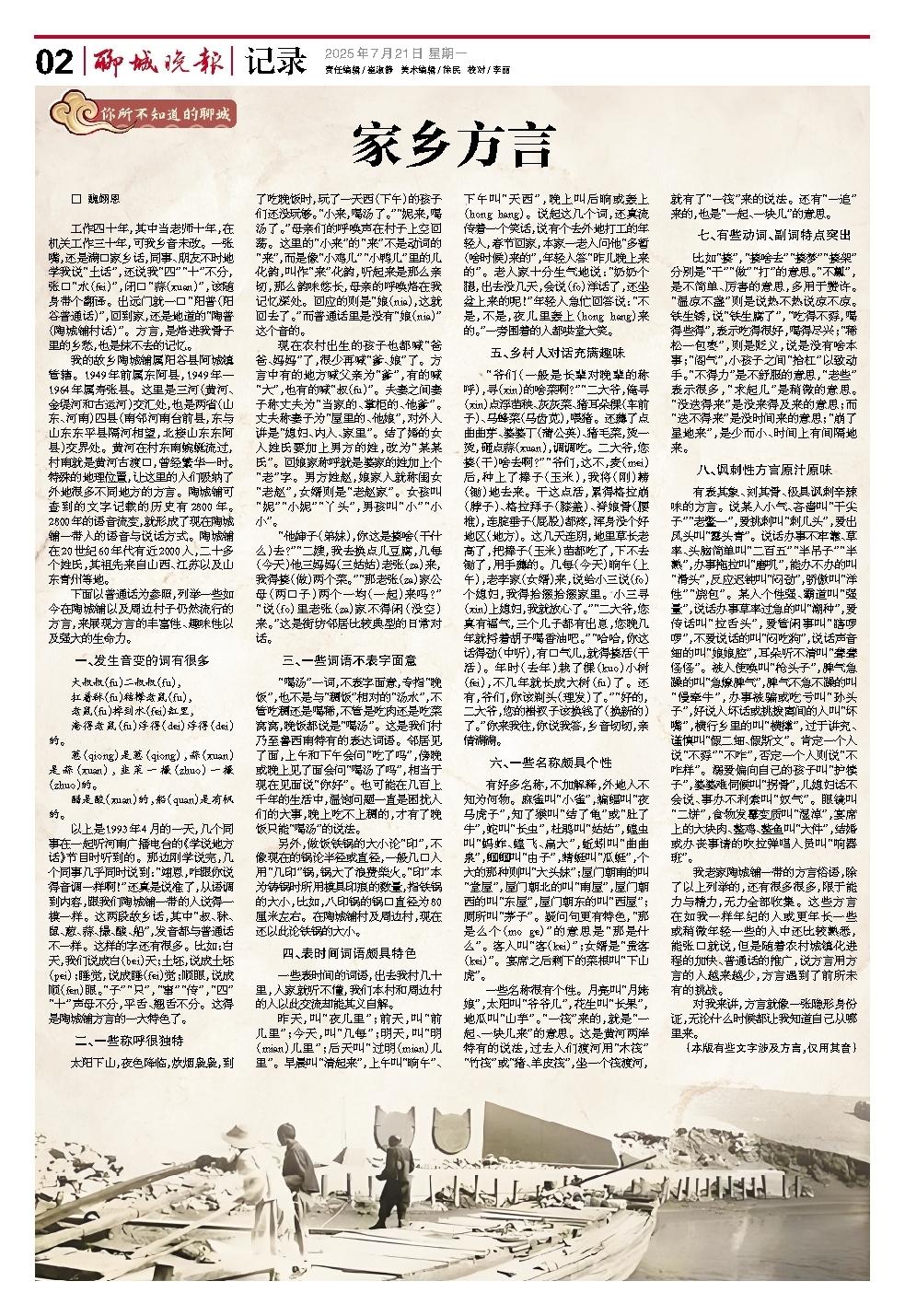家乡方言
□ 魏翊恩
工作四十年,其中当老师十年,在机关工作三十年,可我乡音未改。一张嘴,还是满口家乡话,同事、朋友不时地学我说“土话”,还说我“四”“十”不分,张口“水(fei)”,闭口“蒜(xuan)”,该随身带个翻译。出远门就一口“阳普(阳谷普通话)”,回到家,还是地道的“陶普(陶城铺村话)”。方言,是烙进我骨子里的乡愁,也是抹不去的记忆。
我的故乡陶城铺属阳谷县阿城镇管辖。1949年前属东阿县,1949年—1964年属寿张县。这里是三河(黄河、金堤河和古运河)交汇处,也是两省(山东、河南)四县(南邻河南台前县,东与山东东平县隔河相望,北接山东东阿县)交界处。黄河在村东南蜿蜒流过,村南就是黄河古渡口,曾经繁华一时。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人们吸纳了外地很多不同地方的方言。陶城铺可查到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有2800年。2800年的语音流变,就形成了现在陶城铺一带人的语音与说话方式。陶城铺在20世纪60年代有近2000人,二十多个姓氏,其祖先来自山西、江苏以及山东青州等地。
下面以普通话为参照,列举一些如今在陶城铺以及周边村子仍然流行的方言,来展现方言的丰富性、趣味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
一、发生音变的词有很多
大叔叔(fu)二叔叔(fu),
扛着秫(fu)秸撵老鼠(fu),
老鼠(fu)掉到水(fei)缸里,
淹得老鼠(fu)浮得(dei)浮得(dei)的。
葱(qiong)是葱(qiong),蒜(xuan)是蒜(xuan),韭菜一撮(zhuo)一撮(zhuo)的。
醋是酸(xuan)的,船(quan)是有帆的。
以上是1993年4月的一天,几个同事在一起听河南广播电台的《学说地方话》节目时听到的。那边刚学说完,几个同事几乎同时说到:“翊恩,咋跟你说得音调一样啊!”还真是说准了,从语调到内容,跟我们陶城铺一带的人说得一模一样。这两段故乡话,其中“叔、秫、鼠、葱、蒜、撮、酸、船”,发音都与普通话不一样。这样的字还有很多。比如:白天,我们说成白(bei)天;土坯,说成土坯(pei);睡觉,说成睡(fei)觉;顺眼,说成顺(fen)眼。“子”“只”,“窜”“传”,“四”“十”声母不分,平舌、翘舌不分。这得是陶城铺方言的一大特色了。
二、一些称呼很独特
太阳下山,夜色降临,炊烟袅袅,到了吃晚饭时,玩了一天西(下午)的孩子们还没玩够。“小来,喝汤了。”“妮来,喝汤了。”母亲们的呼唤声在村子上空回荡。这里的“小来”的“来”不是动词的“来”,而是像“小鸡儿”“小鸭儿”里的儿化韵,叫作“来”化韵,听起来是那么亲切,那么韵味悠长,母亲的呼唤烙在我记忆深处。回应的则是“娘(nia),这就回去了。”而普通话里是没有“娘(nia)”这个音的。
现在农村出生的孩子也都喊“爸爸、妈妈”了,很少再喊“爹、娘”了。方言中有的地方喊父亲为“爹”,有的喊“大”,也有的喊“叔(fu)”。夫妻之间妻子称丈夫为“当家的、掌柜的、他爹”。丈夫称妻子为“屋里的、他娘”,对外人讲是“媳妇、内人、家里”。结了婚的女人姓氏要加上男方的姓,改为“某某氏”。回娘家称呼就是婆家的姓加上个“老”字。男方姓赵,娘家人就称闺女“老赵”,女婿则是“老赵家”。女孩叫“妮”“小妮”“丫头”,男孩叫“小”“小小”。
“他婶子(弟妹),你这是揍啥(干什么)去?”“二嫂,我去换点儿豆腐,几每(今天)他三妈妈(三姑姑)老张(za)来,我得揍(做)两个菜。”“那老张(za)家公母(两口子)两个一均(一起)来吗?”“说(fo)里老张(za)家不得闲(没空)来。”这是街坊邻居比较典型的日常对话。
三、一些词语不表字面意
“喝汤”一词,不表字面意,专指“晚饭”,也不是与“稠饭”相对的“汤水”,不管吃稠还是喝稀,不管是吃肉还是吃菜窝窝,晚饭都说是“喝汤”。这是我们村乃至鲁西南特有的表达词语。邻居见了面,上午和下午会问“吃了吗”,傍晚或晚上见了面会问“喝汤了吗”,相当于现在见面说“你好”。也可能在几百上千年的生活中,温饱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的大事,晚上吃不上稠的,才有了晚饭只能“喝汤”的说法。
另外,做饭铁锅的大小论“印”,不像现在的锅论半径或直径,一般几口人用“几印”锅,锅大了浪费柴火。“印”本为铸锅时所用模具印痕的数量,指铁锅的大小,比如,八印锅的锅口直径为80厘米左右。在陶城铺村及周边村,现在还以此论铁锅的大小。
四、表时间词语颇具特色
一些表时间的词语,出去我村几十里,人家就听不懂,我们本村和周边村的人以此交流却能其义自解。
昨天,叫“夜儿里”;前天,叫“前儿里”;今天,叫“几每”;明天,叫“明(mian)儿里”;后天叫“过明(mian)儿里”。早晨叫“清起来”,上午叫“晌午”、下午叫“天西”,晚上叫后晌或轰上(hong hang)。说起这几个词,还真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有个去外地打工的年轻人,春节回家,本家一老人问他“多暂(啥时候)来的”,年轻人答“昨儿晚上来的”。老人家十分生气地说:“奶奶个腿,出去没几天,会说(fo)洋话了,还坐盆上来的呢!”年轻人急忙回答说:“不是,不是,夜儿里轰上(hong hang)来的。”一旁围着的人都哄堂大笑。
五、乡村人对话充满趣味
“爷们(一般是长辈对晚辈的称呼),寻(xin)的啥菜啊?”“二大爷,俺寻(xin)点浮苗秧、灰灰菜、猪耳朵棵(车前子)、马蜂菜(马齿苋),喂猪。还薅了点曲曲芽、婆婆丁(蒲公英)、猪毛菜,烫一烫,砸点蒜(xuan),调调吃。二大爷,您揍(干)啥去啊?”“爷们,这不,麦(mei)后,种上了棒子(玉米),我将(刚)耪(锄)地去来。干这点活,累得格拉崩(脖子)、格拉拜子(膝盖)、脊娘骨(腰椎),连腚垂子(屁股)都疼,浑身没个好地区(地方)。这几天连阴,地里草长老高了,把棒子(玉米)苗都吃了,下不去锄了,用手薅的。几每(今天)晌午(上午),老李家(女婿)来,说给小三说(fo)个媳妇,我得拾掇拾掇家里。小三寻(xin)上媳妇,我就放心了。”“二大爷,您真有福气,三个儿子都有出息,您晚几年就捋着胡子喝香油吧。”“哈哈,你这话得劲(中听),有口气儿,就得揍活(干活)。年时(去年)栽了棵(kuo)小树(fei),不几年就长成大树(fu)了。还有,爷们,你该剃头(理发)了。”“好的,二大爷,您的褂衩子该换钱了(换新的)了。”你来我往,你说我答,乡音切切,亲情满满。
六、一些名称颇具个性
有好多名称,不加解释,外地人不知为何物。麻雀叫“小雀”,蝙蝠叫“夜马虎子”,知了猴叫“结了龟”或“肚了牛”,蛇叫“长虫”,杜鹃叫“姑姑”,蝗虫叫“蚂蚱、蝗飞、扁大”,蚯蚓叫“曲曲泉”,蝈蝈叫“由子”,蜻蜓叫“瓜蜓”,个大的那种则叫“大头妹”;屋门朝南的叫“堂屋”,屋门朝北的叫“南屋”,屋门朝西的叫“东屋”,屋门朝东的叫“西屋”;厕所叫“茅子”。疑问句更有特色,“那是么个(mo ge)”的意思是“那是什么”。客人叫“客(kei)”;女婿是“贵客(kei)”。宴席之后剩下的菜根叫“下山虎”。
一些名称很有个性。月亮叫“月姥娘”,太阳叫“爷爷儿”,花生叫“长果”,地瓜叫“山芋”。“一筏”来的,就是“一起、一块儿来”的意思。这是黄河两岸特有的说法,过去人们渡河用“木筏”“竹筏”或“猪、羊皮筏”,坐一个筏渡河,就有了“一筏”来的说法。还有“一追”来的,也是“一起、一块儿”的意思。
七、有些动词、副词特点突出
比如“揍”,“揍啥去”“揍梦”“揍架”分别是“干”“做”“打”的意思。“不瓤”,是不简单、厉害的意思,多用于赞许。“温凉不盏”则是说热不热说凉不凉。铁生锈,说“铁生腐了”,“吃得不孬,喝得些得”,表示吃得很好,喝得尽兴;“稀松一包枣”,则是贬义,说是没有啥本事;“阁气”,小孩子之间“抬杠”以致动手。“不得力”是不舒服的意思,“老些”表示很多,“求起儿”是稍微的意思。“没迭得来”是没来得及来的意思;而“迭不得来”是没时间来的意思;“崩了星地来”,是少而小、时间上有间隔地来。
八、讽刺性方言原汁原味
有表其象、刻其骨、极具讽刺辛辣味的方言。说某人小气、吝啬叫“干尖子”“老鳖一”,爱挑刺叫“刺儿头”,爱出风头叫“露头青”。说话办事不牢靠、草率、头脑简单叫“二百五”“半吊子”“半熟”,办事拖拉叫“磨叽”,能办不办的叫“滑头”,反应迟钝叫“闷劲”,骄傲叫“洋性”“烧包”。某人个性强、霸道叫“强量”,说话办事草率过急的叫“潮种”,爱传话叫“拉舌头”,爱管闲事叫“瞎啰啰”,不爱说话的叫“闷吃狗”,说话声音细的叫“娘娘腔”,耳朵听不清叫“聋聋怪怪”。被人使唤叫“枪头子”,脾气急躁的叫“急燎脾气”,脾气不急不躁的叫“慢牵牛”,办事被骗或吃亏叫“孙头子”,好说人坏话或挑拨离间的人叫“坏嘴”,横行乡里的叫“横撑”,过于讲究、谨慎叫“假二细、假斯文”。肯定一个人说“不孬”“不咋”,否定一个人则说“不咋样”。溺爱偏向自己的孩子叫“护犊子”,婆婆难伺候叫“拐骨”,儿媳妇话不会说、事办不利索叫“奴气”。眼镜叫“二饼”,食物发霉变质叫“湿淖”,宴席上的大块肉、整鸡、整鱼叫“大件”,结婚或办丧事请的吹拉弹唱人员叫“响器班”。
我老家陶城铺一带的方言俗语,除了以上列举的,还有很多很多,限于能力与精力,无力全部收集。这些方言在如我一样年纪的人或更年长一些或稍微年轻一些的人中还比较熟悉,能张口就说,但是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普通话的推广,说方言用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方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我来讲,方言就像一张隐形身份证,无论什么时候都让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