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春寒里的温暖
■ 魏霞
二十多年前,我参加本科自学考试。听过来人说《古代汉语》一科不好过关,我就报了个培训班。培训的地方离家二百多里,我独自前往,培训一星期。从家出发时天气晴暖,我穿着春装出了门。谁知到达的当晚北风呼呼地刮了一夜,第二天就闹起了倒春寒,空中还飘起了小雪花。
傍晚,学习了一天的我回到居住的旅馆,感到情况不妙:喉咙疼得似刀割,浑身发冷,四肢无力。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这是感冒的前奏。这时再想起老辈人的话——出门,饥不饥带干粮,冷不冷带衣裳,已经迟了。我怕病倒了耽误培训,就决定买感冒药去。咨询旅馆服务员最近的药店位置后,我晃出旅馆,沿街去找。很幸运,过了一个路口,没走几步就有一家。
药店不大,门楣窄小,门头上“康宁药房”四个隶书字写得有些大小不一,细看却别有韵味。我撩开碎花布拼成的棉门帘,一脚迈进去,差点跌倒:里边的地面比外边的街面低了有二三十厘米。或许是天不好的缘故吧,店里甚是昏暗,一只瓦数很小的灯泡有气无力地亮着。看见我进去,一位中年男子从柜台后慌忙站了起来。
“怎么啦?”他关切地问,声音有些沙哑。
我看向他。他上身穿着蓝色的中山装,头发略显稀疏,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大约五十岁的模样,斯斯文文的一个人。
我告诉了他症状。
“先量量体温。”他从柜台一侧的抽屉里拿出一支体温计,甩了甩,递给我。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坐在柜台外的一张圆凳子上打量着药店的陈设:东西两侧靠墙的架子上摆满了西药;正对着门口的墙面,立着由一个个小小的抽屉组成的柜子,那是中药柜了,我想。
“出门在外不容易,得学会照顾好自己。”他说。
我惊。我蹩脚的普通话让他听出我不是本地人。
我虚弱地笑了笑,无奈地看看身上单薄的衣服。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明天气温将有所回升,我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了。”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他补充道:“中央台的天气预报准。”说着温和地向我笑了笑。
我们攀谈了大约五分钟,他要走了体温计,抬头迎着灯光看了看,说:“三十七度二,稍微有些发烧。”
他转身把体温计放进抽屉,让我把胳膊放在柜台上,露出手腕给我把脉。把脉时他并不看我,眼神悠远深邃看向别处。过了一会儿,他拿开把脉的手,慢悠悠地对我说:“不用吃药。”
“不用吃药?”我惊异地问。平时在家一感冒,医生至少让吃上三天的药。他似乎听出了我语调中的疑惑,慢条斯理地向我解释:“你的感冒不严重,主要是上火受凉,充分休息,多喝些热水,完全没有必要吃药。”
他说得没错:我本来睡眠质量就差,加上新换了地方,窗外又呼呼地刮风,搞得我一夜没睡好;培训了一天,因忘记带水杯,一天没能喝口热水。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才给我开了三粒有助于睡眠的药。
第二天,走在异乡的街头,感冒果真不见了踪影。
“但愿世间人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么多年过去了,每逢遇到倒春寒,我总会想起陌生的药店店主给予我的那份善意,心里总是暖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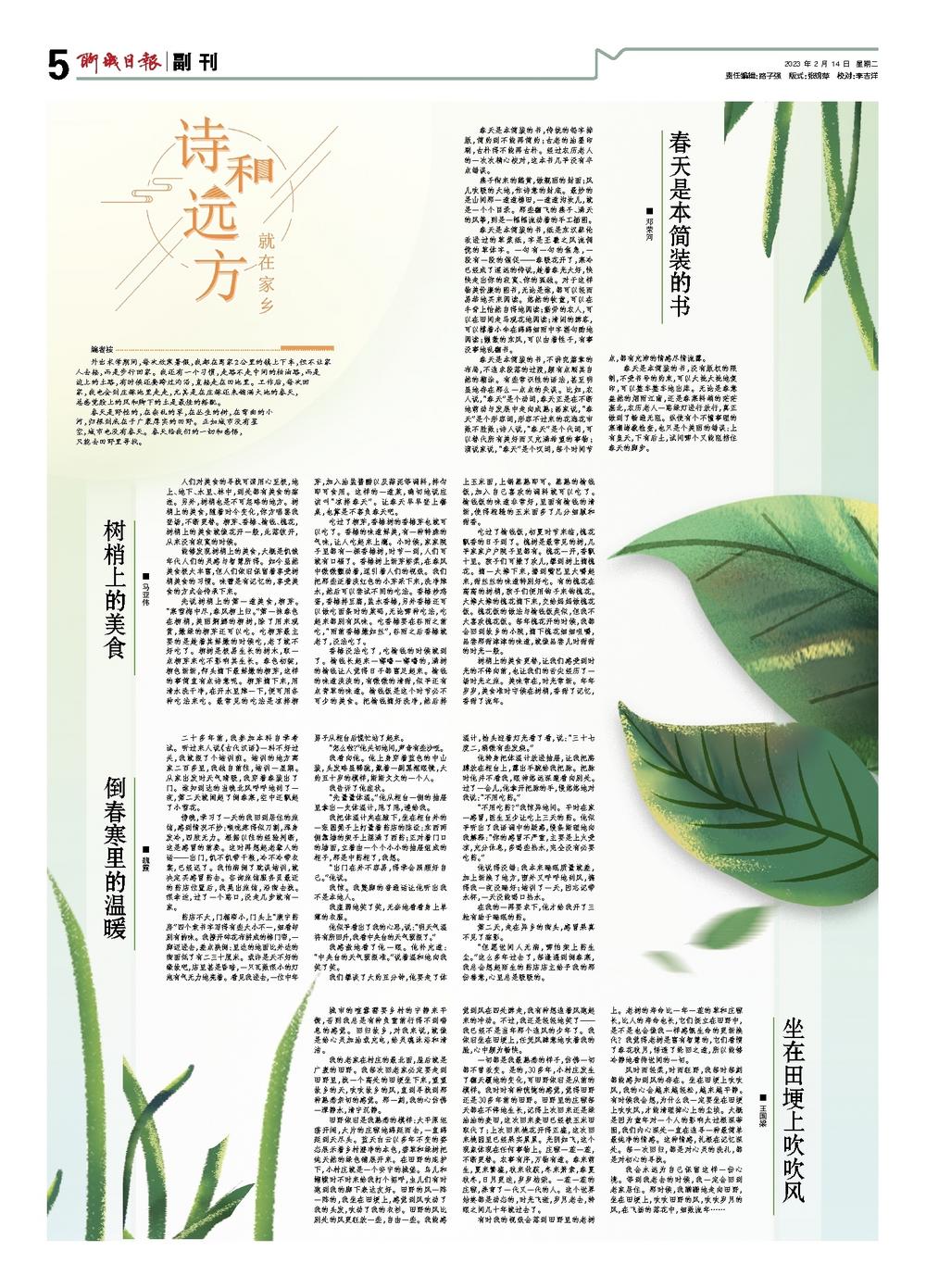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