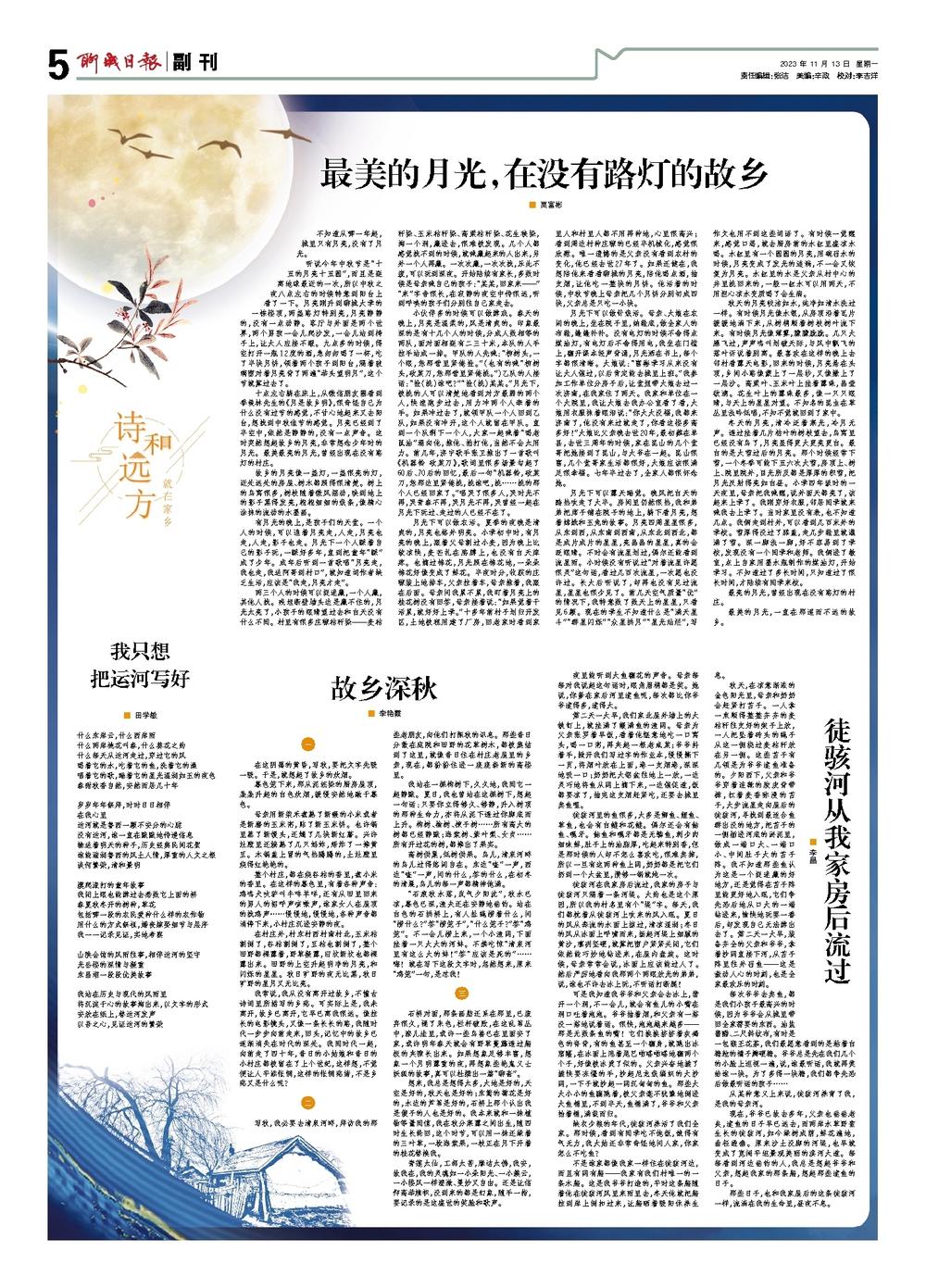故乡深秋
■ 李艳霞
一
在这阴蔼的黄昏,写秋,要把文字先暖一暖。于是,就想起了故乡的炊烟。
暮色笼下来,那从泥坯垛的厨房屋顶,袅袅升起的白色炊烟,缓慢安然地融于暮色。
母亲用新柴禾煮熟了新碾的小米或者是新磨的玉米粥,贴了新玉米饼。也许锅里蒸了新馒头,还熥了几块新红薯。兴许灶膛里还燎熟了几只蚂蚱,焐炸了一捧黄豆。木锅盖上冒的气热腾腾的,土灶膛里烧得红艳艳的。
整个村庄,都在烧谷秸的香里,煮小米的香里。在这样的暮色里,有着各种声音:鸡鸣犬吠驴叫牛哞羊咩,还有从田里回来的男人的招呼声咳嗽声,谁家女人在屋顶的找鸡声……慢慢地,慢慢地,各种声音都消停下来,小村庄沉进安静的夜。
在村庄外,村东村西村南村北,玉米秸割倒了,谷秸割倒了,豆秸也割倒了,整个田野都裸露着,野草凝露,旧坟新坟也都裸露出来。田野的上空升起明净的月亮,和闪烁的星星。秋日旷野的夜无比黑,秋日旷野的星月又无比亮。
我常说,我从没有离开过故乡,不懂古诗词里所描写的乡愁。可实际上是,我未离开,故乡已离开,它早已离我很远。像拉长的电影镜头,又像一条长长的路,我随时代一步步向前走来,回头,记忆中的故乡已逐渐消失在时代的深处。我同时代一起,向前走了四十年,昔日的小姑娘和昔日的小村庄都被留在了上个世纪,这样想,不觉便让人平添怅惘,这样的怅惘愁绪,不是乡愁又是什么呢?
二
写秋,我必要去清泉河畔,拜访我的那些老朋友,向他们打探秋的讯息。那些昔日分散在庭院和田野的花草树木,都被集结到了这里,就像昔日住在村庄老屋里的乡亲,现在,都纷纷住进一座座崭新的高楼里。
我站在一棵构树下,久久地,我同它一起静默。夏日,我也曾站在这棵树下,想起一句话:只要你立得够久、够静,升入树顶的那种生命力,亦将从泥下透过你脚底而上升。构树、榆树、楝子树……所有高大的树都已经静默;海棠树、紫叶梨、女贞……所有开过花的树,都捧出了果实。
高树供巢,低树供果。鸟儿,清泉河畔的鸟儿过得悠闲自在。东边“喳”一声,西边“喳”一声,问的什么,答的什么,在初冬的清晨,鸟儿的每一声都精神饱满。
“石痕秋水落,岚气夕阳沈”,秋水已凉,暮色已深,渔夫还在安静地垂钓。站在白色的石拱桥上,有人扯绳捞着什么,问“捞什么?”答“捞笼子”,“什么笼子?”答“鸡笼”。不一会儿捞上来,一个小渔网,下面挂着一只大大的河蚌。不禁吃惊“清泉河里有这么大的蚌!”答“应该是死的”……嗨!就在写下这段文字时,忽然想来,原来“鸡笼”一句,是怼我!
三
石桥对面,那条画舫还系在那里,已废弃很久,褪了朱色,栏杆破败,在这乱苇丛中,潦儿洼里,或许一些鸟兽已在里面安了家,或许明年春天就会有野草蔓藤透过船板的夹隙长出来。如果想象足够丰富,想象一个月明露重的夜,再想象些艳鬼义士妖狐的故事,真可以杜撰出一篇“聊斋”。
想来,我总是想得太多,大地是好的,天空是好的,秋天也是好的;东篱的菊花是好的,水边的芦苇是好的,石桥上那个认出我是傻子的人也是好的。我本来就和一株植物等量同值,我在秋分寒露之间出生,随四时生长轮回,这个时节,可以用一株还绿着的三叶草,一枚海棠果,一枝正在月下开着的桂花替换我。
青莲太仙,工部太苦,摩诘太佛,我安,故我在,我的灵魂如一小朵阳光、一小簇云,一小缕风一样澄澈、曼妙又自由。还是让信仰高举旗帜,没到来的都是幻象,随手一指,要记录的是这盛世的笑脸和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