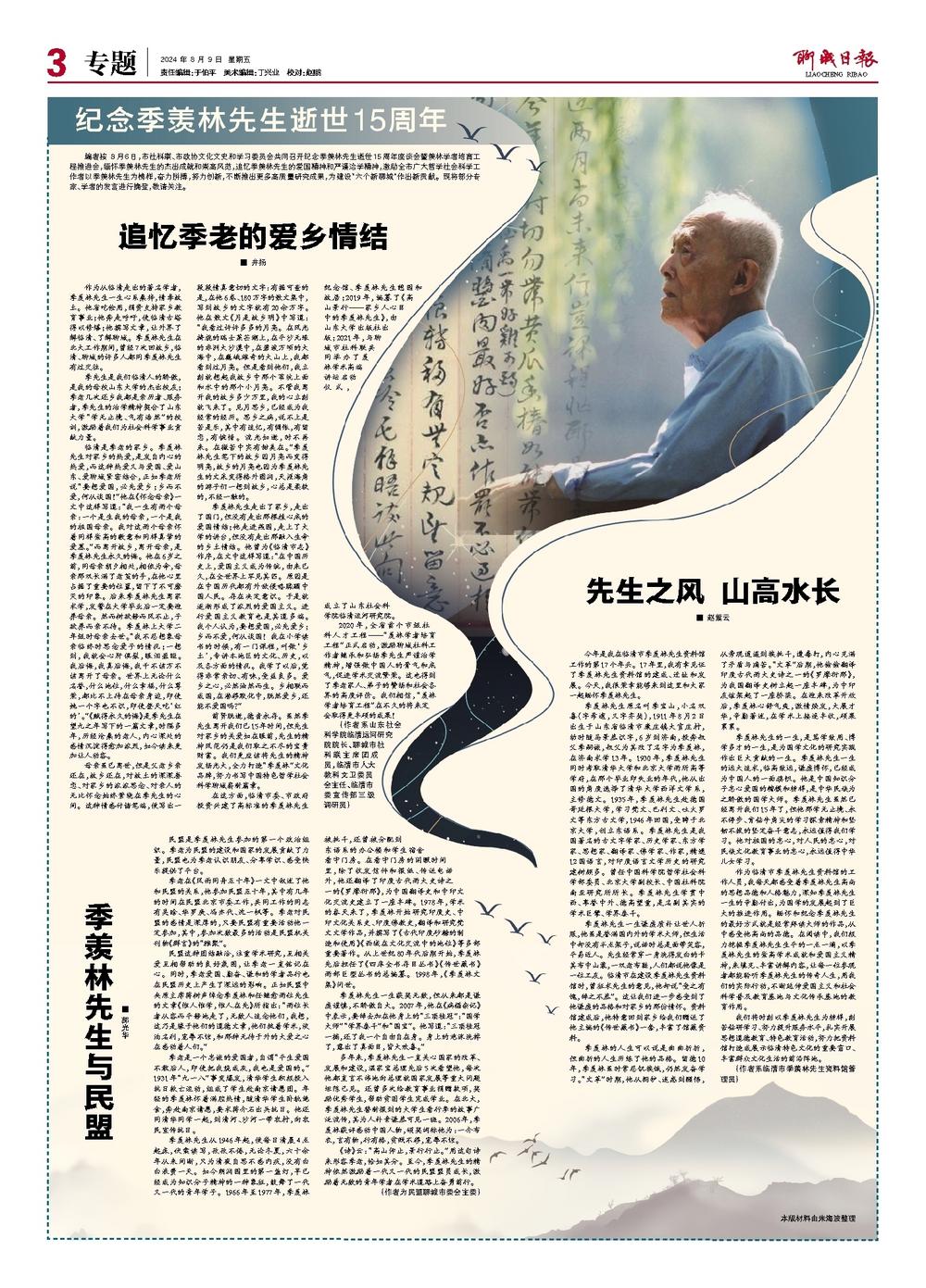季羡林先生与民盟
■ 郝光华
民盟是季羡林先生参加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季老为民盟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民盟也为季老认识朋友、分享学识、感受快乐提供了平台。
季老在《风雨同舟五十年》一文中叙述了他和民盟的关系,他参加民盟五十年,其中有几年的时间在民盟北京市委工作,共同工作的同志有吴晗、华罗庚、冯亦代、沈一帆等。季老对民盟的感情是深厚的,只要民盟有重要活动他一定参加,其中,参加次数最多的活动是民盟机关刊物《群言》的“雅聚”。
民盟这种团结融洽,注重学术研究,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良好氛围,让季老一直铭记在心。同时,季老爱国、勤奋、谦和的学者品行也在民盟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民盟中央原主席蒋树声悼念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先生的文章《惟人惟学,惟人在先》所指出:“两位长者从容而平静地走了,无数人追念他们,我想,这乃是缘于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执着学术,淡泊名利,宠辱不惊,和那种无待于外的大爱之心在感动着人们。”
季老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年轻的季羡林怀着满腔热情,随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他还同清华同学一起,到清河、沙河一带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
季羡林先生从1946年起,便每日清晨4点起床,伏案读写,孜孜不倦,无论冬夏,六十余年从未间断,只为清夜自思不感内疚,没有白白浪费一天。如今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早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的一种象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1966年至1977年,季羡林被批斗,还曾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看守门房。在看守门房的闲暇时间里,除了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外,他还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1978年,学术的春天来了,季羡林开始研究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并撰写了《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季羡林先后担任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998年,《季羡林文集》问世。
季羡林先生一生获奖无数,但从来都是谦虚谨慎,不骄傲自大。2007年,他在《病榻杂记》中表示,要辞去加在他身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他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多年来,季羡林先生一直关心国家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温家宝总理先后5次看望他,每次他都直言不讳地向总理就国家发展等重大问题坦陈己见。还曾多次给教育事业捐赠款项,奖励优秀学生,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在北大,季羡林先生替新报到的大学生看行李的故事广泛流传,其为人朴素谦恭可见一斑。2006年,季羡林获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称他为: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这句诗来形容季老,恰如其分。至今,季羡林先生的精神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民盟盟员成长,激励着无数的青年学者在学术道路上奋勇前行。
(作者为民盟聊城市委会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