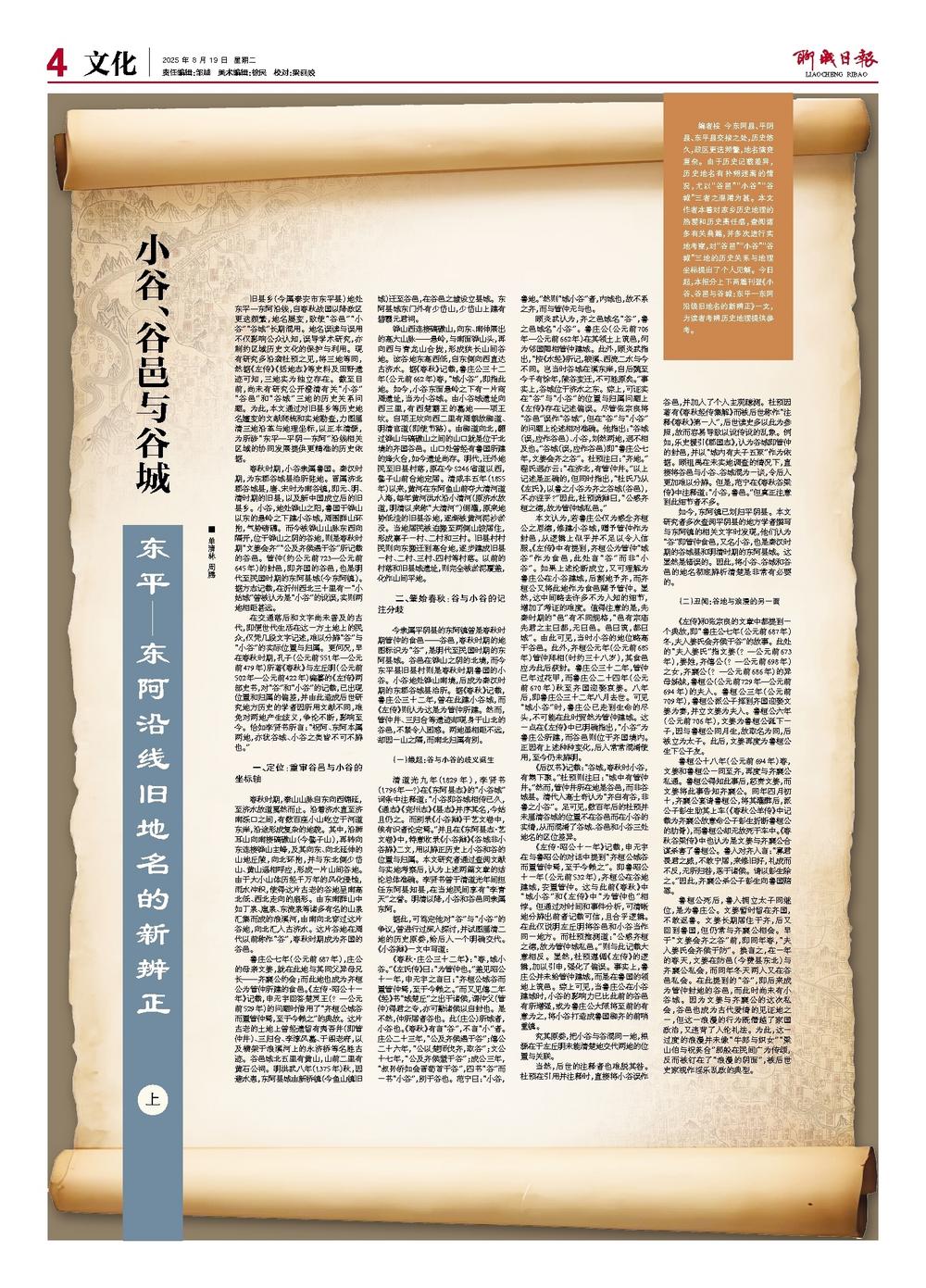小谷、谷邑与谷城
东平—东阿沿线旧地名的新辨正(上)
编者按 今东阿县、平阴县、东平县交接之处,历史悠久,政区更迭频繁,地名演变复杂。由于历史记载差异,历史地名有扑朔迷离的情况,尤以“谷邑”“小谷”“谷城”三者之混淆为甚。本文作者本着对家乡历史地理的热爱和历史责任感,查阅诸多有关典籍,并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对“谷邑”“小谷”“谷城”三地的历史关系与地理坐标提出了个人见解。今日起,本报分上下两篇刊登《小谷、谷邑与谷城:东平—东阿沿线旧地名的新辨正》一文,为读者考辨历史地理提供参考。
■ 单清林 周腾
旧县乡(今属泰安市东平县)地处东平—东阿沿线,自春秋战国以降政区更迭频繁,地名屡变,致使“谷邑”“小谷”“谷城”长期混用。地名误读与误用不仅影响公众认知,误导学术研究,亦制约区域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利用。现有研究多沿袭杜预之见,将三地等同,然据《左传》《括地志》等史料及田野遗迹可知,三地实为独立存在。截至目前,尚未有研究公开澄清有关“小谷”“谷邑”和“谷城”三地的历史关系问题。为此,本文通过对旧县乡等历史地名嬗变的文献爬梳和实地勘查,力图厘清三地沿革与地理坐标,以正本清源,为所涉“东平—平阴—东阿”沿线相关区域的协同发展提供更精准的历史依据。
春秋时期,小谷隶属鲁国。秦汉时期,为东郡谷城县治所驻地。晋属济北郡谷城县,唐、宋时为南谷镇,即元、明、清时期的旧县,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旧县乡。小谷,地处铧山之阳,鲁国于铧山以东的悬岭之下建小谷城,周围群山环抱,气势磅礴。而今被铧山山脉东西向隔开,位于铧山之阴的谷地,则是春秋时期“文姜会齐”“公及齐侯遇于谷”所记载的谷邑。管仲(约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的封邑,即齐国的谷邑,也是明代至民国时期的东阿县城(今东阿镇)。据方志记载,在沂州西北三十里有一“小姑城”曾被认为是“小谷”的讹误,实则两地相距甚远。
在交通落后和文字尚未普及的古代,即便世代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民众,仅凭几段文字记述,难以分辨“谷”与“小谷”的实际位置与归属。更何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所著《春秋》与左丘明(公元前502年—公元前422年)编纂的《左传》两部史书,对“谷”和“小谷”的记载,已出现位置和归属的偏差,并由此造成后世研究地方历史的学者因所用文献不同,难免对两地产生歧义,争论不断,影响至今。恰如李贤书所言:“祝阿、东阿本属两地,亦犹谷城、小谷之类皆不可不辨也。”
一、定位:重审谷邑与小谷的坐标轴
春秋时期,泰山山脉自东向西绵延,至济水故道戛然而止。沿着济水直至济南泺口之间,有数百座小山屹立于河道东岸,沿途形成复杂的地貌。其中,沿狮耳山向南接碻磝山(今鏊子山),再转向东连接铧山主峰,及其向东、向北延伸的山地丘陵,向北环抱,并与东北侧少岱山、黄山遥相呼应,形成一片山间谷地。由于大小山体历经千万年的风化侵蚀,雨水冲积,使得这片古老的谷地呈南高北低、西北走向的扇形。由东南群山中如丁泉、扈泉、东流泉等诸多有名的山泉汇集而成的浪溪河,由南向北穿过这片谷地,向北汇入古济水。这片谷地在周代以前称作“谷”,春秋时期成为齐国的谷邑。
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庄公的母亲文姜,就在此地与其同父异母兄长——齐襄公约会;而此地也成为齐桓公为管仲所建的食邑。《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申无宇回答楚灵王(?—公元前529年)的问题时借用了“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的典故。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遗留有夷吾井(即管仲井)、三归台、李淳风墓、于阁老府,以及横架于浪溪河上的永济桥等名胜古迹。谷邑城北五里有黄山,山前二里有黄石公祠。明洪武八年(1375年)秋,因避水患,东阿县城由新桥镇(今鱼山镇旧城)迁至谷邑,在谷邑之墟设立县城。东阿县城东门外有少岱山,少岱山上建有碧霞元君祠。
铧山西连接碻磝山,向东、南伸展出的高大山脉——悬岭,与南面铧山头,再向西与青龙山合拢,形成狭长山间谷地。该谷地东高西低,自东侧向西直达古济水。据《春秋》记载,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春,“城小谷”,即指此地。如今,小谷东面悬岭之下有一片商周遗址,当为小谷城。由小谷城遗址向西三里,有西楚霸王的墓地——项王坟。自项王坟向西二里有周朝故御道、明清官道(即使节路)。由御道向北,翻过铧山与碻磝山之间的山口就是位于北境的齐国谷邑。山口处曾经有鲁国所建的烽火台,如今遗址尚存。明代,迁外地民至旧县村落,原在今S246省道以西,鏊子山前台地定居。清咸丰五年(1855年)以来,黄河在东阿鱼山前夺大清河道入海,每年黄河洪水沿小清河(原济水故道,明清以来称“大清河”)倒灌,原来地势低洼的旧县谷地,逐渐被黄河泥沙淤没。当地居民被迫搬至两侧山坡居住,形成寨子一村、二村和三村。旧县村村民则向东搬迁到高台地,逐步建成旧县一村、二村、三村、四村等村落。以前的村落和旧县城遗址,则完全被淤泥覆盖,化作山间平地。
二、肇始春秋:谷与小谷的记注分歧
今隶属平阴县的东阿镇曾是春秋时期管仲的食邑——谷邑,春秋时期的地图标识为“谷”,是明代至民国时期的东阿县城。谷邑在铧山之阴的北境,而今东平县旧县村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小谷。小谷地处铧山南境,后成为秦汉时期的东郡谷城县治所。据《春秋》记载,鲁庄公三十二年,曾在此建小谷城,而《左传》则认为这是为管仲所建。然而,管仲井、三归台等遗迹却现身于山北的谷邑,不禁令人困惑。两地虽相距不远,却因一山之隔,而南北归属有别。
(一)缘起:谷与小谷的歧义诞生
清道光九年(1829年),李贤书(1796年—?)在《东阿县志》的“小谷城”词条中注释道:“小谷即谷城相传已久,《通志》《兖州志》《县志》并序其名,今姑且仍之。而别录《小谷辩》于艺文卷中,俟有识者论定焉。”并且在《东阿县志·艺文卷》中,特意收录《小谷辩》《谷城非小谷辨》二文,用以辨正历史上小谷和谷的位置与归属。本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与实地考察后,认为上述两篇文章的结论总体准确。李贤书曾于清道光年间担任东阿县知县,在当地民间享有“李青天”之誉。明清以降,小谷和谷邑同隶属东阿。
据此,可笃定他对“谷”与“小谷”的争议,曾进行过深入探讨,并试图厘清二地的历史原委,给后人一个明确交代。《小谷辩》一文中写道: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左氏传》曰:“为管仲也。”盖见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而又见僖二年《经》书“城楚丘”之出于诸侯,谓仲父(管仲)得君之专,亦可勤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谷也。此(庄公)所城者,小谷也。《春秋》有言“谷”,不言“小”者。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谷”;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成公三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范宁曰:“小谷,鲁地。”然则“城小谷”者,内城也,故不系之齐,而与管仲无与也。
顾炎武认为,齐之邑城名“谷”,鲁之邑城名“小谷”。鲁庄公(公元前706年—公元前662年)在其领土上筑邑,何为邻国卿相管仲建城。此外,顾炎武指出,“按《水经》所记,狼溪、西流二水与今不同。岂当时谷城在溪东岸,自后魏至今千有馀年,陵谷变迁,不可胜原矣。”事实上,谷城位于济水之东。综上,可证实在“谷”与“小谷”的位置与归属问题上《左传》存在记述偏误。尽管张宗良将“谷邑”误作“谷城”,但在“谷”与“小谷”的问题上论述相对准确。他指出:“谷城(误,应作谷邑)、小谷,划然两地,迥不相及也。”谷城(误,应作谷邑)即“鲁庄公七年,文姜会齐之谷”。杜预注曰:“齐地。”程氏迥亦云:“在济北,有管仲井。”以上记述是正确的,但同时指出,“杜氏乃从《左氏》,以鲁之小谷为齐之谷城(谷邑),不亦诬乎?”因此,杜预诡辩曰,“公感齐桓之德,故为管仲城私邑。”
本文认为,若鲁庄公仅为感念齐桓公之恩德,修建小谷城,赠予管仲作为封邑,从逻辑上似乎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左传》中有提到,齐桓公为管仲“城谷”作为食邑,此处言“谷”而非“小谷”。如果上述论断成立,又可理解为鲁庄公在小谷建城,后割地予齐,而齐桓公又将此地作为食邑赐予管仲。显然,这中间略去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增加了考证的难度。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的“邑”有不同规格,“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由此可见,当时小谷的地位略高于谷邑。此外,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拜相(时约三十八岁),其食邑应为此后获封。鲁庄公三十二年,管仲已年过花甲,而鲁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70年)秋至齐国迎娶哀姜。八年后,即鲁庄公三十二年八月去世。可见“城小谷”时,鲁庄公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不可能在此时贸然为管仲建城。这一点在《左传》中已明确指出,“小谷”为鲁庄公所建,而谷邑则位于齐国境内。正因有上述种种变化,后人常常混淆使用,至今仍未辨明。
《后汉书》记载:“谷城,春秋时小谷,有雋下聚。”杜预则注曰:“城中有管仲井。”然而,管仲井所在地是谷邑,而非谷城县。清代人高士奇认为“齐自有谷,非鲁之小谷”。足可见,数百年后的杜预并未厘清谷城的位置不在谷邑而在小谷的实情,从而混淆了谷城、谷邑和小谷三处地名的区位差异。
《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申无宇在与鲁昭公的对话中提到“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即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2年),齐桓公在谷地建城,安置管仲。这与此前《春秋》中“城小谷”和《左传》中“为管仲也”相悖。但通过对时间和事件分析,可清晰地分辨出前者记载可信,且合乎逻辑。在此仅说明左丘明将谷邑和小谷当作同一地方。而杜预推测道:“公感齐桓之德,故为管仲城私邑。”则与此记载大意相反。显然,杜预遵循《左传》的逻辑,加以引申,强化了偏误。事实上,鲁庄公并未给管仲建城,而是在鲁国的领地上筑邑。综上可见,当鲁庄公在小谷建城时,小谷的影响力已比此前的谷邑有所增强,或为鲁庄公大限将至前的有意为之,将小谷打造成鲁国御齐的前哨重镇。
究其原委,把小谷与谷混同一地,根源在于左丘明未能清楚地交代两地的位置与关联。
当然,后世的注释者也难脱其咎。杜预在引用并注释时,直接将小谷误作谷邑,并加入了个人主观臆测。杜预因著有《春秋经传集解》而被后世称作“注释《春秋》第一人”,后世读史多以此为参照,故而容易导致以讹传讹的乱象。例如,乐史援引《郡国志》,认为谷城即管仲的封邑,并以“城内有夫子五冢”作为依据。顾祖禹在未实地调查的情况下,直接将谷邑与小谷、谷城混为一谈,令后人更加难以分辨。但是,范宁在《春秋谷梁传》中注释道:“小谷,鲁邑。”但真正注意到此细节者不多。
如今,东阿镇已划归平阴县。本文研究者多次查阅平阴县的地方学者撰写与东阿镇的相关文字时发现,他们认为“谷”即管仲食邑,又名小谷,也是秦汉时期的谷城县和明清时期的东阿县城。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将小谷、谷城和谷邑的地名彻底辨析清楚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丑闻:谷地与浪漫的另一面
《左传》和张宗良的文章中都提到一个典故,即“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的故事。此处的“夫人姜氏”指文姜(?—公元前673年),姜姓,齐僖公(?—公元前698年)之女,齐襄公(?—公元前686年)的异母姊妹,鲁桓公(公元前729年—公元前694年)的夫人。鲁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鲁桓公派公子挥到齐国迎娶文姜为妻,并立文姜为夫人。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文姜为鲁桓公诞下一子,因与鲁桓公同月生,故取名为同,后被立为太子。此后,文姜再度为鲁桓公生下公子友。
鲁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春,文姜和鲁桓公一同至齐,再度与齐襄公私通。鲁桓公得知此事后,怒责文姜,而文姜将此事告知齐襄公。同年四月初十,齐襄公宴请鲁桓公,将其灌醉后,派公子彭生助其上车(《春秋公羊传》中记载为齐襄公故意命公子彭生折断鲁桓公的肋骨),而鲁桓公却无故死于车中。《春秋谷梁传》中也认为是文姜与齐襄公合谋杀害了鲁桓公。鲁人对齐人言:“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因此,齐襄公杀公子彭生向鲁国赔罪。
鲁桓公死后,鲁人拥立太子同继位,是为鲁庄公。文姜暂时留在齐国,不敢返鲁。文姜长期居住于齐,后又回到鲁国,但仍常与齐襄公相会。早于“文姜会齐之谷”前,即同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换言之,在一年的春天,文姜在防邑(今费县东北)与齐襄公私会,而同年冬天两人又在谷邑私会。在此提到的“谷”,即后来成为管仲封地的谷邑,而此时尚未有小谷城。因为文姜与齐襄公的这次私会,谷邑也成为古代爱情的见证地之一,但这一浪漫的行为既僭越了家国政治,又违背了人伦礼法。为此,这一过度的浪漫并未像“牛郎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般在民间广为传颂,反而被钉在了“浪漫的阴面”,被后世史家视作淫乐乱政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