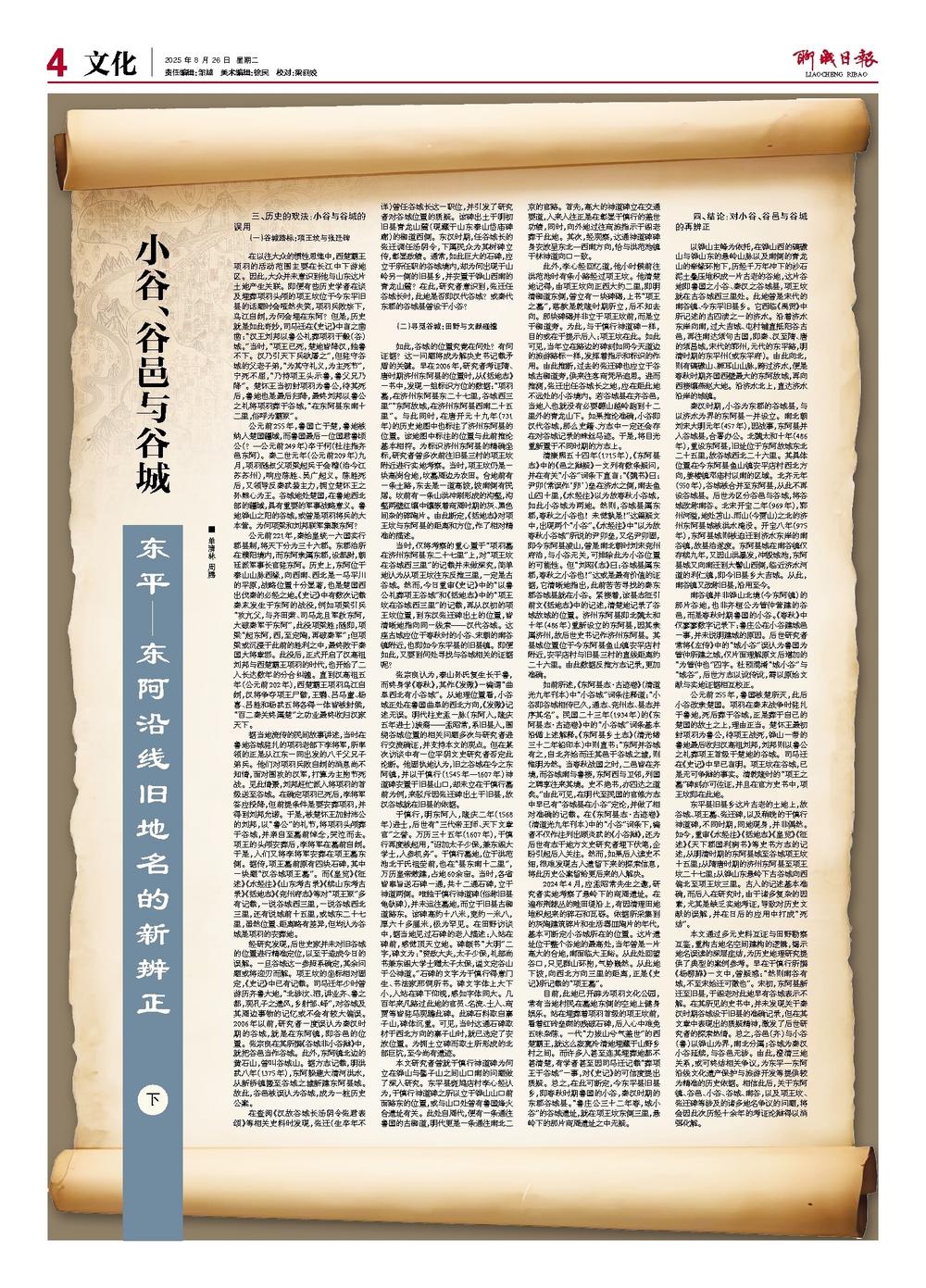小谷、谷邑与谷城 东平—东阿沿线旧地名的新辨正(下)
■ 单清林 周腾
三、历史的戏法:小谷与谷城的误用
(一)谷城路标:项王坟与张迁碑
在以往大众的惯性思维中,西楚霸王项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大众并未意识到他与山东这片土地产生关联。即便有些历史学者在谈及埋葬项羽头颅的项王坟位于今东平旧县的话题时会哑然失笑,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为何会埋在东阿?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司马迁在《史记》中言之凿凿:“汉王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于毂(谷)城。”当时,“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但驻守谷城的父老子弟,“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宁死不屈,“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楚怀王当初封项羽为鲁公,待其死后,鲁地也是最后归降,最终刘邦以鲁公之礼将项羽葬于谷城,“在东阿县东南十二里,俗呼为霸冢”。
公元前255年,鲁国亡于楚,鲁地被纳入楚国疆域,而鲁国最后一位国君鲁顷公(?—公元前249年)卒于柯(杜注指齐邑东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项羽随叔父项梁起兵于会稽(治今江苏苏州),响应陈胜、吴广起义。陈胜死后,又领导反秦武装主力,拥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谷城地处楚国,在鲁地西北部的疆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鲁地铧山之阳的谷城,或曾是项羽将兵的大本营。为何项梁和刘邦联军集聚东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东郡治所在濮阳境内,而东阿隶属东郡,设都尉,朝廷派军事长官驻东阿。历史上,东阿位于泰山山脉西缘,向西南、西北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战略位置十分显著,也是楚国西出伐秦的必经之地。《史记》中有数次记载秦末发生于东阿的战役,例如项梁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此役项梁胜;随即,项梁“起东阿,西,至定陶,再破秦军”;但项梁或沉浸于此前的胜利之中,最终败于秦国大将章邯。此役后,正式开启了汉高祖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时代,也开始了二人长达数年的分合纠缠。直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汉将争夺项王尸骸,王翳、吕马童、杨喜、吕胜和杨武五将各得一体皆被封侯,“百二秦关终属楚”之功业最终收归汉家天下。
据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讲述,当时在鲁地谷城驻扎的项羽老部下李将军,所率领的正是从江东一同出发的八千父兄子弟兵。他们对项羽兵败自刎的消息尚不知情,面对围攻的汉军,打算为主抱节死战。见此情景,刘邦赶忙派人将项羽的首级送至谷城。在确定项羽已死后,李将军答应投降,但前提条件是要安葬项羽,并得到刘邦允诺。于是,被楚怀王加封沛公的刘邦,以“鲁公”的礼节,将项羽头颅葬于谷城,并亲自至墓前悼念,哭泣而去。项王的头颅安葬后,李将军在墓前自刎。于是,人们又将李将军安葬在项王墓东侧。据传,项王墓前原有四块石碑,其中一块题“汉谷城项王墓”。而《皇览》《征述》《水经注》《山东考古录》《续山东考古录》《括地志》《兖州府志》等对“项王冢”多有记载,一说谷城西三里,一说谷城西北三里,还有说城前十五里,或城东二十七里,虽然位置、距离略有差异,但均认为谷城是项羽的安葬地。
经研究发现,后世史家并未对旧谷城的位置进行精准定位,以至于造成今日的误解。一旦谷城这一参照系确定,其余问题或将迎刃而解。项王坟的坐标相对固定,《史记》中已有记载。司马迁年少时曾游历齐鲁大地,“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对谷城及其周边事物的记忆或不会有较大偏误。2006年以前,研究者一度误认为秦汉时期的谷城,就是在东阿镇,即谷邑的位置。张宗良在其所撰《谷城非小谷辩》中,就把谷邑当作谷城。此外,东阿镇北边的黄石山,曾叫谷城山。据方志记载,明洪武八年(1375年),东阿躲避大清河洪水,从新桥镇搬至谷城之墟新建东阿县城。故此,谷邑被误认为谷城,成为一桩历史公案。
在查阅《汉故谷城长汤阴令张君表颂》等相关史料时发现,张迁(生卒年不详)曾任谷城长这一职位,并引发了研究者对谷城位置的质疑。该碑出土于明初旧县青龙山麓(现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的御道西侧。东汉时期,任谷城长的张迁调任汤阴令,下属民众为其树碑立传,彰显政绩。通常,如此巨大的石碑,应立于所任职的谷城境内,却为何出现于山岭另一侧的旧县乡,并安置于铧山西南的青龙山麓?在此,研究者意识到,张迁任谷城长时,此地是否即汉代谷城?或秦代东郡的谷城县曾设于小谷?
(二)寻觅谷城:田野与文献碰撞
如此,谷城的位置究竟在何处?有何证据?这一问题将成为解决史书记载矛盾的关键。早在2006年,研究者考证隋、唐时期济州东阿县的位置时,从《括地志》一书中,发现一组标识方位的数据:“项羽墓,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七里,谷城西三里”“东阿故城,在济州东阿县西南二十五里”。与此同时,在唐开元十九年(731年)的历史地图中也标注了济州东阿县的位置。该地图中标注的位置与此前推论基本相符。为标识济州东阿县的精确坐标,研究者曾多次前往旧县三村的项王坟附近进行实地考察。当时,项王坟仍是一块高岗台地,坟墓周边为农田。台地前有一条土路,东去是一道高坡,坡南侧有民居。坟前有一条山洪冲刷形成的沟壑,沟壑两壁红壤中镶嵌着商周时期的灰、黑色间杂的碎陶片。由此断定,《括地志》对项王坟与东阿县的距离和方位,作了相对精准的描述。
当时,仅将考察的重心置于“项羽墓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七里”上,对“项王坟在谷城西三里”的记载并未做深究,简单地认为从项王坟往东反推三里,一定是古谷城。然而,今日重审《史记》中的“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和《括地志》中的“项王坟在谷城西三里”的记载,再从汉初的项王坟位置,到东汉张迁碑出土的位置,皆清晰地指向同一线索——汉代谷城。这座古城应位于春秋时的小谷、宋朝的南谷镇附近,也即如今东平县的旧县镇。即便如此,又要到何处寻找与谷城相关的证据呢?
张宗良认为,泰山孙氏复生长于鲁,而终身学《春秋》,其作《发微》一编谓“曲阜西北有小谷城”。从地理位置看,小谷城正处在鲁国曲阜的西北方向,《发微》记述无误。明代柱史孟一脉(东阿人,隆庆五年进士)族裔——孟昭常,系旧县人,围绕谷城位置的相关问题多次与研究者进行交流确证,并支持本文的观点。但在某次访谈中有一位平阴文史研究者否定此论断。他固执地认为,旧之谷城在今之东阿镇,并以于慎行(1545年—1607年)神道碑安置于旧县山口,却未立在于慎行墓前为例,来驳斥因张迁碑出土于旧县,故汉谷城就在旧县的依据。
于慎行,明东阿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后世有“三代帝王师、天下文章官”之誉。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于慎行再度被起用,“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于慎行墓地,位于洪范池北于氏祖茔前,也在“县东南十二里”,万历皇帝敕建,占地60余亩。当时,各省皆奉旨送石碑一通,共十二通石碑,立于神道两侧。唯独于慎行神道碑(俗称旧县龟驮碑),并未运往墓地,而立于旧县古御道路东。该碑高约十八米,宽约一米八,厚六十多厘米,极为罕见。在田野访谈中,据当地见过石碑的老人描述:人站在碑前,感觉顶天立地。碑额书“大明”二字,碑文为:“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神道。”石碑的文字为于慎行得意门生、书法家邢侗所书。碑文字体上大下小,人站在碑下仰视,感如字体同大。几百年来凡路过此地的官员、名流、士人、商贾等皆驻马观瞻此碑。此碑石料取自寨子山,碑体沉重。可见,当时这通石碑取材于西北方向的寨子山时,就已选定了安放位置。为拥土立碑而取土所形成的北部巨坑,至今尚有遗迹。
本文研究者曾就于慎行神道碑为何立在铧山与鏊子山之间山口南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东平县斑鸠店村李心经认为,于慎行神道碑之所以立于铧山山口前面路东的位置,或与山口处曾有鲁国烽火台遗址有关。此处自周代,便有一条通往鲁国的古御道,明代更是一条通往南北二京的官路。首先,高大的神道碑立在交通要道,人来人往正是在彰显于慎行的盖世功绩,同时,向外地过往商旅指示于阁老葬于此地。其次,经观察,这通神道碑碑身安放呈东北—西南方向,恰与洪范池镇于林神道向口一致。
此外,李心经回忆道,他小时候前往洪范池时有条小路经过项王坟。他清楚地记得,由项王坟向正西大约二里,即明清御道东侧,曾立有一块碑碣,上书“项王之墓”,落款是乾隆时期所立,后不知去向。那块碑碣并非立于项王坟前,而是立于御道旁。为此,与于慎行神道碑一样,目的或在于提示后人:项王坟在此。如此可见,当年立在路边的碑刻如同今天道边的旅游路标一样,发挥着指示和标识的作用。由此推断,过去的张迁碑也应立于谷城古御道旁,供来往客商凭吊追思。进而推测,张迁出任谷城长之地,应在距此地不远处的小谷境内。若谷城县在齐谷邑,当地人也就没有必要翻山越岭跑到十二里外的青龙山下。如果推论准确,小谷即汉代谷城,那么史籍、方志中一定还会存在对谷城记录的蛛丝马迹。于是,将目光重新置于不同时期的方志上。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东阿县志》中的《邑之辩疑》一文列有数条疑问,并在有关“小谷”词条下直言:“《魏书》曰:尹卯(常误作‘卵’)垒在济水之侧,南去鱼山四十里,《水经注》以为故春秋小谷城,如此小谷城为两地。然则,谷城县属东郡,春秋之小谷也!未觉孰是!”这篇疑文中,出现两个“小谷”。《水经注》中“以为故春秋小谷城”所说的尹卯垒,又名尹卯固,即今东阿县凌山,曾是南北朝时刘宋兖州府治,与小谷无关,可排除此为小谷位置的可能性。但“刘昭《志》曰:谷城县属东郡,春秋之小谷也!”这或是最有价值的证据,它清晰地指出,此前苦苦寻找的秦东郡谷城县就在小谷。紧接着,该县志征引前文《括地志》中的记述,清楚地记录了谷城故城的位置。济州东阿县即北魏太和十年(486年)重新设立的东阿县,因其隶属济州,故后世史书记作济州东阿县。其县城位置位于今东阿县鱼山镇安平店村附近,安平店村与旧县三村的直线距离约二十六里。由此数据反推方志记录,更加准确。
如前所述,《东阿县志·古迹卷》(清道光九年刊本)中“小谷城”词条注释道:“小谷即谷城相传已久,通志、兖州志、县志并序其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东阿县志·古迹卷》中的“小谷城”词条基本沿循上述解释。《东阿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中则直书:“东阿并谷城有之,自北齐始而迁其邑于谷城之墟,则惟明为然。当春秋战国之时,二邑皆在齐境,而谷城南与鲁接,东阿西与卫邻,列国之聘享往来其境。史不绝书,亦四达之道矣。”由此可见,在明代至民国的官修方志中早已有“谷城县在小谷”定论,并做了相对准确的记载。在《东阿县志·古迹卷》(清道光九年刊本)中的“小谷”词条下,编者不仅作注列出顾炎武的《小谷辩》,还为后世有志于地方文史研究者埋下伏笔,企盼引起后人关注。然而,如果后人读史不细,很难发现古人遗留下来的探索信息,将此历史公案留给更后来的人解决。
2024年4月,应孟昭常先生之邀,研究者实地考察了悬岭下的商周遗址。在遍布荆棘丛的畦田堤沿上,有因清理田地堆积起来的碎石和瓦砾。依据所采集到的灰陶建筑碎片和生活器皿陶片的年代,基本可断定小谷城所在的位置。这片遗址位于整个谷地的最高处,当年曾是一片高大的台地,南面临大王峪。从此处回望谷口,只见群山环抱,气势巍然。从此地下坡,向西北方向三里的距离,正是《史记》所记载的“项王墓”。
目前,此地已开辟为项羽文化公园,常有当地村民在墓地东侧的空地上健身娱乐。站在埋葬着项羽首级的项王坟前,看着红砖垒砌的残破石碑,后人心中难免五味杂陈。一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就这么寂寞冷清地埋藏于山野乡村之间。而许多人甚至连其埋葬地都不甚清楚,有学者甚至因司马迁记载“葬项王于谷城”一事,对《史记》的可信度提出质疑。总之,在此可断定,今东平县旧县乡,即春秋时期鲁国的小谷,秦汉时期的东郡谷城县。“鲁庄公三十二年春,城小谷”的谷城遗址,就在项王坟东侧三里,悬岭下的那片商周遗址之中无疑。
四、结论:对小谷、谷邑与谷城的再辨正
以铧山主峰为依托,在铧山西的碻磝山与铧山东的悬岭山脉以及南侧的青龙山的牵缘环抱下,历经千万年冲下的沙石泥土叠压堆积成一片古老的谷地,这片谷地即鲁国之小谷、秦汉之谷城县,项王坟就在古谷城西三里处。此地曾是宋代的南谷镇、今东平旧县乡。它西临《禹贡》中所记述的古四渎之一的济水。沿着济水东岸向南,过大吉城、屯村铺直抵阳谷古邑,再往南达须句古国,即秦、汉至隋、唐的须昌城,宋代的郓州,元代的东平路,明清时期的东平州(或东平府)。由此向北,则有碻磝山、狮耳山山脉,跨过济水,便是春秋时期齐国西壁最大的东阿故城,再向西接壤燕赵大地。沿济水北上,直达济水沿岸的城镇。
秦汉时期,小谷为东郡的谷城县,与以济水为界的东阿县一并设立。南北朝刘宋大明元年(457年),因战事,东阿县并入谷城县,合署办公。北魏太和十年(486年),重设东阿县,旧址位于东阿故城东北二十五里,故谷城西北二十六里。其具体位置在今东阿县鱼山镇安平店村西北方向,姜楼镇邓庙村以南的区域。北齐元年(550年),谷城被合并至东阿县,从此不再设谷城县。后世为区分谷邑与谷城,将谷城改称南谷。北宋开宝二年(969年),郓州河溢,地处苫山、雨山(今贾山)之北的济州东阿县城被洪水淹没。开宝八年(975年),东阿县城则被迫迁到济水东岸的南谷镇,故县治遂废。东阿县城在南谷镇仅存续九年,又因山洪暴发,冲毁城池,东阿县城又向南迁到大髻山西侧,临近济水河道的利仁镇,即今旧县乡大吉城。从此,南谷镇又改称旧县,沿用至今。
南谷镇并非铧山北境(今东阿镇)的那片谷地,也非齐桓公为管仲营建的谷邑,而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小谷。《春秋》中仅寥寥数字记录下:鲁庄公在小谷建城邑一事,并未说明建城的原因。后世研究者常将《左传》中的“城小谷”误认为鲁国为管仲所建之城,仅片面理解原文后增加的“为管仲也”四字。杜预混淆“城小谷”与“城谷”,后世方志以讹传讹,需以原始文献与实地证据相互校正。
公元前255年,鲁国被楚所灭,此后小谷改隶楚国。项羽在秦末战争时驻扎于鲁地,死后葬于谷城,正是葬于自己的楚国的故土之上,理由正当。楚怀王最初封项羽为鲁公,待项王战死,铧山一带的鲁地最后收归汉高祖刘邦,刘邦则以鲁公之礼葬项王首级于楚地的谷城。司马迁在《史记》中早已言明。项王坟在谷城,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清乾隆时的“项王之墓”碑刻亦可佐证,并且在官方史书中,项王坟即在此地。
东平县旧县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故谷城、项王墓、张迁碑,以及稍晚的于慎行神道碑,不同时期,同地现身,并非偶然。如今,重审《水经注》《括地志》《皇览》《征述》《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史书方志的记述,从明清时期的东阿县城至谷城项王坟十五里;从隋唐时期的济州东阿县至项王坟二十七里;从铧山东悬岭下古谷城向西偏北至项王坟三里。古人的记述基本准确,而后人在研究时,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尤其是缺乏实地考证,导致对历史文献的误解,并在日后的应用中打成“死结”。
本文通过多元史料互证与田野勘察互鉴,重构古地名空间建构的逻辑,揭示地名误读的深层症结,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参考。早在于慎行所撰《杨柳辨》一文中,曾疑惑:“然则南谷有城,不至宋始迁可徵也”。宋初,东阿县新迁至旧县,于阁老对此地早有谷城表示不解。在其所见的史书中,并未发现关于秦汉时期谷城设于旧县的准确记录,但在其文章中表现出的质疑精神,激发了后世研究者的探索热情。总之,谷邑(齐)与小谷(鲁)以铧山为界,南北分属;谷城为秦汉小谷延续,与谷邑无涉。由此,澄清三地关系,或可终结相关争议,为东平—东阿沿线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等提供较为精准的历史依据。相信此后,关于东阿镇、谷邑、小谷、谷城、南谷,以及项王坟、张迁碑等涉及的诸多地名争议的问题,将会因此次历经十余年的考证论辩得以消弭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