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烟火是人家
——读李遵宪诗集《火焰的悲欢》有感
聊城 王梅芳
读李遵宪老师的诗,于我而言称得上一种新奇的体验。我读过许多诗,激昂的、沉静的、华丽的、淡雅的,但这部《火焰的悲欢》却是不同的。阅读时,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奇异而诡谲:一半是绿油油的麦田,阳光耀眼,田埂上有人坐着,咂巴了一口旱烟;另一半阴云密布,有闪电撕裂长空,下方的大地沉默而凝重,闪烁着蓝幽幽的火苗,和天上的银链遥遥对应。二者合在一起,像是无声的对抗与联合。
苦难,是我阅读时最直观的感受。我们似乎并不善于表达苦难,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咬牙承受并绝口不提才是对苦难的一贯态度。但诗人不会如此,雪莱说:“最为不幸的人被苦难抚育成了诗人,他们把从苦难中学到的东西用诗歌教给别人。”李遵宪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在《人,或者自然》一诗中写到:“唯有黄连,像人一样拖着庞大的根系,带着满腔的苦衷,走了很远的路途。”也许这就表明了他的态度——苦难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兴许还是人生的真谛,而与“苦”相伴前行,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诗人从不回避苦难,相反,他平静、客观且长久地记录着苦难。
这种“苦”首先来自故乡。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乡下,灵魂也属于乡村的少年,离开家乡到城市打拼,乡土与城市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我在光明照耀的地方,看到围拢而来的飞蛾和螟虫/这些在城市的余温里求生的生灵,惊恐地靠在一起/像是城市给了它们难言的恩情。”
这之中难免夹杂着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痛苦。也许是至亲的离世,也许更重一些,重得像一个时代的苦难郁积,重到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背负。不论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还是小家庭中的一声悲号,皆是绕不开、躲不了的山一般沉重的“不易”。
诗歌构建起的精神世界,能以体恤式的温柔,消解自身的苦难。所以诗人书写苦难,却并未沉溺其中,相反,他始终满怀希望与感激,从中汲取营养,化作深情的颂歌。
他歌颂生长的黄土地,歌颂菜地与麦田,歌颂故去的古老岁月。他歌颂顽强不屈的生命,歌颂生生不息的传承。他也始终热爱着生活,“活着,没有一件事是无辜的,哪怕阳光下的/或者阴影中隐藏的部分,哪怕听懂了哑巴的一个简单的手势/或者理解了一个乞丐无意的抚摸/都是化解生活枯萎的勋章”。
于李遵宪老师而言,诗歌是他认识生活、表达生活并体谅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不由思考起“诗人”这一角色的特性与使命:他当有敏锐的感知、刻骨的尊严,要拥有真实的记录、永不停止的思考和永不灭绝的希望,当然还要有一份诗心和一点天分。诗人始终是要有探寻自我的追求与社会责任感的。他们观察、理解世界,也被世界所观察。诗人在《我未曾经历的平静》一诗中写道:“当世界的一切都能够平静如初,我还有什么可歌颂的呢。”所以在未抵达世界的平静之前,诗人需要去记录,去歌颂,去揭示困窘与灾难,去歌颂美好与自由。
李遵宪老师的诗中总是写到光,他的诗就像他经常描写的火焰与闪电一样,拷问自己的灵魂,也拷问世界的灵魂。它是历史,也是指引,是东方的燧人氏或者西方的普罗米修斯,都是传递和守护的存在,是真实而客观的美,是每一个滚烫挣扎的灵魂,也是热烈奔腾的人世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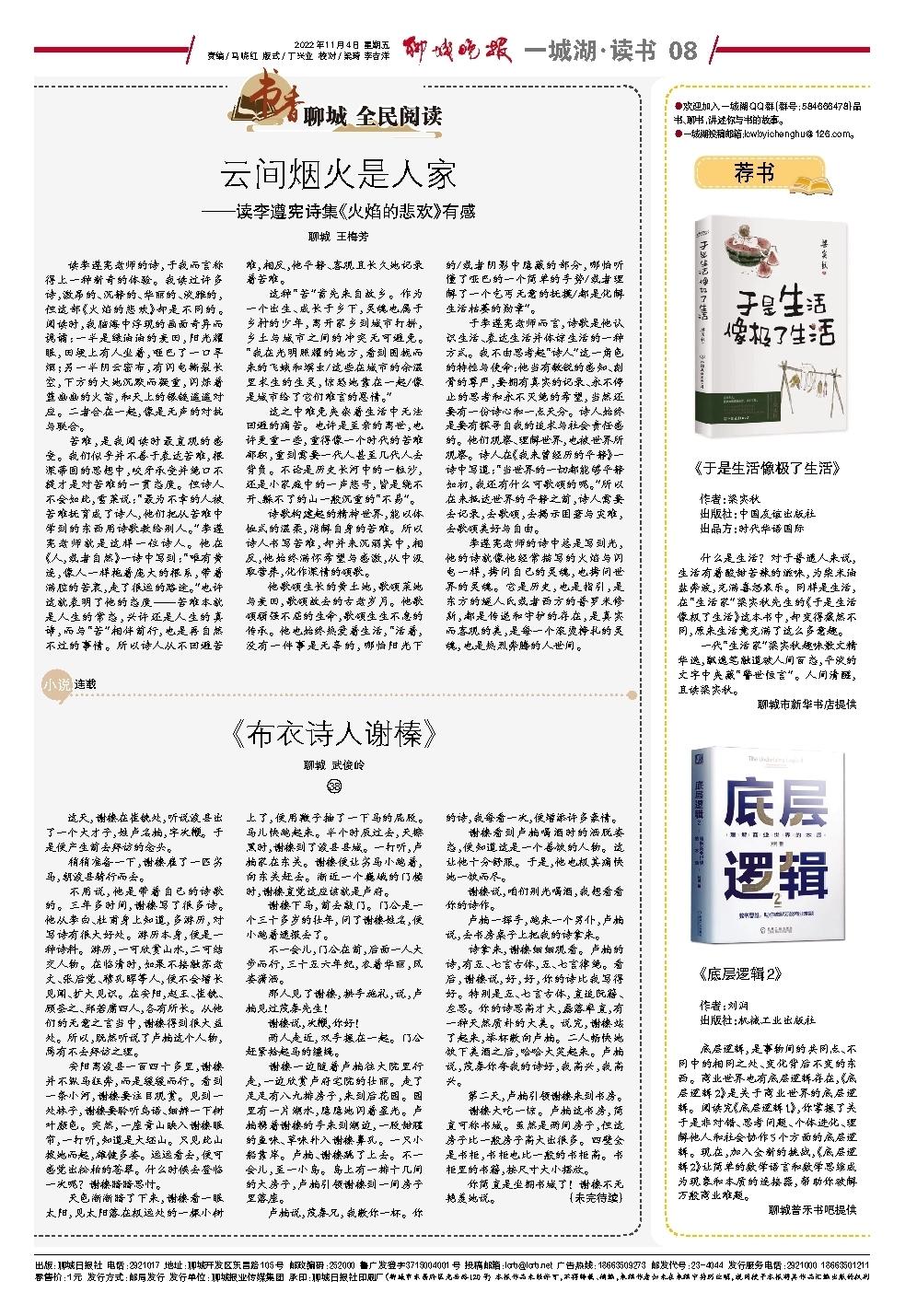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