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畔书声朗
■ 李晶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大运河畔的聊城一中学习生活了整整38年。几年前,虽搬离了一中家属院,但是每日从闸口沿着运河去往校园,不管是骑着自行车穿过四季风景,慢悠悠地行驶在河岸的青石板路上,还是沿着岸上绿化带中弯曲的小径拾级而下,从河边垂柳轻拂的石板路上一边细数每一道波纹的来历,一边步行到达校园,总有朗朗书声在耳边响起。
河道里的读书声
1990年运河河道里的读书声将我送进了大学校园。
1983年初秋,当考上初中的我骑着爷爷买的那辆只有车轮、车座、车把和脚踏板的自行车,沿着一条干涸的河流从疙疙瘩瘩的泥土路到聊城一中大门口,伸出左脚用鞋底在前车轮上摩擦使其慢下来后再跳下车时,13岁的我还不知道,这条荒滩蔓草的河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运河,也不知道,河西岸就是见证了运河漕运最繁华时期的鼎鼎大名的山陕会馆。
但这并不影响我喜欢这条河,虽然它常年没水,一到春天,河道就蓬勃生长出一丛丛野草,看起来就像是一片长条状的蜿蜒草原。也只有在雨季,草下才会有流水声,使得这河有了河的样子,可秋天一到,草下的水大多销声匿迹,只留下几个水洼还在唱着挽歌。水洼里偶尔有鱼,水边的草尖上降落着一只蜻蜓或者蝴蝶,岸上居民家的鸡,也会散步到这儿,顺便一步一伸头地觅点儿零食,在炊烟升起时还舍不得回去。放学后,总有孩子从河道里一路打闹着回家。也有人捧一本书,坐在岸边的垂柳下,或者在河道里低着头念念有词地走来走去——这些都是高中生,他们做的事和我们这些初中生没有关系。我们只觉得这条河适合我们偶尔来疯玩,或者干脆就是两岸之间的第三条路。
20世纪80年代,这条河就在时光里荒芜着,甚至在两岸居民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里持续散发着别样味道。可是,等我上了高三,却发现这是一处难得的学习胜地。
尤其是夏天,天亮得早,外面也比较凉快。起来之后匆匆洗漱一下,拿本书就从一中西院的宿舍里跑出来,顺着倾斜的河岸下去,在河道里背书。每次来,总以为已经足够早,可总有人比我更早。他们或席地而坐,低头快速地小声读,语速之快,即便仔细倾听,也很难辨析其内容;或仰头闭眼,眉头紧皱,嘴唇快速翕动,忽而又停住了,似乎在苦苦思索着什么;或背对着人站立,时而低头看书,时而仰头背诵;或蹲在地上,一手握书,一手拿着一根小树枝或者小瓦片,甚至直接用食指,边念念有词,边在河道的沙地上飞快地画来画去……我喜欢慢慢地踱着步背书,边慢慢移动脚步,边小声读、小声背,从一中桥向南走,走到前面拐弯处就转回来。背着背着,阳光就从树缝里斜射过来,照在河道蓬勃的野草和野花上,露珠闪烁着钻石一样的光芒。身上开始微微出汗了,抬头看到桥头上的早点摊上,油条和烧饼已经冒出诱人的香气,于是走过去,买根油条,又转身回到河道里,边吃边背书。等到上课将至,才带着一头细密的汗珠匆匆跑向教室。
我的历史和地理大多是在这条河道里背得滚瓜烂熟的,只是那时候没有想到,历史上著名的大运河,地理书上不得不说的大运河,就是我脚下的这一条。
现在这条河,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每天上下班都要走在这条河的河岸上,看着碧绿河水和两岸茂密的绿化树,我总会忍不住地想,这河水是怎样从历史流到了现在,河里又有多少不为我知的故事呢?
特别的图书馆
在运河西岸,聊城一中原来的西院里,有一座美国人建于清末的教堂,坐西面东,朝向运河,高大巍峨。这是一中原来的图书馆。
1983年,刚上初一不久,老师说,同学们想借什么书,就写个借条,然后由图书委员收齐后统一到图书馆去借。那时候对我来说,图书馆是个全新且神秘的存在,所以我自告奋勇,说自己身高体壮,可以帮图书委员把书抱回来。
学校通知老师说,书已经找好了,可以去抱了,于是我们几个人兴致勃勃地从教室里飞出去,飞过一中门外的小石桥,飞到图书馆前。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房子,青砖红瓦,像个城堡。一座建筑,竟然有的地方是两层,有的地方是三层,还有的地方是四层。长大以后才知道,两层的是教堂主体建筑,三层的是望楼,四层的是钟楼。但在当时,书的吸引力更大。我们跑进图书馆大门,走进房顶特别高、屋内光线昏暗的大房子里,突然之间都老实了起来,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环顾四周。一种庄严肃穆感压迫着我们。屋内很凉爽,似乎把所有强烈的阳光都隔绝在了外面,这让我觉得,我是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图书馆的老师抬起头冲我们招招手,说,书在里面,跟我来。说着,她就起身走进一道门。我们紧跟着鱼贯而入,老师指着桌子上的一堆书说,这就是你们班的,抱走吧。
我觉得遍体生凉。抬头,赫然发现在这座巨大的房子里,一排排高大的架子安静地站在昏暗中,有着一种特别的沉浮感。翕动鼻翼,一股纸张在岁月里沉淀的厚重味道弥漫开来,这是那些架子上一排一排的书散发出来的。我忍不住走到那些架子前,满怀欣喜地看着那些书,伸出手就想去触摸一下。那些书有的纸张是白色的,有的是黄色的。它们诱惑着我,像是有无数双手牵引着我。老师大声说,赶紧把书抱走了!
老师,这些书,都可以借吗?我问。
当然。看完一本还上,就可以借下一本。
我咧开嘴笑了。
回头再看这些书架子,发现有阳光穿过高高的窗户照进来,屋内明亮了一些,光线里的尘埃在欢快地跳舞。
抱着书刚出门,就有一个同学忍无可忍地把书往另一个同学手上一放,说,憋死我了,谁有纸?快点给我,我要去厕所!抓起纸就跑,好像后面有条疯狗在追。
我们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
这时候,又一个同学脸色发白地把书一放,也追随那个同学而去。
图书馆的老师看到了,也笑了,说,又有一到图书馆就想去厕所的了。
是图书馆里太阴凉了。
其实,最早的时候,在西方,教堂就是传播文化的地方,有点学校的性质,甚至一些大学就是从教堂发展而来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中把教堂作为图书馆,也算是和教堂的某些功能相契合的吧。
现在,功能更加齐全、设计更加人性化的图书馆在聊城已不少见,但是走在绿树披拂的运河大堤上,我依然会怀念那些走过运河上的小石桥到图书馆借书的日子,那些书陪伴了我38年,也将继续陪伴我,让我的每个梦里,都有朗朗书声。
(图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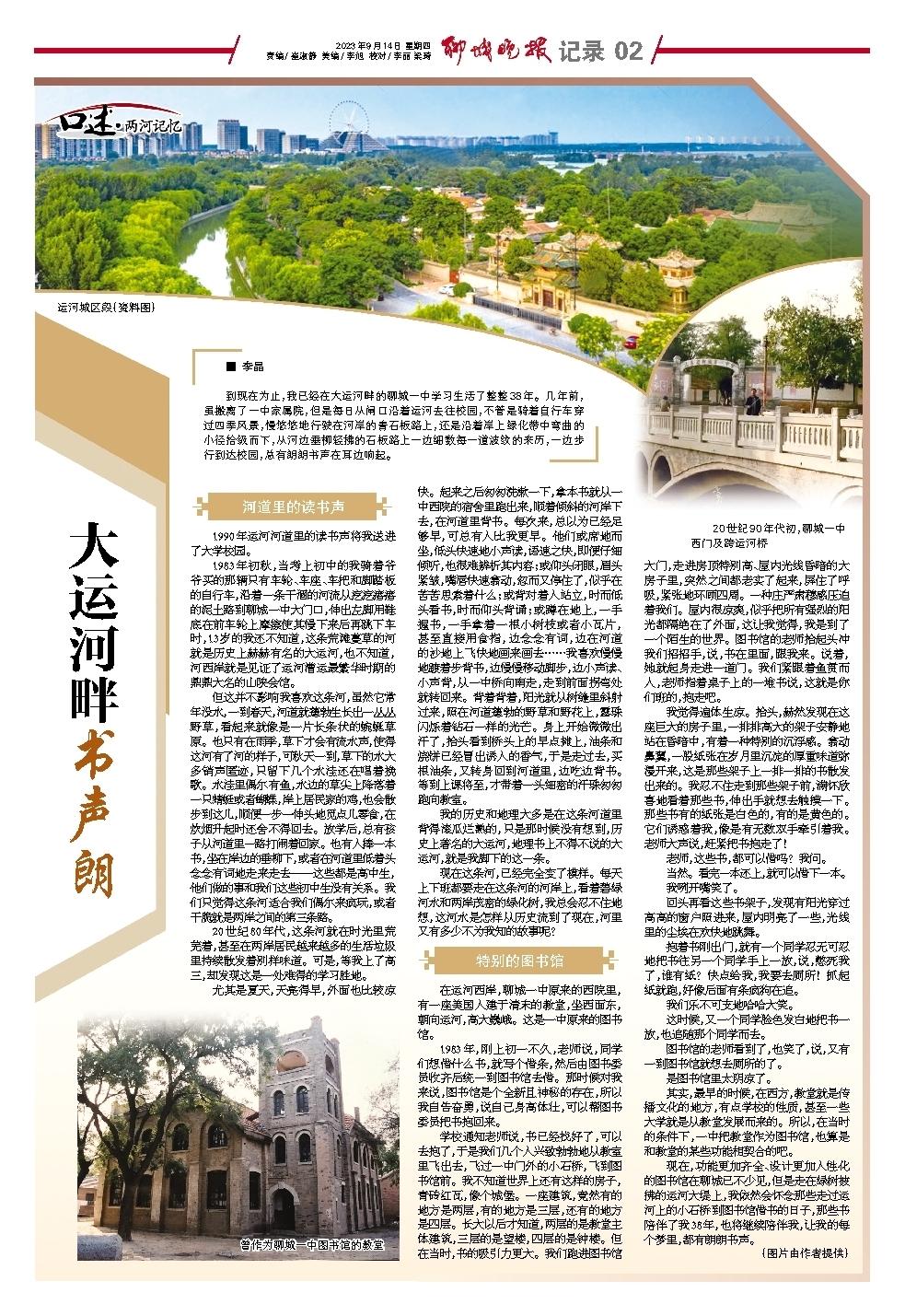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