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蝴蝶牌缝纫机
□ 耿仁国
43年前,一台缝纫机,犹如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带着爱与期待,飞进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十里井村,降临在我们家。
1981年秋,在南京长江港务局工作的大姨,帮我家买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在南京火车站通过火车货运,邮到了济南火车站。那时,还没有手机,电话也只有公社邮电局才有,通讯联系大部分靠信件。
那天中午,父亲母亲正在家里吃饭,公社邮递员骑着绿色邮政自行车到了我家门口,给我家送来一封电报。电报上说,大姨给我家购买的缝纫机已到济南火车站,叫我家人去济南取来。一家人非常高兴,决定让父亲去济南。
当时,交通还不发达,阳谷到济南的客车刚刚开通,每天仅有一班。父亲便决定骑自行车去济南。
那时,我家还没有自行车,村里有自行车的也没几家。村东张会计跟父亲关系不错,他家有一辆刚买不久的金鹿牌大轮自行车。父亲带了包大前门香烟,赔着笑脸,到张会计家借来了自行车。他准备好了钱和粮票,在自行车车把上挂上他那个黑色大提包,里边装上手电筒、捆绑缝纫机的绳子等。次日一早,父亲满怀希望,踏上了前往济南的路途。那时的他,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期待与憧憬。
我们家到济南约有二百公里的路程。那时的道路大多没有硬化,都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探险。他沿着土路,往东北方向骑行,先到阿城镇,后在东阿县城东过了黄河大桥,直奔济南。他一路感受着秋天的气息,欣赏着沿途的风景。虽然道路难走,但他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因为他知道,那台缝纫机将为家庭带来便捷与欢乐。
到达平阴县城的时候,正好遇到唱戏的,父亲在那里看戏,休息了一会儿。他走进路边一家国营饭店,交上钱和粮票,吃了顿饭。饭后他继续前行,在天黑之前进了济南城。
父亲从段店往里,边走边问,终于打听到了济南火车站的位置,可是到了那里以后,火车站的工人已经下班了。找不到人,父亲只好找了一个地方席地而坐。因为怕人偷自行车,他搂着自行车睡了一夜。
天亮了,父亲到火车站货场,找到了负责人,说明了情况。那位工作人员非常负责、非常热情,帮父亲在货场里找到了缝纫机包装箱,箱子上面贴着标签,里边就是从南京火车站发来的缝纫机。
工作人员问父亲,你带手续了吗?
父亲不知道要什么手续,说没有。
工作人员说,你没有任何手续,我没法给你,这样吧,你回去,到大队上开一封介绍信,再来取吧。
父亲无奈,叫那位工作人员写了介绍信的样式,放进提包里,骑着自行车从济南返回。
回来路上,父亲历尽艰辛。虽是秋日,太阳还是炽烈如火,他一路骑行,汗流浃背,口渴难耐。他曾在路过小村庄时,到户家讨水喝;曾在路边卖水小摊上买水喝;还曾在路边的水井里,自己打水喝……
走到东阿县城东边山路上时,不知什么原因,自行车后胎没气了,父亲只好推着前行。走了七八里路,到达一个小镇,费尽周折,找到了一家修自行车的铺子,人家一看,原来是后胎扎进了一个小铁屑。父亲叫人家补了胎,然后小心谨慎地骑行,终于回到了家。
回到家后,张会计正好有事,需要自行车,父亲就把自行车还给了他。
父亲找到大队书记,让他开了一封介绍信。稳妥起见,大队书记去公社开会的时候,又让公社加盖了一个公社公章。
但是,张会计家的自行车不能再借了,怎么办呢?父亲找到一个亲戚,说明了情况,好说歹说,借了人家的自行车,做好了第二天再去济南的准备。
夜里,明月皎洁,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钟表,不知具体时间。父亲看院子里非常明亮,以为是天亮了,就赶紧起床,洗漱完毕,带上介绍信,骑上自行车又出发了。
因为上一次走了一趟,这次,路上顺利多了。
父亲经阿城到了东阿县城,往东过了黄河大桥,进入平阴县城,又到长清,然后到了济南段店,再到济南火车站货场。工作人员收了介绍信,把缝纫机包装箱交给了父亲。
取到缝纫机包装箱,父亲如获至宝,把箱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向人家道了谢,就赶紧往家走。
出了济南,骑行在一道道山梁上,山路弯弯,父亲的心情特别愉快,特别舒畅。
到达长清县城的时候,天黑了,父亲决定不再走夜路了。
月亮升起来,父亲找了一个宾馆住下。在宾馆里,他交上粮票和钱,美美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父亲就赶紧起床,又出发了。走到黄河边的时候,一轮红日才冒出头。
下午,父亲终于回到家了,虽然疲惫,但精神抖擞。那一刻,全家人都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打开包装箱,一台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展现在眼前。
父亲按照说明书,把缝纫机安装好,脚踩踏板试了试,非常好用。村里人听说了,纷纷来看,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自从我家有了这台缝纫机,母亲给我们缝制衣服就方便多了,它工作起来,仿佛一只真正的蝴蝶在翩翩起舞,用它缝制的衣服针脚细密,线条流畅。它不仅为母亲分担了繁重的家务,更成为我们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给我们带来无尽的便利和欢乐。
如今,四十余载已过,那台缝纫机虽然不再常用,但父亲依然将其视为珍宝。他时常擦拭它,仿佛在向它诉说那些过去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父亲说,这台缝纫机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要把它永久珍藏,一代代传下去。
(图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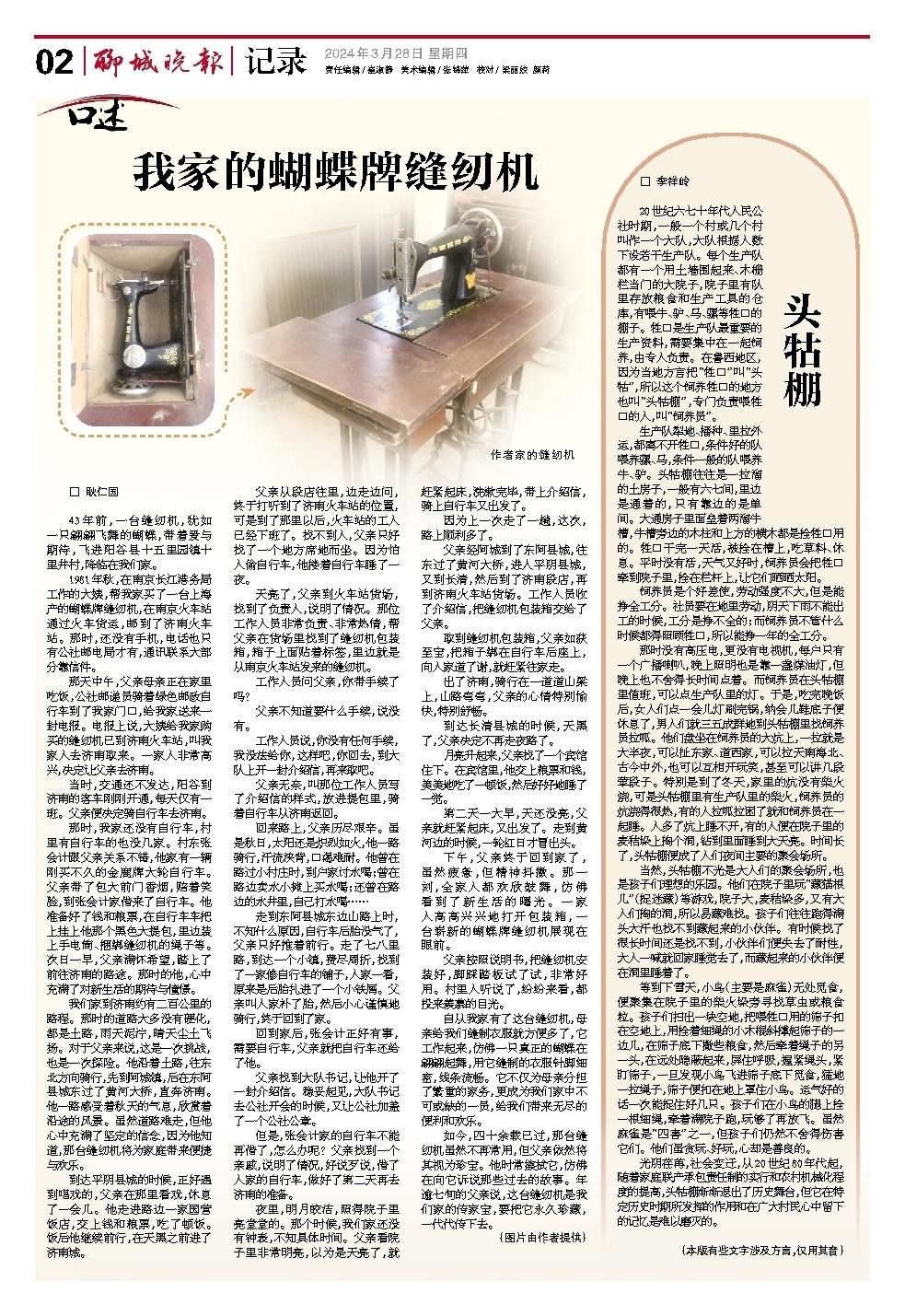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