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牯棚
□ 李祥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一般一个村或几个村叫作一个大队,大队根据人数下设若干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用土墙围起来、木栅栏当门的大院子,院子里有队里存放粮食和生产工具的仓库,有喂牛、驴、马、骡等牲口的棚子。牲口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需要集中在一起饲养,由专人负责。在鲁西地区,因为当地方言把“牲口”叫“头牯”,所以这个饲养牲口的地方也叫“头牯棚”,专门负责喂牲口的人,叫“饲养员”。
生产队犁地、播种、里拉外运,都离不开牲口,条件好的队喂养骡、马,条件一般的队喂养牛、驴。头牯棚往往是一拉溜的土房子,一般有六七间,里边是通着的,只有靠边的是单间。大通房子里面垒着两溜牛槽,牛槽旁边的木柱和上方的横木都是拴牲口用的。牲口干完一天活,被拴在槽上,吃草料、休息。平时没有活,天气又好时,饲养员会把牲口牵到院子里,拴在栏杆上,让它们晒晒太阳。
饲养员是个好差使,劳动强度不大,但是能挣全工分。社员要在地里劳动,阴天下雨不能出工的时候,工分是挣不全的;而饲养员不管什么时候都得照顾牲口,所以能挣一年的全工分。
那时没有高压电,更没有电视机,每户只有一个广播喇叭,晚上照明也是靠一盏煤油灯,但晚上也不舍得长时间点着。而饲养员在头牯棚里值班,可以点生产队里的灯。于是,吃完晚饭后,女人们点一会儿灯刷完锅,纳会儿鞋底子便休息了,男人们就三五成群地到头牯棚里找饲养员拉呱。他们盘坐在饲养员的大炕上,一拉就是大半夜,可以扯东家、道西家,可以拉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也可以互相开玩笑,甚至可以讲几段荤段子。特别是到了冬天,家里的炕没有柴火烧,可是头牯棚里有生产队里的柴火,饲养员的炕烧得很热,有的人拉呱拉困了就和饲养员在一起睡。人多了炕上睡不开,有的人便在院子里的麦秸垛上掏个洞,钻到里面睡到大天亮。时间长了,头牯棚便成了人们夜间主要的聚会场所。
当然,头牯棚不光是大人们的聚会场所,也是孩子们理想的乐园。他们在院子里玩“藏猫根儿”(捉迷藏)等游戏,院子大,麦秸垛多,又有大人们掏的洞,所以易藏难找。孩子们往往跑得满头大汗也找不到藏起来的小伙伴。有时候找了很长时间还是找不到,小伙伴们便失去了耐性,大人一喊就回家睡觉去了,而藏起来的小伙伴便在洞里睡着了。
等到下雪天,小鸟(主要是麻雀)无处觅食,便聚集在院子里的柴火垛旁寻找草虫或粮食粒。孩子们扫出一块空地,把喂牲口用的筛子扣在空地上,用拴着细绳的小木棍斜撑起筛子的一边儿,在筛子底下撒些粮食,然后牵着绳子的另一头,在远处隐蔽起来,屏住呼吸,握紧绳头,紧盯筛子,一旦发现小鸟飞进筛子底下觅食,猛地一拉绳子,筛子便扣在地上罩住小鸟。运气好的话一次能捉住好几只。孩子们在小鸟的腿上拴一根细绳,牵着满院子跑,玩够了再放飞。虽然麻雀是“四害”之一,但孩子们仍然不舍得伤害它们。他们虽贪玩、好玩,心却是善良的。
光阴荏苒,社会变迁,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头牯棚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在广大村民心中留下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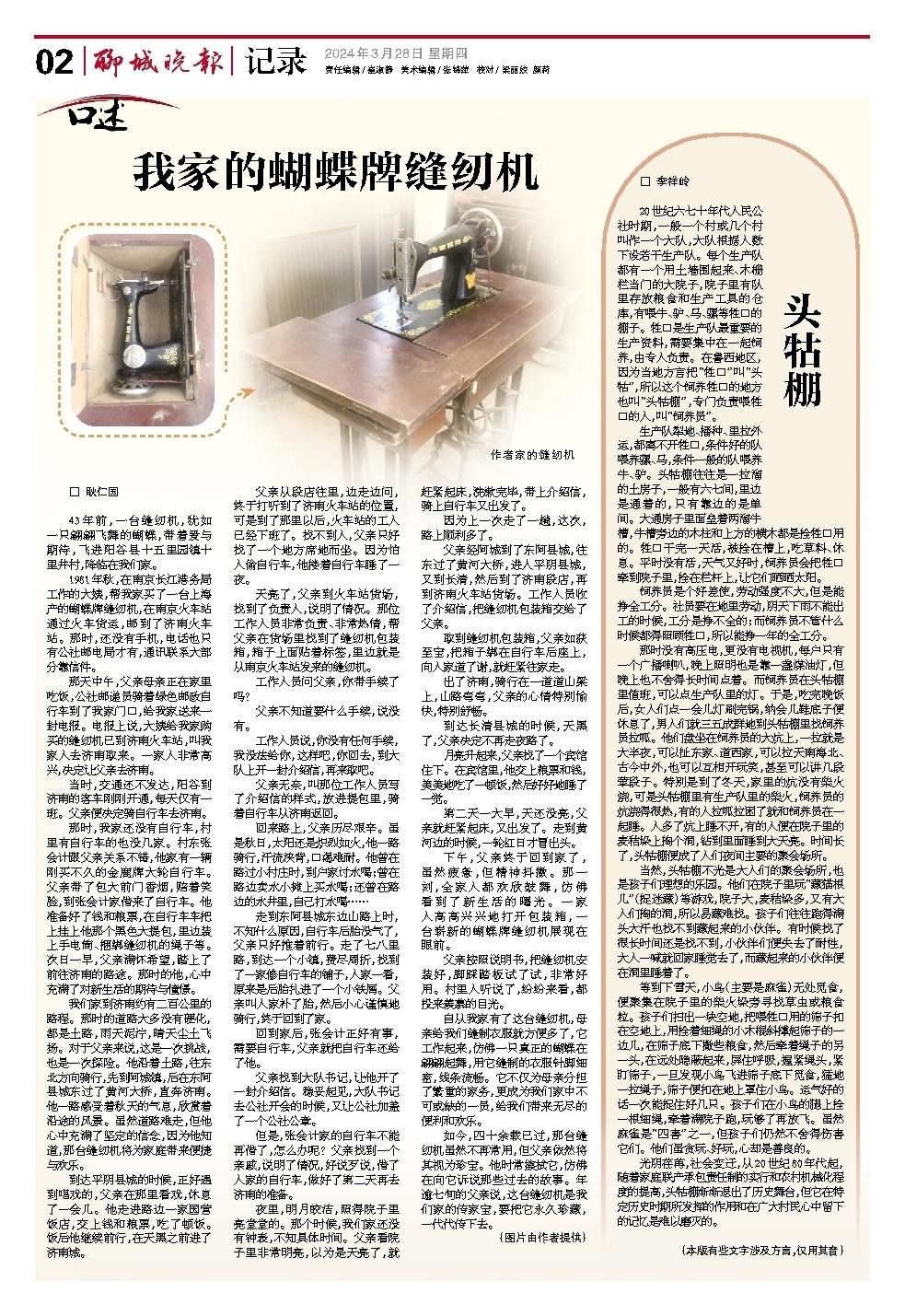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