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老灶台
○ 孙利
奶奶说:“二小,你去麦场拿一篮子麦秸,我引火用。”我很不高兴,扭着头瞪着眼,摔打着篮子,带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走出了院子。
麦秸是碾去麦粒后的麦秆。在北方小麦主产区,麦秸不仅是驴骡牲畜的主要饲料,也是建造房屋的重要材料。当然,麦秸质地松软,也可以烧火做饭,但大家都舍不得烧,只拿来引火用。
麦秸垛底小,中间大,顶部拱状,形似蘑菇。这种形状的垛子能贮存更多麦秸。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看一个村富不富,能不能吃饱饭,只需看麦秸垛的高矮。
我七岁时,奶奶便开始支使我干活,每天早晨都让我去麦场撕麦秸。麦秸是松散的,但麦秸垛上的麦秸经过叠压牵拉,形成一个整体,要撕一把还真不容易。我一根根地拽,等我拽满一篮子,回到家时,厨房顶上早已飘起了炊烟。
奶奶是个勤快人,无论冬夏,凌晨五点就起床,喂猪、喂鸡鸭,之后开始做饭。有时我也跟着起来,坐在灶台前,烤着暖暖的灶火。
奶奶左手拉动风箱,右手有节奏地往锅底添柴火。火苗像红红的舌头,不紧不慢地舔舐着锅底。我窝在一旁的柴火堆里,脸被烤得暖暖的,一会儿便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见奶奶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另一只手轻轻地拿掉我身上的柴草。
我家的灶台四四方方,是父亲用青砖砌的。灶台中间有一口大铁锅,靠墙的一面垒着烟道,一头连接灶膛,一头直通屋顶。奶奶说,父亲砌的灶台很好用,主要是因为烟道盘得好,位置正确,通风也好,这样不仅容易引火,而且节省柴火。不过,再好的灶台使用一年左右都得打理和保养,其实打理起来也简单,就是把锅揭下来,倒扣在院子里,用铲子除去锅灰,再用棍子通通烟道。
在我九岁那年,奶奶教我引火。当时,我比灶台高不了多少,奶奶站在一旁指挥:先把引火的麦秸放在灶口,然后点着火柴,慢慢靠近灶口,把火柴放在麦秸底下,用嘴吹一吹,火很快便燃着了,最后再把燃着的麦秸推进灶膛,紧接着左手慢慢拉动风箱,右手往灶膛里添柴火。我第一次引着火后,跑到院子里,看到烟道里冒出的黑烟,兴奋得又跑又跳。
过了几年,家里盖了新房,老灶台被拆除。父亲思来想去,认为还是在老地方垒个灶台比较合适。新灶台是老灶台的升级版,周身贴着光滑的瓷砖,灶台的台面也更加宽敞。年迈的奶奶和灶台打了一辈子交道,更是舍不得离开如此整洁的厨房,每顿饭都要亲自下厨。
20世纪90年代,家里陆续添置了煤气炉、电磁炉、电饭煲、电水壶等,有了这些电器,灶台逐渐闲置起来。为了充分利用空间,父亲又在灶台上放了一块木板,变成了一张大桌子。
我们逐渐长大,离开父母在外地安家。不过,每次回家相聚,奶奶都要掀开木板,重新生火。也许,奶奶认为,只有灶膛里噼里啪啦的声响才是团聚的歌谣;只有屋顶上袅袅的炊烟,才是一家人的精气神。
厨房外的小菜园里,韭菜一茬接着一茬,翠绿翠绿的;新灶台代替了老灶台,我也接过了奶奶的烧火棍,每个周末都要带着孩子回趟老家,学着奶奶的样子指挥他们。面对灶膛里的火苗,我似乎找到了家最初的模样,似乎看到了我们兄妹几个围坐在一起的样子。
奶奶一辈子爱烧灶火,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40年前奶奶吆喝我的声音:“二小,你去麦场拿一篮子麦秸,我引火用。”可惜,现在,我即使抱着麦秸,也无法送到奶奶身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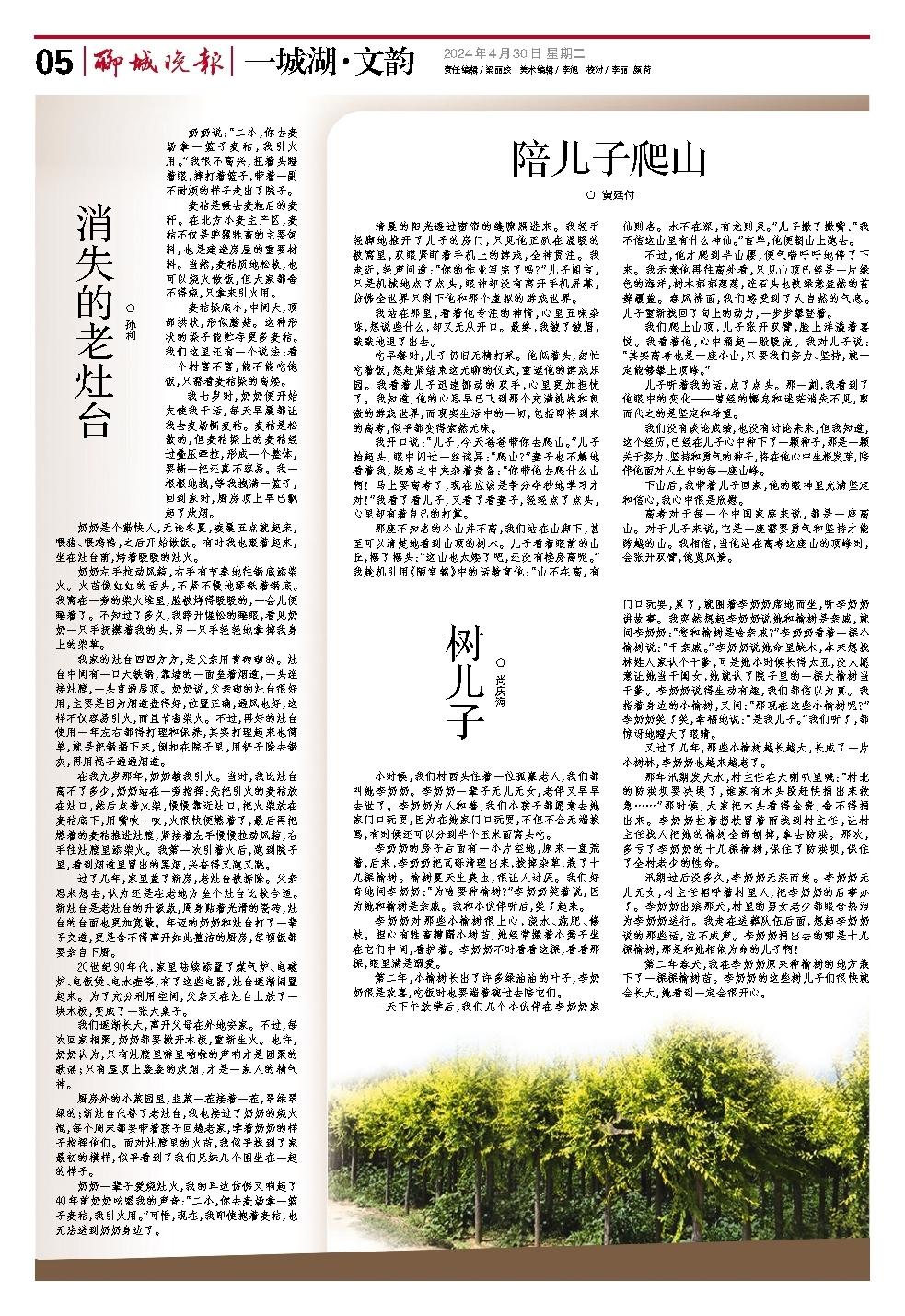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