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
□ 王栋
“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生产队,我一直对这个词怀着深厚的感情。在乡村生活过的人,那一代,有谁不知道生产队呢?”
这是作家付秀莹小说里的句子,这几句话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是70后——我记事的时候,生产队还是具体的、有形的,还有模有样。虽然我只抓住了生产队的一个尾巴,但是,我儿时的记忆,跟生产队里的那些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老家在茌平区冯官屯镇望鲁店村。当时,我们生产队除了家北、东洼、顶河、河东这几百亩土地,还有队部——队部里有油坊,以及草屋——实际上是牛棚、猪圈、场院、仓囤的统称。草屋在村外寨壕的北面,是我和小伙伴经常去的地方。我对这里充满了好奇。我记得队里有几头健壮的鲁西黄牛,腆着大肚子,脾气暴躁;还有白嘴唇的大叫驴。牛棚里弥漫着青草味、屎尿味,湿漉漉的。在草屋西头儿的几间房里,队里还养着蚕——白石灰粉刷的墙壁,白胖胖的蚕宝宝在竹匾上的桑叶堆里弓着身子。蚕室里很静,静得只听到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沙沙”声。蚕室里有一种甜甜的、腥腥的动植物混合的味道。病了的蚕宝宝则被挑拣出来,和黑色的蚕粪、残缺的桑叶梗一起被遗弃在道边。那些蚕宝宝还没有死去,它们翘着脑袋,还在寻找桑叶吃。我和小伙伴可怜它们,便把它们带回家去,喂养几天。
草屋后面是偌大的场院。夏季的麦子,秋季的棒子、红薯、高粱、大豆、棉花都集中到场院里碾轧或者晾晒。麦子收完了,一个个馒头样的麦秸垛林立在场院里,像一座座城堡;秋季,棒子秸相互依偎在一起,也成为一座城堡——这里是捉迷藏最好的藏身之处。一到冬天,场院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在这里,我们捉迷藏、打尜、跳房子……
生产队里还有菜园瓜园。菜园在东洼,离村子有三四里路。菜园里有一间小土屋,有前后两个门,这样便于观察菜园的情况。屋前是一口旱井,井口很大,站在井边往下看,不免让人心惊胆战。井壁是用大青砖垒成的,井水不算深,非常清澈,有几根柴草浮在水面,还有一两只青蛙伏在井壁,伸着长长的后腿。小伙伴投个坷垃进去,青蛙便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去了。井上面有水车,蒙着眼睛的黑驴周而复始地拉着水车,它前面的路永远没有尽头。水顺着阳沟缓缓流进韭菜地、茄子地……
瓜园好像在家北,种着甜瓜、面瓜、梢瓜。面瓜一兜儿面,瓜瓤是甜的;青甜瓜名字叫羊角蜜,又脆又甜;梢瓜,浅绿色,大的像成年人的胳膊一样粗,脆脆的、微甜,老了的则有点儿发黄,吃起来有点儿酸。现在,梢瓜不多见了。瓜熟了,队长就举着喇叭筒子喊,分瓜啦,分瓜啦,都去领瓜啊!我们小孩子耳朵尖,听到喊声就往瓜园里跑。于是瓜园的窝棚前就挤满了一排小脑袋,分瓜前,我们的口水,早已吞咽了很多。
偷瓜?那个年代的人谁没有偷过瓜呢?我的偷瓜经历在脑海里是空白的。娘笑着跟妻子讲我的偷瓜故事——打小就笨,跟小伙伴一起去偷瓜,人家都拿着一个大甜瓜,他两手空空,人家吃,他干看着。
那时,生产队在村子里还有一口水井,全队的人都去这口井里挑水。若是水桶掉到井里,就用杀猪时用的肉钩子去捞。有不懂事的孩子往井里撒尿或者拉屎,被人看到了,那个熊孩子除了挨骂,还要挨打。水脏了,全队的老少爷们就去淘井,把水一桶桶提上来,还要下去把井底的脏物清理干净。
队长是生产队的最高首领,权力的象征则是一口钟。钟声响起,是上工的号角。社员(那时人民公社还没有改名为乡镇,村民都叫社员)便在钟下集合,队长掐着腰,神气地派活儿,然后人们拿着生产工具奔赴各自的岗位。集体劳动我没有参加过——我还没有长大成人,生产队就解散了:土地包产到户,牲畜农机具拍卖给社员,草屋被扒掉,场院上多出一片红砖新居。70后成了见证生产队的最后一代——它以后改名为村民小组,以另一种身份存在,但已经不那么具体形象了。据说生产队解散时,不少人都流下了热泪。但很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让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生产队,渐渐成了遥远的回忆和背景。
有位作家说过,我们怀念一个时代,不是它有多好,而是那时我们年轻。
生产队,在我被岁月冲刷的记忆里,有它的片段。那里,住着我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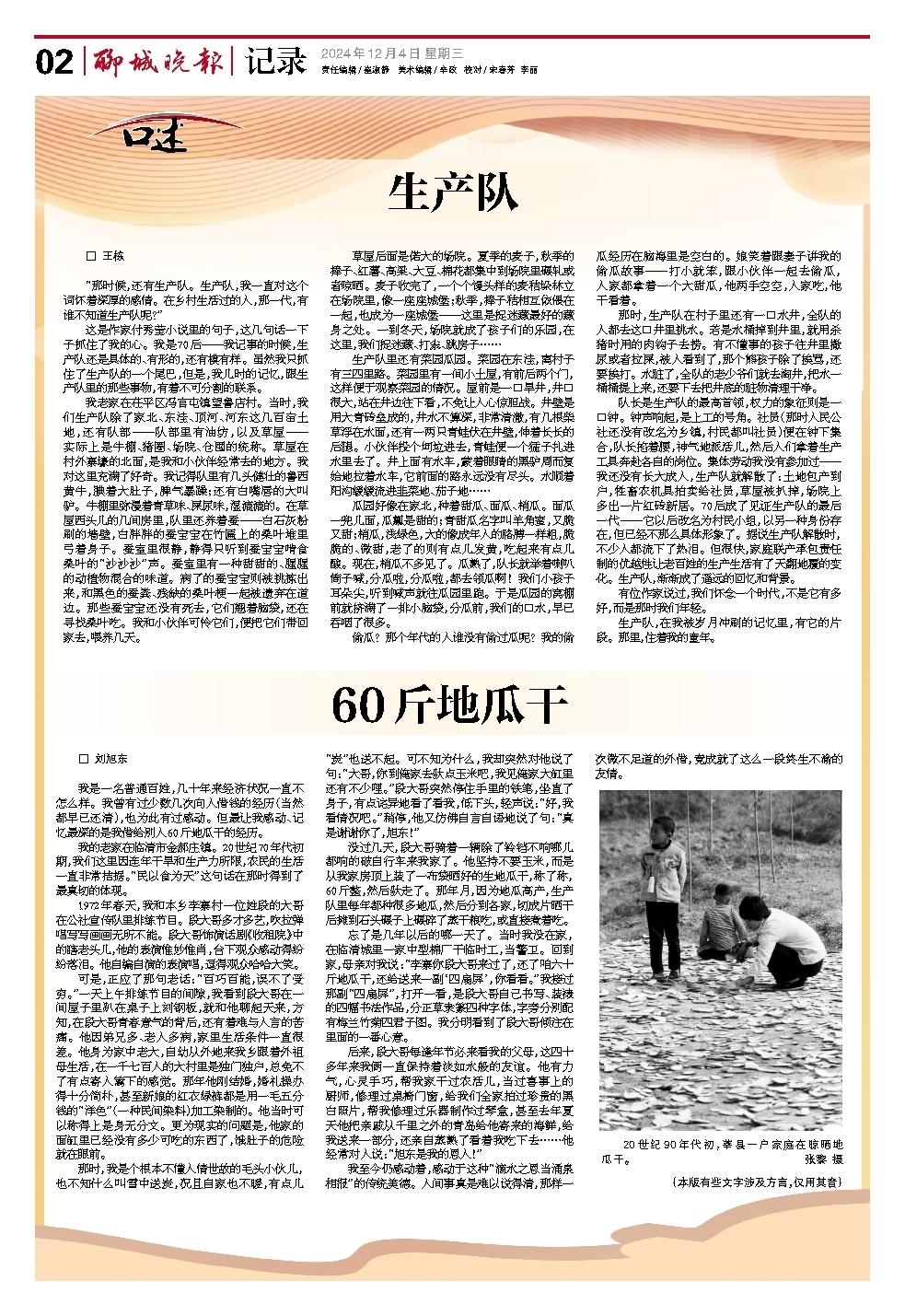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