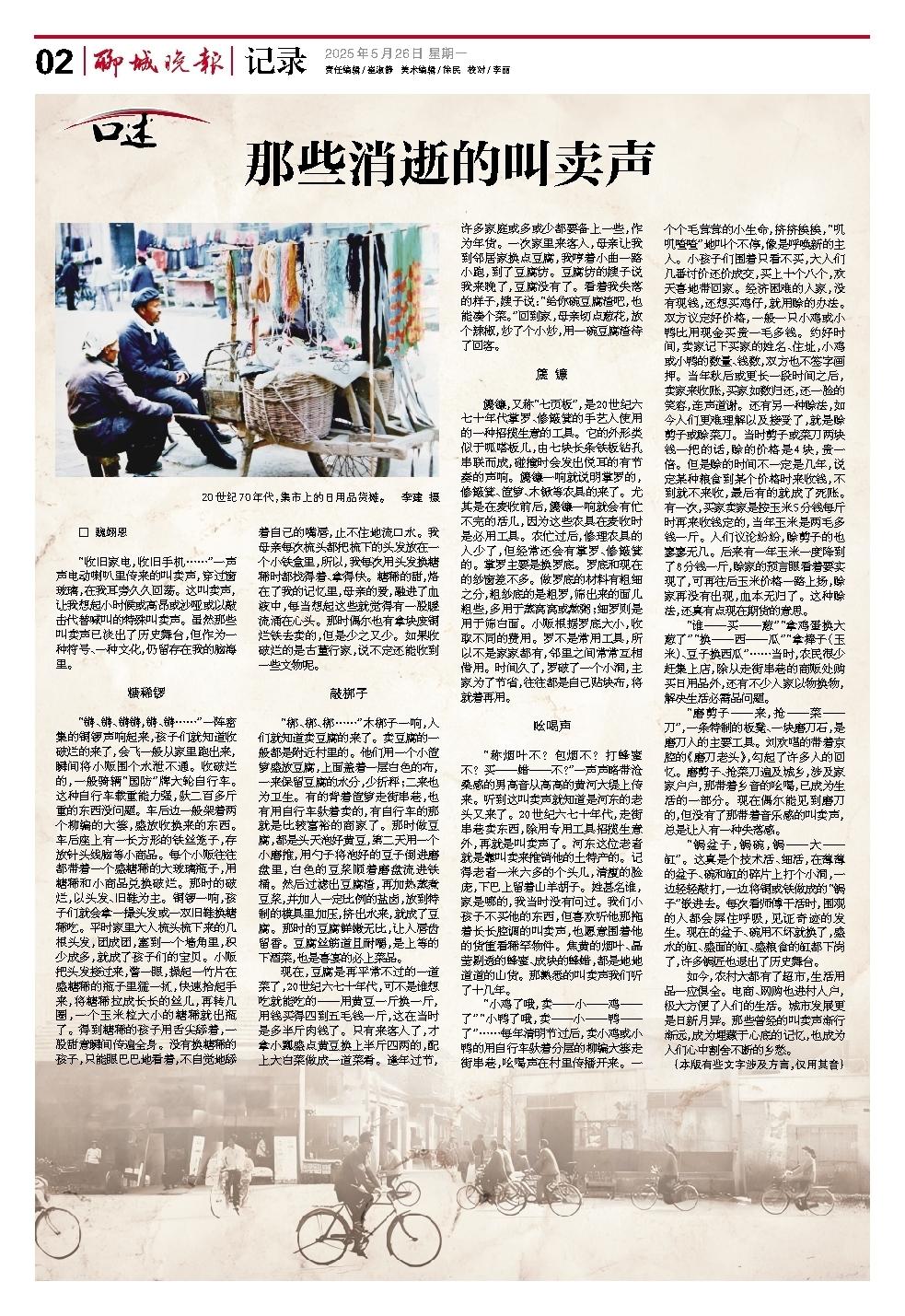那些消逝的叫卖声
□ 魏翊恩
“收旧家电,收旧手机……”一声声电动喇叭里传来的叫卖声,穿过窗玻璃,在我耳旁久久回荡。这叫卖声,让我想起小时候或高昂或沙哑或以敲击代替喊叫的特殊叫卖声。虽然那些叫卖声已淡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文化,仍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糖稀锣
“锵、锵、锵锵,锵、锵……”一阵密集的铜锣声响起来,孩子们就知道收破烂的来了,会飞一般从家里跑出来,瞬间将小贩围个水泄不通。收破烂的,一般骑辆“国防”牌大轮自行车。这种自行车载重能力强,驮二百多斤重的东西没问题。车后边一般架着两个柳编的大篓,盛放收换来的东西。车后座上有一长方形的铁丝笼子,存放针头线脑等小商品。每个小贩往往都带着一个盛糖稀的大玻璃瓶子,用糖稀和小商品兑换破烂。那时的破烂,以头发、旧鞋为主。铜锣一响,孩子们就会拿一撮头发或一双旧鞋换糖稀吃。平时家里大人梳头梳下来的几根头发,团成团,塞到一个墙角里,积少成多,就成了孩子们的宝贝。小贩把头发接过来,瞥一眼,操起一竹片在盛糖稀的瓶子里猛一,快速抬起手来,将糖稀拉成长长的丝儿,再转几圈,一个玉米粒大小的糖稀就出瓶了。得到糖稀的孩子用舌尖舔着,一股甜意瞬间传遍全身。没有换糖稀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不自觉地舔着自己的嘴唇,止不住地流口水。我母亲每次梳头都把梳下的头发放在一个小铁盒里,所以,我每次用头发换糖稀时都找得着、拿得快。糖稀的甜,烙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的爱,融进了血液中,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有一股暖流涌在心头。那时偶尔也有拿块废铜烂铁去卖的,但是少之又少。如果收破烂的是古董行家,说不定还能收到一些文物呢。
敲梆子
“梆、梆、梆……”木梆子一响,人们就知道卖豆腐的来了。卖豆腐的一般都是附近村里的。他们用一个小笸箩盛放豆腐,上面盖着一层白色的布,一来保留豆腐的水分,少折秤;二来也为卫生。有的背着笸箩走街串巷,也有用自行车驮着卖的,有自行车的那就是比较富裕的商家了。那时做豆腐,都是头天泡好黄豆,第二天用一个小磨推,用勺子将泡好的豆子倒进磨盘里,白色的豆浆顺着磨盘流进铁桶。然后过滤出豆腐渣,再加热蒸煮豆浆,并加入一定比例的盐卤,放到特制的模具里加压,挤出水来,就成了豆腐。那时的豆腐鲜嫩无比,让人唇齿留香。豆腐丝筋道且耐嚼,是上等的下酒菜,也是喜宴的必上菜品。
现在,豆腐是再平常不过的一道菜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不是谁想吃就能吃的——用黄豆一斤换一斤,用钱买得四到五毛钱一斤,这在当时是多半斤肉钱了。只有来客人了,才拿小瓢盛点黄豆换上半斤四两的,配上大白菜做成一道菜肴。逢年过节,许多家庭或多或少都要备上一些,作为年货。一次家里来客人,母亲让我到邻居家换点豆腐,我哼着小曲一路小跑,到了豆腐坊。豆腐坊的嫂子说我来晚了,豆腐没有了。看着我失落的样子,嫂子说:“给你碗豆腐渣吧,也能凑个菜。”回到家,母亲切点葱花,放个辣椒,炒了个小炒,用一碗豆腐渣待了回客。
篪 镰
篪镰,又称“七页板”,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掌罗、修簸箕的手艺人使用的一种招揽生意的工具。它的外形类似于呱嗒板儿,由七块长条铁板钻孔串联而成,碰撞时会发出悦耳的有节奏的声响。篪镰一响就说明掌罗的,修簸箕、笸箩、木锨等农具的来了。尤其是在麦收前后,篪镰一响就会有忙不完的活儿,因为这些农具在麦收时是必用工具。农忙过后,修理农具的人少了,但经常还会有掌罗、修簸箕的。掌罗主要是换罗底。罗底和现在的纱窗差不多。做罗底的材料有粗细之分,粗纱底的是粗罗,筛出来的面儿粗些,多用于蒸窝窝或熬粥;细罗则是用于筛白面。小贩根据罗底大小,收取不同的费用。罗不是常用工具,所以不是家家都有,邻里之间常常互相借用。时间久了,罗破了一个小洞,主家为了节省,往往都是自己贴块布,将就着再用。
吆喝声
“称烟叶不?包烟不?打蜂蜜不?买——蜡——不?”一声声略带沧桑感的男高音从高高的黄河大堤上传来。听到这叫卖声就知道是河东的老头又来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街串巷卖东西,除用专用工具招揽生意外,再就是叫卖声了。河东这位老者就是靠叫卖来推销他的土特产的。记得老者一米六多的个头儿,清瘦的脸庞,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姓甚名谁,家是哪的,我当时没有问过。我们小孩子不买他的东西,但喜欢听他那拖着长长腔调的叫卖声,也愿意围着他的货筐看稀罕物件。焦黄的烟叶、晶莹剔透的蜂蜜、成块的蜂蜡,都是地地道道的山货。那熟悉的叫卖声我们听了十几年。
“小鸡了哦,卖——小——鸡——了”“小鸭了哦,卖——小——鸭——了”……每年清明节过后,卖小鸡或小鸭的用自行车驮着分层的柳编大篓走街串巷,吆喝声在村里传播开来。一个个毛茸茸的小生命,挤挤挨挨,“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像是呼唤新的主人。小孩子们围着只看不买,大人们几番讨价还价成交,买上十个八个,欢天喜地带回家。经济困难的人家,没有现钱,还想买鸡仔,就用赊的办法。双方议定好价格,一般一只小鸡或小鸭比用现金买贵一毛多钱。约好时间,卖家记下买家的姓名、住址,小鸡或小鸭的数量、钱数,双方也不签字画押。当年秋后或更长一段时间之后,卖家来收账,买家如数归还,还一脸的笑容,连声道谢。还有另一种赊法,如今人们更难理解以及接受了,就是赊剪子或赊菜刀。当时剪子或菜刀两块钱一把的话,赊的价格是4块,贵一倍。但是赊的时间不一定是几年,说定某种粮食到某个价格时来收钱,不到就不来收,最后有的就成了死账。有一次,买家卖家是按玉米5分钱每斤时再来收钱定的,当年玉米是两毛多钱一斤。人们议论纷纷,赊剪子的也寥寥无几。后来有一年玉米一度降到了8分钱一斤,赊家的预言眼看着要实现了,可再往后玉米价格一路上扬,赊家再没有出现,血本无归了。这种赊法,还真有点现在期货的意思。
“谁——买——葱”“拿鸡蛋换大葱了”“换——西——瓜”“拿棒子(玉米)、豆子换西瓜”……当时,农民很少赶集上店,除从走街串巷的商贩处购买日用品外,还有不少人家以物换物,解决生活必需品问题。
“磨剪子——来,抢——菜——刀”,一条特制的板凳、一块磨刀石,是磨刀人的主要工具。刘欢唱的带着京腔的《磨刀老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磨剪子、抢菜刀遍及城乡,涉及家家户户,那带着乡音的吆喝,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偶尔能见到磨刀的,但没有了那带着音乐感的叫卖声,总是让人有一种失落感。
“锔盆子,锔碗,锔——大——缸”。这真是个技术活、细活,在薄薄的盆子、碗和缸的碎片上打个小洞,一边轻轻敲打,一边将铜或铁做成的“锔子”嵌进去。每次看师傅干活时,围观的人都会屏住呼吸,见证奇迹的发生。现在的盆子、碗用不坏就换了,盛水的缸、盛面的缸、盛粮食的缸都下岗了,许多锔匠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农村大都有了超市,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电商、网购也进村入户,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城市发展更是日新月异。那些曾经的叫卖声渐行渐远,成为埋藏于心底的记忆,也成为人们心中割舍不断的乡愁。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