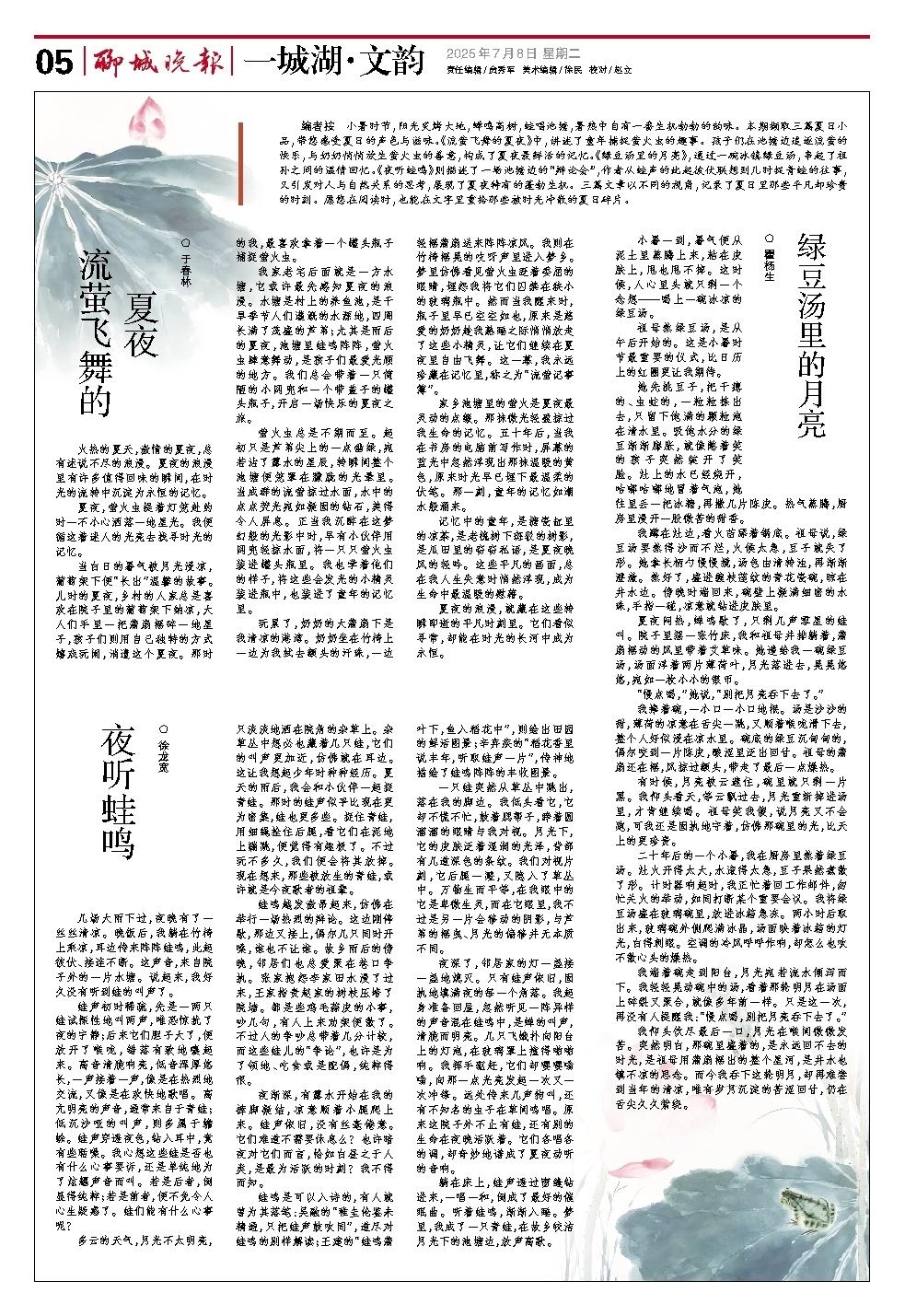绿豆汤里的月亮
○ 瞿杨生
小暑一到,暑气便从泥土里蒸腾上来,粘在皮肤上,甩也甩不掉。这时候,人心里头就只剩一个念想——喝上一碗冰凉的绿豆汤。
祖母熬绿豆汤,是从午后开始的。这是小暑时节最重要的仪式,比日历上的红圈更让我期待。
她先挑豆子,把干瘪的、虫蛀的,一粒粒拣出去,只留下饱满的颗粒泡在清水里。吸饱水分的绿豆渐渐膨胀,就像憋着笑的孩子突然绽开了笑脸。灶上的水已经烧开,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她往里丢一把冰糖,再撒几片陈皮。热气蒸腾,厨房里漫开一股微苦的甜香。
我蹲在灶边,看火苗舔着锅底。祖母说,绿豆汤要熬得沙而不烂,火候太急,豆子就失了形。她拿长柄勺慢慢搅,汤色由清转浊,再渐渐澄澈。熬好了,盛进缠枝莲纹的青花瓷碗,晾在井水边。傍晚时端回来,碗壁上凝满细密的水珠,手指一碰,凉意就钻进皮肤里。
夏夜闷热,蝉鸣歇了,只剩几声零星的蛙叫。院子里摆一张竹床,我和祖母并排躺着,蒲扇摇动的风里带着艾草味。她递给我一碗绿豆汤,汤面浮着两片薄荷叶,月光落进去,晃晃悠悠,宛如一枚小小的银币。
“慢点喝,”她说,“别把月亮吞下去了。”
我捧着碗,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汤是沙沙的甜,薄荷的凉意在舌尖一跳,又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人好似浸在凉水里。碗底的绿豆沉甸甸的,偶尔咬到一片陈皮,酸涩里泛出回甘。祖母的蒲扇还在摇,风掠过额头,带走了最后一点燥热。
有时候,月亮被云遮住,碗里就只剩一片黑。我仰头看天,等云飘过去,月光重新掉进汤里,才肯继续喝。祖母笑我傻,说月亮又不会跑,可我还是固执地守着,仿佛那碗里的光,比天上的更珍贵。
二十年后的一个小暑,我在厨房里熬着绿豆汤。灶火开得太大,水滚得太急,豆子果然煮散了形。计时器响起时,我正忙着回工作邮件,匆忙关火的举动,如同打断某个重要会议。我将绿豆汤盛在玻璃碗里,放进冰箱急冻。两小时后取出来,玻璃碗外侧爬满冰晶,汤面映着冰箱的灯光,白得刺眼。空调的冷风呼呼作响,却怎么也吹不散心头的燥热。
我端着碗走到阳台,月光宛若流水倾泻而下。我轻轻晃动碗中的汤,看着那轮明月在汤面上碎裂又聚合,就像多年前一样。只是这一次,再没有人提醒我:“慢点喝,别把月亮吞下去了。”
我仰头饮尽最后一口,月光在喉间微微发苦。突然明白,那碗里盛着的,是永远回不去的时光,是祖母用蒲扇摇出的整个星河,是井水也镇不凉的思念。而今我吞下这轮明月,却再难尝到当年的清凉,唯有岁月沉淀的苦涩回甘,仍在舌尖久久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