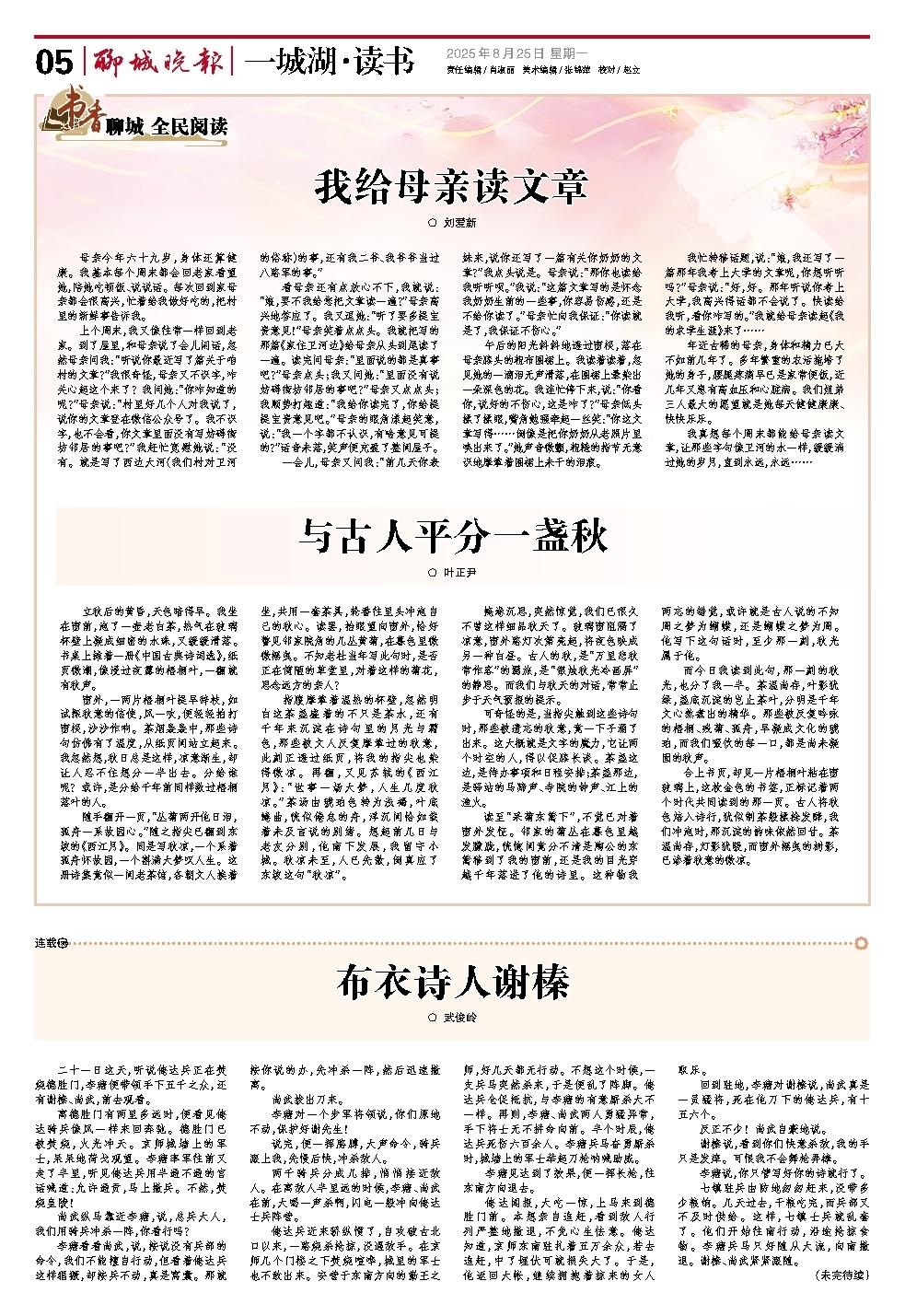与古人平分一盏秋
○ 叶正尹
立秋后的黄昏,天色暗得早。我坐在窗前,泡了一壶老白茶,热气在玻璃杯壁上凝成细密的水珠,又缓缓滑落。书桌上摊着一册《中国古典诗词选》,纸页微潮,像浸过夜露的梧桐叶,一翻就有秋声。
窗外,一两片梧桐叶提早辞枝,如试探秋意的信使,风一吹,便轻轻拍打窗棂,沙沙作响。茶烟袅袅中,那些诗句仿佛有了温度,从纸页间站立起来。我忽然想,秋日总是这样,凉意渐生,却让人忍不住想分一半出去。分给谁呢?或许,是分给千年前同样数过梧桐落叶的人。
随手翻开一页,“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随之指尖已翻到东坡的《西江月》。同是写秋凉,一个系着孤舟怀故园,一个斟满大梦叹人生。这册诗集竟似一间老茶馆,各朝文人挨着坐,共用一套茶具,轮番往里头冲泡自己的秋心。读罢,抬眼望向窗外,恰好瞥见邻家院角的几丛黄菊,在暮色里微微摇曳。不知老杜当年写此句时,是否正在简陋的草堂里,对着这样的菊花,思念远方的亲人?
指腹摩挲着温热的杯壁,忽然明白这茶盏盛着的不只是茶水,还有千年来沉淀在诗句里的月光与霜色,那些被文人反复摩挲过的秋意,此刻正透过纸页,将我的指尖也染得微凉。再翻,又见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茶汤由琥珀色转为浅褐,叶底蜷曲,恍似倦怠的舟,浮沉间恰如载着未及言说的别绪。想起前几日与老友分别,他南下发展,我留守小城。秋凉未至,人已先散,倒真应了东坡这句“秋凉”。
掩卷沉思,突然惊觉,我们已很久不曾这样细品秋天了。玻璃窗阻隔了凉意,窗外路灯次第亮起,将夜色映成另一种白昼。古人的秋,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的羁旅,是“银烛秋光冷画屏”的静思。而我们与秋天的对话,常常止步于天气预报的提示。
可奇怪的是,当指尖触到这些诗句时,那些被遗忘的秋意,竟一下子涌了出来。这大概就是文字的魔力,它让两个时空的人,得以促膝长谈。茶盏这边,是待办事项和日程安排;茶盏那边,是驿站的马蹄声、寺院的钟声、江上的渔火。
读至“采菊东篱下”,不觉已对着窗外发怔。邻家的菊丛在暮色里越发朦胧,恍惚间竟分不清是陶公的东篱移到了我的窗前,还是我的目光穿越千年落进了他的诗里。这种物我两忘的错觉,或许就是古人说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他写下这句话时,至少那一刻,秋光属于他。
而今日我读到此句,那一刻的秋光,也分了我一半。茶温尚存,叶影犹绿,盏底沉淀的岂止茶叶,分明是千年文心熬煮出的精华。那些被反复吟咏的梧桐、残菊、孤舟,早凝成文化的琥珀,而我们啜饮的每一口,都是尚未凝固的秋声。
合上书页,却见一片梧桐叶粘在窗玻璃上,这枚金色的书签,正标记着两个时代共同读到的那一页。古人将秋色焙入诗行,犹似制茶般揉捻发酵,我们冲泡时,那沉淀的韵味依然回甘。茶温尚存,灯影犹暖,而窗外摇曳的树影,已渗着秋意的微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