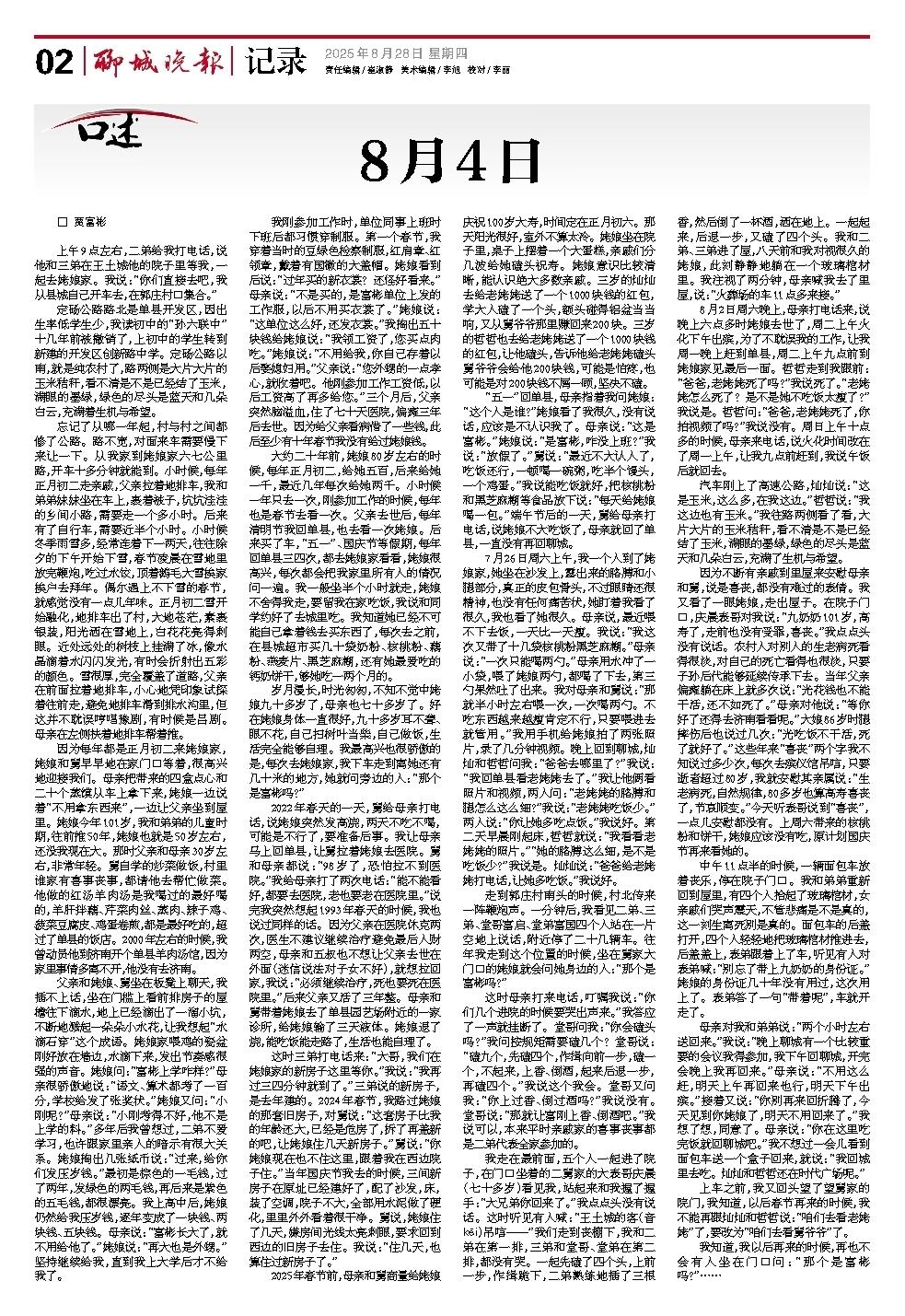8月4日
□ 贾富彬
上午9点左右,二弟给我打电话,说他和三弟在王土城他的院子里等我,一起去姥娘家。我说:“你们直接去吧,我从县城自己开车去,在郭庄村口集合。”
定砀公路路北是单县开发区,因出生率低学生少,我读初中的“孙六联中”十几年前被撤销了,上初中的学生转到新建的开发区创新路中学。定砀公路以南,就是纯农村了,路两侧是大片大片的玉米秸秆,看不清是不是已经结了玉米,满眼的墨绿,绿色的尽头是蓝天和几朵白云,充满着生机与希望。
忘记了从哪一年起,村与村之间都修了公路。路不宽,对面来车需要慢下来让一下。从我家到姥娘家六七公里路,开车十多分钟就能到。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二走亲戚,父亲拉着地排车,我和弟弟妹妹坐在车上,裹着被子,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需要走一个多小时。后来有了自行车,需要近半个小时。小时候冬季雨雪多,经常连着下一两天,往往除夕的下午开始下雪,春节凌晨在雪地里放完鞭炮,吃过水饺,顶着鹅毛大雪挨家挨户去拜年。偶尔遇上不下雪的春节,就感觉没有一点儿年味。正月初二雪开始融化,地排车出了村,大地苍茫,素裹银装,阳光洒在雪地上,白花花亮得刺眼。近处远处的树枝上挂满了冰,像水晶滴着水闪闪发光,有时会折射出五彩的颜色。雪很厚,完全覆盖了道路,父亲在前面拉着地排车,小心地凭印象试探着往前走,避免地排车滑到排水沟里,但这并不耽误哼唱豫剧,有时候是吕剧。母亲在左侧扶着地排车帮着推。
因为每年都是正月初二来姥娘家,姥娘和舅早早地在家门口等着,很高兴地迎接我们。母亲把带来的四盒点心和二十个蒸馍从车上拿下来,姥娘一边说着“不用拿东西来”,一边让父亲坐到屋里。姥娘今年101岁,我和弟弟的儿童时期,往前推50年,姥娘也就是50岁左右,还没我现在大。那时父亲和母亲30岁左右,非常年轻。舅自学的炒菜做饭,村里谁家有喜事丧事,都请他去帮忙做菜。他做的红汤羊肉汤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羊肝拌藕、芹菜肉丝、蒸肉、辣子鸡、菠菜豆腐皮、鸡蛋卷煎,都是最好吃的,超过了单县的饭店。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曾动员他到济南开个单县羊肉汤馆,因为家里事情多离不开,他没有去济南。
父亲和姥娘、舅坐在板凳上聊天,我插不上话,坐在门槛上看前排房子的屋檐往下滴水,地上已经滴出了一溜小坑,不断地溅起一朵朵小水花,让我想起“水滴石穿”这个成语。姥娘家喂鸡的瓷盆刚好放在墙边,水滴下来,发出节奏感很强的声音。姥娘问:“富彬上学咋样?”母亲很骄傲地说:“语文、算术都考了一百分,学校给发了张奖状。”姥娘又问:“小刚呢?”母亲说:“小刚考得不好,他不是上学的料。”多年后我曾想过,二弟不爱学习,也许跟家里亲人的暗示有很大关系。姥娘掏出几张纸币说:“过来,给你们发压岁钱。”最初是棕色的一毛钱,过了两年,发绿色的两毛钱,再后来是紫色的五毛钱,都很漂亮。我上高中后,姥娘仍然给我压岁钱,逐年变成了一块钱、两块钱、五块钱。母亲说:“富彬长大了,就不用给他了。”姥娘说:“再大也是外甥。”坚持继续给我,直到我上大学后才不给我了。
我刚参加工作时,单位同事上班时下班后都习惯穿制服。第一个春节,我穿着当时的豆绿色检察制服,红肩章、红领章,戴着有国徽的大盖帽。姥娘看到后说:“过年买的新衣裳?还怪好看来。”母亲说:“不是买的,是富彬单位上发的工作服,以后不用买衣裳了。”姥娘说:“这单位这么好,还发衣裳。”我掏出五十块钱给姥娘说:“我领工资了,您买点肉吃。”姥娘说:“不用给我,你自己存着以后娶媳妇用。”父亲说:“您外甥的一点孝心,就收着吧。他刚参加工作工资低,以后工资高了再多给您。”三个月后,父亲突然脑溢血,住了七十天医院,偏瘫三年后去世。因为给父亲看病借了一些钱,此后至少有十年春节我没有给过姥娘钱。
大约二十年前,姥娘80岁左右的时候,每年正月初二,给她五百,后来给她一千,最近几年每次给她两千。小时候一年只去一次,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年也是春节去看一次。父亲去世后,每年清明节我回单县,也去看一次姥娘。后来买了车,“五一”、国庆节等假期,每年回单县三四次,都去姥娘家看看,姥娘很高兴,每次都会把我家里所有人的情况问一遍。我一般坐半个小时就走,姥娘不舍得我走,要留我在家吃饭,我说和同学约好了去城里吃。我知道她已经不可能自己拿着钱去买东西了,每次去之前,在县城超市买几十袋奶粉、核桃粉、藕粉、燕麦片、黑芝麻糊,还有她最爱吃的钙奶饼干,够她吃一两个月的。
岁月漫长,时光匆匆,不知不觉中姥娘九十多岁了,母亲也七十多岁了。好在姥娘身体一直很好,九十多岁耳不聋、眼不花,自己扫树叶当柴,自己做饭,生活完全能够自理。我最高兴也很骄傲的是,每次去姥娘家,我下车走到离她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她就问旁边的人:“那个是富彬吗?”
2022年春天的一天,舅给母亲打电话,说姥娘突然发高烧,两天不吃不喝,可能是不行了,要准备后事。我让母亲马上回单县,让舅拉着姥娘去医院。舅和母亲都说:“98岁了,恐怕拉不到医院。”我给母亲打了两次电话:“能不能看好,都要去医院,老也要老在医院里。”说完我突然想起1993年春天的时候,我也说过同样的话。因为父亲在医院休克两次,医生不建议继续治疗避免最后人财两空,母亲和五叔也不想让父亲去世在外面(迷信说法对子女不好),就想拉回家,我说:“必须继续治疗,死也要死在医院里。”后来父亲又活了三年整。母亲和舅带着姥娘去了单县园艺场附近的一家诊所,给姥娘输了三天液体。姥娘退了烧,能吃饭能走路了,生活也能自理了。
这时三弟打电话来:“大哥,我们在姥娘家的新房子这里等你。”我说:“我再过三四分钟就到了。”三弟说的新房子,是去年建的。2024年春节,我路过姥娘的那套旧房子,对舅说:“这套房子比我的年龄还大,已经是危房了,拆了再盖新的吧,让姥娘住几天新房子。”舅说:“你姥娘现在也不住这里,跟着我在西边院子住。”当年国庆节我去的时候,三间新房子在原址已经建好了,配了沙发,床,装了空调,院子不大,全部用水泥做了硬化,里里外外看着很干净。舅说,姥娘住了几天,嫌房间光线太亮刺眼,要求回到西边的旧房子去住。我说:“住几天,也算住过新房子了。”
2025年春节前,母亲和舅商量给姥娘庆祝100岁大寿,时间定在正月初六。那天阳光很好,室外不算太冷。姥娘坐在院子里,桌子上摆着一个大蛋糕,亲戚们分几波给她磕头祝寿。姥娘意识比较清晰,能认识绝大多数亲戚。三岁的灿灿去给老姥姥送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学大人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得铝盆当当响,又从舅爷爷那里赚回来200块。三岁的哲哲也去给老姥姥送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让他磕头,告诉他给老姥姥磕头舅爷爷会给他200块钱,可能是怕疼,也可能是对200块钱不屑一顾,坚决不磕。
“五一”回单县,母亲指着我问姥娘:“这个人是谁?”姥娘看了我很久,没有说话,应该是不认识我了。母亲说:“这是富彬。”姥娘说:“是富彬,咋没上班?”我说:“放假了。”舅说:“最近不大认人了,吃饭还行,一顿喝一碗粥,吃半个馒头,一个鸡蛋。”我说能吃饭就好,把核桃粉和黑芝麻糊等食品放下说:“每天给姥娘喝一包。”端午节后的一天,舅给母亲打电话,说姥娘不大吃饭了,母亲就回了单县,一直没有再回聊城。
7月26日周六上午,我一个人到了姥娘家,她坐在沙发上,露出来的胳膊和小腿部分,真正的皮包骨头,不过眼睛还很精神,也没有任何痛苦状,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我也看了她很久。母亲说,最近喂不下去饭,一天比一天瘦。我说:“我这次又带了十几袋核桃粉黑芝麻糊。”母亲说:“一次只能喝两勺。”母亲用水冲了一小袋,喂了姥娘两勺,都喝了下去,第三勺果然吐了出来。我对母亲和舅说:“那就半小时左右喂一次,一次喝两勺。不吃东西越来越瘦肯定不行,只要喂进去就管用。”我用手机给姥娘拍了两张照片,录了几分钟视频。晚上回到聊城,灿灿和哲哲问我:“爸爸去哪里了?”我说:“我回单县看老姥姥去了。”我让他俩看照片和视频,两人问:“老姥姥的胳膊和腿怎么这么细?”我说:“老姥姥吃饭少。”两人说:“你让她多吃点饭。”我说好。第二天早晨刚起床,哲哲就说:“我看看老姥姥的照片。”“她的胳膊这么细,是不是吃饭少?”我说是。灿灿说:“爸爸给老姥姥打电话,让她多吃饭。”我说好。
走到郭庄村南头的时候,村北传来一阵鞭炮声。一分钟后,我看见二弟、三弟、堂哥富启、堂弟富国四个人站在一片空地上说话,附近停了二十几辆车。往年我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坐在舅家大门口的姥娘就会问她身边的人:“那个是富彬吗?”
这时母亲打来电话,叮嘱我说:“你们几个进院的时候要哭出声来。”我答应了一声就挂断了。堂哥问我:“你会磕头吗?”我问按规矩需要磕几个?堂哥说:“磕九个,先磕四个,作揖向前一步,磕一个,不起来,上香、倒酒,起来后退一步,再磕四个。”我说这个我会。堂哥又问我:“你上过香、倒过酒吗?”我说没有。堂哥说:“那就让富刚上香、倒酒吧。”我说可以,本来平时亲戚家的喜事丧事都是二弟代表全家参加的。
我走在最前面,五个人一起进了院子,在门口坐着的二舅家的大表哥庆晨(七十多岁)看见我,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大兄弟你回来了。”我点点头没有说话。这时听见有人喊:“王土城的客(音kēi)吊唁——”我们走到丧棚下,我和二弟在第一排,三弟和堂哥、堂弟在第二排,都没有哭。一起先磕了四个头,上前一步,作揖跪下,二弟熟练地插了三根香,然后倒了一杯酒,洒在地上。一起起来,后退一步,又磕了四个头。我和二弟、三弟进了屋,八天前和我对视很久的姥娘,此刻静静地躺在一个玻璃棺材里。我注视了两分钟,母亲喊我去了里屋,说:“火葬场的车11点多来接。”
8月2日周六晚上,母亲打电话来,说晚上六点多时姥娘去世了,周二上午火化下午出殡,为了不耽误我的工作,让我周一晚上赶到单县,周二上午九点前到姥娘家见最后一面。哲哲走到我跟前:“爸爸,老姥姥死了吗?”我说死了。“老姥姥怎么死了?是不是她不吃饭太瘦了?”我说是。哲哲问:“爸爸,老姥姥死了,你拍视频了吗?”我说没有。周日上午十点多的时候,母亲来电话,说火化时间改在了周一上午,让我九点前赶到,我说午饭后就回去。
汽车刚上了高速公路,灿灿说:“这是玉米,这么多,在我这边。”哲哲说:“我这边也有玉米。”我往路两侧看了看,大片大片的玉米秸秆,看不清是不是已经结了玉米,满眼的墨绿,绿色的尽头是蓝天和几朵白云,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因为不断有亲戚到里屋来安慰母亲和舅,说是喜丧,都没有难过的表情。我又看了一眼姥娘,走出屋子。在院子门口,庆晨表哥对我说:“九奶奶101岁,高寿了,走前也没有受罪,喜丧。”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农村人对别人的生老病死看得很淡,对自己的死亡看得也很淡,只要子孙后代能够延续传承下去。当年父亲偏瘫躺在床上就多次说:“光花钱也不能干活,还不如死了。”母亲对他说:“等你好了还得去济南看看呢。”大娘86岁时腿摔伤后也说过几次:“光吃饭不干活,死了就好了。”这些年来“喜丧”两个字我不知说过多少次,每次去殡仪馆吊唁,只要逝者超过80岁,我就安慰其亲属说:“生老病死,自然规律,80多岁也算高寿喜丧了,节哀顺变。”今天听表哥说到“喜丧”,一点儿安慰都没有。上周六带来的核桃粉和饼干,姥娘应该没有吃,原计划国庆节再来看她的。
中午11点半的时候,一辆面包车放着丧乐,停在院子门口。我和弟弟重新回到屋里,有四个人抬起了玻璃棺材,女亲戚们哭声震天,不管悲痛是不是真的,这一刻生离死别是真的。面包车的后盖打开,四个人轻轻地把玻璃棺材推进去,后盖盖上,表弟跟着上了车,听见有人对表弟喊:“别忘了带上九奶奶的身份证。”姥娘的身份证几十年没有用过,这次用上了。表弟答了一句“带着呢”,车就开走了。
母亲对我和弟弟说:“两个小时左右送回来。”我说:“晚上聊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我得参加,我下午回聊城,开完会晚上我再回来。”母亲说:“不用这么赶,明天上午再回来也行,明天下午出殡。”接着又说:“你别再来回折腾了,今天见到你姥娘了,明天不用回来了。”我想了想,同意了。母亲说:“你在这里吃完饭就回聊城吧。”我不想过一会儿看到面包车送一个盒子回来,就说:“我回城里去吃。灿灿和哲哲还在时代广场呢。”
上车之前,我又回头望了望舅家的院门,我知道,以后春节再来的时候,我不能再跟灿灿和哲哲说:“咱们去看老姥姥”了,要改为“咱们去看舅爷爷”了。
我知道,我以后再来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人坐在门口问:“那个是富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