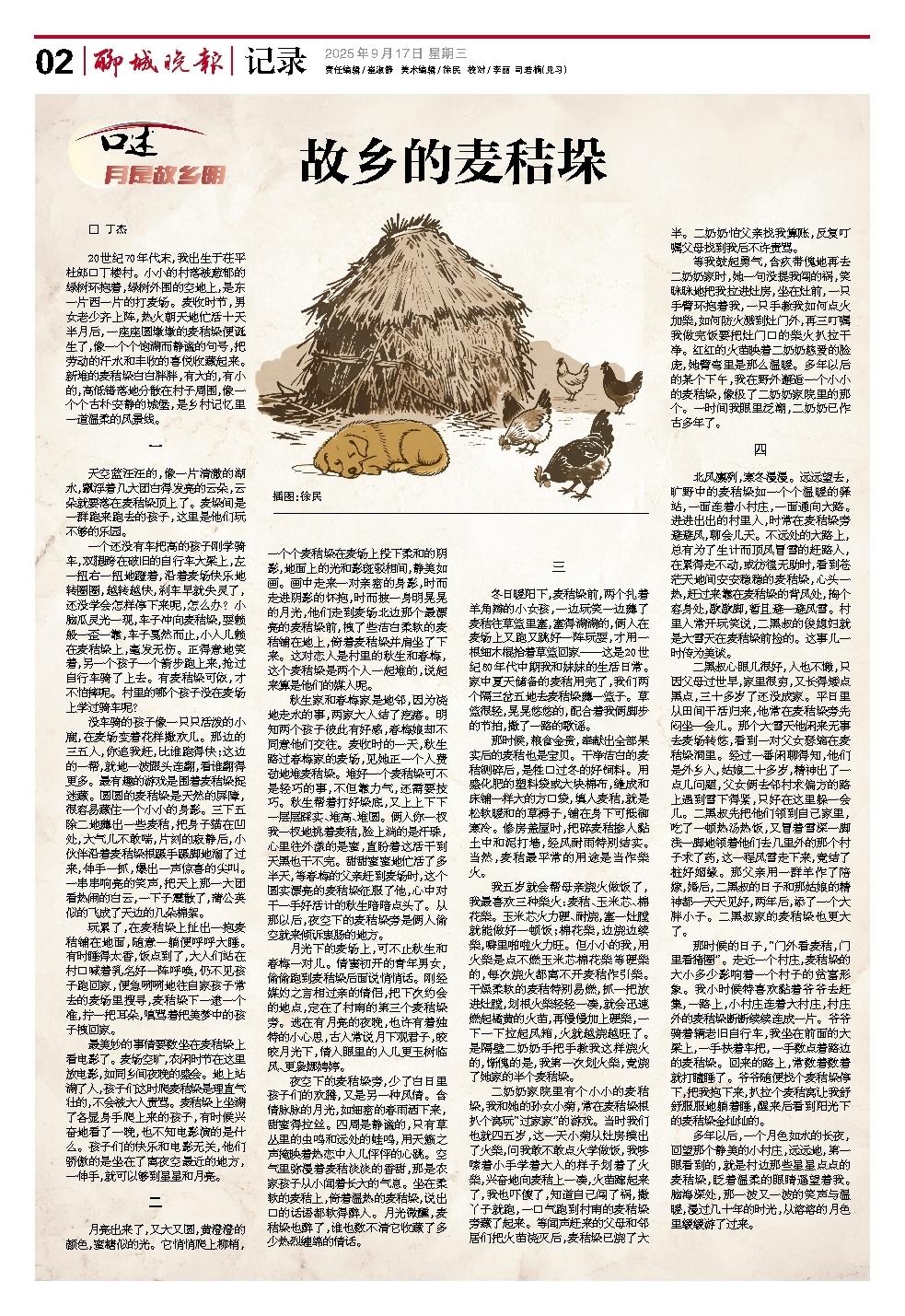故乡的麦秸垛
□ 丁杰
20世纪70年代末,我出生于茌平杜郎口丁楼村。小小的村落被葱郁的绿树环抱着,绿树外围的空地上,是东一片西一片的打麦场。麦收时节,男女老少齐上阵,热火朝天地忙活十天半月后,一座座圆墩墩的麦秸垛便诞生了,像一个个饱满而静谧的句号,把劳动的汗水和丰收的喜悦收藏起来。新堆的麦秸垛白白胖胖,有大的,有小的,高低错落地分散在村子周围,像一个个古朴安静的城堡,是乡村记忆里一道温柔的风景线。
一
天空蓝汪汪的,像一片清澈的湖水,飘浮着几大团白得发亮的云朵,云朵就要落在麦秸垛顶上了。麦垛间是一群跑来跑去的孩子,这里是他们玩不够的乐园。
一个还没有车把高的孩子刚学骑车,双腿跨在破旧的自行车大梁上,左一扭右一扭地蹬着,沿着麦场快乐地转圈圈,越转越快,刹车早就失灵了,还没学会怎样停下来呢,怎么办?小脑瓜灵光一现,车子冲向麦秸垛,耍赖般一歪一靠,车子戛然而止,小人儿赖在麦秸垛上,毫发无伤。正得意地笑着,另一个孩子一个箭步跑上来,抢过自行车骑了上去。有麦秸垛可依,才不怕摔呢。村里的哪个孩子没在麦场上学过骑车呢?
没车骑的孩子像一只只活泼的小鹿,在麦场变着花样撒欢儿。那边的三五人,你追我赶,比谁跑得快;这边的一帮,就地一波跟头连翻,看谁翻得更多。最有趣的游戏是围着麦秸垛捉迷藏。圆圆的麦秸垛是天然的屏障,很容易藏住一个小小的身影。三下五除二地薅出一些麦秸,把身子猫在凹处,大气儿不敢喘,片刻的寂静后,小伙伴沿着麦秸垛根蹑手蹑脚地溜了过来,伸手一抓,爆出一声惊喜的尖叫。一串串响亮的笑声,把天上那一大团看热闹的白云,一下子震散了,蒲公英似的飞成了天边的几朵棉絮。
玩累了,在麦秸垛上扯出一抱麦秸铺在地面,随意一躺便呼呼大睡。有时睡得太香,饭点到了,大人们站在村口喊着乳名好一阵呼唤,仍不见孩子跑回家,便急咧咧地往自家孩子常去的麦场里搜寻,麦秸垛下一逮一个准,拧一把耳朵,嗔骂着把美梦中的孩子拽回家。
最美妙的事情要数坐在麦秸垛上看电影了。麦场空旷,农闲时节在这里放电影,如同乡间夜晚的盛会。地上站满了人,孩子们这时爬麦秸垛是理直气壮的,不会被大人责骂。麦秸垛上坐满了各显身手爬上来的孩子,有时候兴奋地看了一晚,也不知电影演的是什么。孩子们的快乐和电影无关,他们骄傲的是坐在了离夜空最近的地方,一伸手,就可以够到星星和月亮。
二
月亮出来了,又大又圆,黄澄澄的颜色,蜜糖似的光。它悄悄爬上柳梢,一个个麦秸垛在麦场上投下柔和的阴影,地面上的光和影斑驳相间,静美如画。画中走来一对亲密的身影,时而走进阴影的怀抱,时而披一身明晃晃的月光,他们走到麦场北边那个最漂亮的麦秸垛前,拽了些洁白柔软的麦秸铺在地上,倚着麦秸垛并肩坐了下来。这对恋人是村里的秋生和春梅,这个麦秸垛是两个人一起堆的,说起来算是他们的媒人呢。
秋生家和春梅家是地邻,因为浇地走水的事,两家大人结了疙瘩。明知两个孩子彼此有好感,春梅娘却不同意他们交往。麦收时的一天,秋生路过春梅家的麦场,见她正一个人费劲地堆麦秸垛。堆好一个麦秸垛可不是轻巧的事,不但靠力气,还需要技巧。秋生帮着打好垛底,又上上下下一层层踩实、堆高、堆圆。俩人你一杈我一杈地挑着麦秸,脸上淌的是汗珠,心里往外漾的是蜜,直盼着这活干到天黑也干不完。甜甜蜜蜜地忙活了多半天,等春梅的父亲赶到麦场时,这个圆实漂亮的麦秸垛征服了他,心中对干一手好活计的秋生暗暗点头了。从那以后,夜空下的麦秸垛旁是俩人偷空就来倾诉衷肠的地方。
月光下的麦场上,可不止秋生和春梅一对儿。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偷偷跑到麦秸垛后面说悄悄话。刚经媒妁之言相过亲的情侣,把下次约会的地点,定在了村南的第三个麦秸垛旁。选在有月亮的夜晚,也许有着独特的小心思,古人常说月下观君子,皎皎月光下,情人眼里的人儿更玉树临风、更袅娜娉婷。
夜空下的麦秸垛旁,少了白日里孩子们的欢腾,又是另一种风情。含情脉脉的月光,如细密的春雨洒下来,甜蜜得拉丝。四周是静谧的,只有草丛里的虫鸣和远处的蛙鸣,用天籁之声掩映着热恋中人儿怦怦的心跳。空气里弥漫着麦秸淡淡的香甜,那是农家孩子从小闻着长大的气息。坐在柔软的麦秸上,倚着温热的麦秸垛,说出口的话语都软得醉人。月光微醺,麦秸垛也醉了,谁也数不清它收藏了多少热烈缠绵的情话。
三
冬日暖阳下,麦秸垛前,两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一边玩笑一边薅了麦秸往草篮里塞,塞得满满的,俩人在麦场上又跑又跳好一阵玩耍,才用一根细木棍抬着草篮回家——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妹妹的生活日常。家中夏天储备的麦秸用完了,我们两个隔三岔五地去麦秸垛薅一篮子。草篮很轻,晃晃悠悠的,配合着我俩脚步的节拍,撒了一路的歌谣。
那时候,粮食金贵,奉献出全部果实后的麦秸也是宝贝。干净洁白的麦秸铡碎后,是牲口过冬的好饲料。用盛化肥的塑料袋或大块棉布,缝成和床铺一样大的方口袋,填入麦秸,就是松软暖和的草褥子,铺在身下可抵御寒冷。修房盖屋时,把碎麦秸掺入黏土中和泥打墙,经风耐雨特别结实。当然,麦秸最平常的用途是当作柴火。
我五岁就会帮母亲烧火做饭了,我最喜欢三种柴火:麦秸、玉米芯、棉花柴。玉米芯火力硬、耐烧,塞一灶膛就能做好一顿饭;棉花柴,边烧边续柴,噼里啪啦火力旺。但小小的我,用火柴是点不燃玉米芯棉花柴等硬柴的,每次烧火都离不开麦秸作引柴。干燥柔软的麦秸特别易燃,抓一把放进灶膛,划根火柴轻轻一凑,就会迅速燃起橘黄的火苗,再慢慢加上硬柴,一下一下拉起风箱,火就越烧越旺了。是隔壁二奶奶手把手教我这样烧火的,惭愧的是,我第一次划火柴,竟烧了她家的半个麦秸垛。
二奶奶家院里有个小小的麦秸垛,我和她的孙女小菊,常在麦秸垛根扒个窝玩“过家家”的游戏。当时我们也就四五岁,这一天小菊从灶房摸出了火柴,问我敢不敢点火学做饭,我哆嗦着小手学着大人的样子划着了火柴,兴奋地向麦秸上一凑,火苗蹿起来了,我也吓傻了,知道自己闯了祸,撒丫子就跑,一口气跑到村南的麦秸垛旁藏了起来。等闻声赶来的父母和邻居们把火苗浇灭后,麦秸垛已烧了大半。二奶奶怕父亲找我算账,反复叮嘱父母找到我后不许责骂。
等我鼓起勇气,含疚带愧地再去二奶奶家时,她一句没提我闯的祸,笑眯眯地把我拉进灶房,坐在灶前,一只手臂环抱着我,一只手教我如何点火加柴,如何防火溅到灶门外,再三叮嘱我做完饭要把灶门口的柴火扒拉干净。红红的火苗映着二奶奶慈爱的脸庞,她臂弯里是那么温暖。多年以后的某个下午,我在野外邂逅一个小小的麦秸垛,像极了二奶奶家院里的那个。一时间我眼里泛潮,二奶奶已作古多年了。
四
北风凛冽,寒冬漫漫。远远望去,旷野中的麦秸垛如一个个温暖的驿站,一面连着小村庄,一面通向大路。进进出出的村里人,时常在麦秸垛旁避避风,聊会儿天。不远处的大路上,总有为了生计而顶风冒雪的赶路人,在累得走不动,或彷徨无助时,看到苍茫天地间安安稳稳的麦秸垛,心头一热,赶过来靠在麦秸垛的背风处,掏个容身处,歇歇脚,暂且避一避风雪。村里人常开玩笑说,二黑叔的俊媳妇就是大雪天在麦秸垛前捡的。这事儿一时传为美谈。
二黑叔心眼儿很好,人也不懒,只因父母过世早,家里很穷,又长得矮点黑点,三十多岁了还没成家。平日里从田间干活归来,他常在麦秸垛旁先闷坐一会儿。那个大雪天他闲来无事去麦场转悠,看到一对父女瑟缩在麦秸垛洞里。经过一番闲聊得知,他们是外乡人,姑娘二十多岁,精神出了一点儿问题,父女俩去邻村求偏方的路上遇到雪下得紧,只好在这里躲一会儿。二黑叔先把他们领到自己家里,吃了一顿热汤热饭,又冒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领着他们去几里外的那个村子求了药,这一程风雪走下来,竟结了桩好姻缘。那父亲用一群羊作了陪嫁,婚后,二黑叔的日子和那姑娘的精神都一天天见好,两年后,添了一个大胖小子。二黑叔家的麦秸垛也更大了。
那时候的日子,“门外看麦秸,门里看猪圈”。走近一个村庄,麦秸垛的大小多少影响着一个村子的贫富形象。我小时候特喜欢黏着爷爷去赶集,一路上,小村庄连着大村庄,村庄外的麦秸垛断断续续连成一片。爷爷骑着辆老旧自行车,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数点着路边的麦秸垛。回来的路上,常数着数着就打瞌睡了。爷爷随便找个麦秸垛停下,把我抱下来,扒拉个麦秸窝让我舒舒服服地躺着睡,醒来后看到阳光下的麦秸垛金灿灿的。
多年以后,一个月色如水的长夜,回望那个静美的小村庄,远远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村边那些星星点点的麦秸垛,眨着温柔的眼睛遥望着我。脑海深处,那一波又一波的笑声与温暖,漫过几十年的时光,从溶溶的月色里缓缓游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