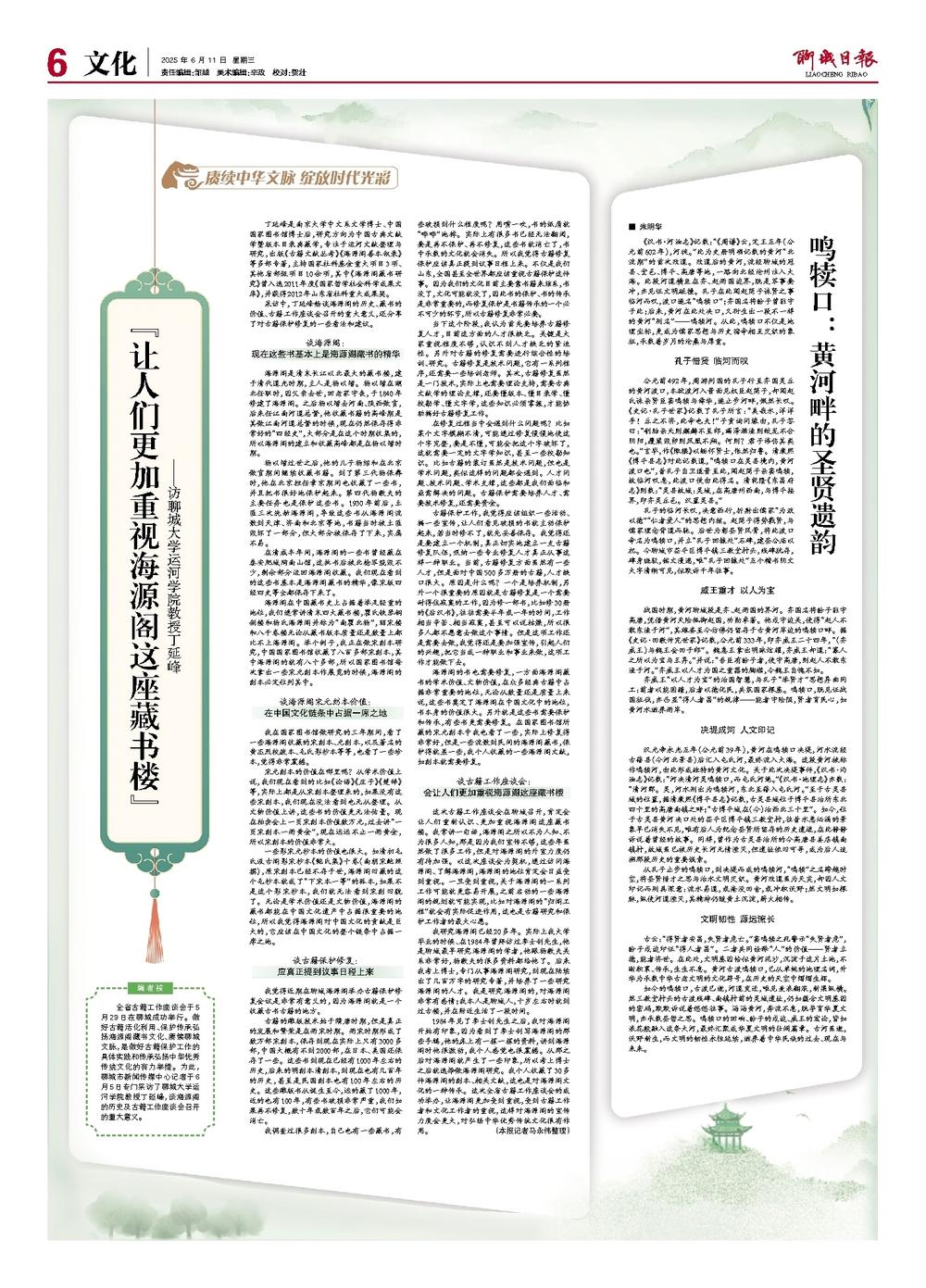“让人们更加重视海源阁这座藏书楼”
——访聊城大学运河学院教授丁延峰
编者按:
全省古籍工作座谈会于5月29日在聊城成功举行。做好古籍活化利用、保护传承弘扬海源阁藏书文化、赓续聊城文脉,是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具体实践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举措。为此,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于6月5日专门采访了聊城大学运河学院教授丁延峰,谈海源阁的历史及古籍工作座谈会召开的重大意义。
丁延峰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暨版本目录典藏学,专注于运河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古籍文献丛考》《海源阁善本叙录》等多部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海源阁藏书研究》曾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得2012年山东省社科重大成果奖。
采访中,丁延峰畅谈海源阁的历史、藏书的价值、古籍工作座谈会召开的重大意义,还分享了对古籍保护修复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谈海源阁:现在这些书基本上是海源阁藏书的精华
海源阁是清末长江以北最大的藏书楼,建于清代道光时期,主人是杨以增。杨以增在湖北任职时,因父亲去世,回老家守丧,于1840年修建了海源阁。之后杨以增去河南、陕西做官,后来任江南河道总督,他收藏书籍的高峰期是其做江南河道总督的时候,现在仍然保存得非常好的“四经史”,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收集的,所以海源阁的建立和收藏高峰都是在杨以增时期。
杨以增过世之后,他的儿子杨绍和在北京做官期间继续收藏书籍。到了第三代杨保彝时,他在北京担任章京期间也收藏了一些书,并且把书很好地保护起来。第四代杨敬夫的主要任务也是保护这些书。1930年前后,土匪三次洗劫海源阁,导致这些书从海源阁流散到天津、济南和北京等地,书籍当时被土匪毁坏了一部分,但大部分被保存了下来,实属不易。
在清咸丰年间,海源阁的一些书曾经藏在泰安肥城陶南山馆,这批书后被北捻军烧毁不少,剩余部分运回海源阁收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书基本是海源阁藏书的精华,像宋版四经四史等全都保存下来了。
海源阁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通常讲清末四大藏书楼,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杨氏海源阁并称为“南瞿北杨”,皕宋楼和八千卷楼无论从藏书版本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比不上海源阁。举个例子,我正在做宋刻本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八百多部宋刻本,其中海源阁的就有八十多部,所以国家图书馆每次拿出一些宋元刻本作展览的时候,海源阁的刻本必定位列其中。
谈海源阁宋元刻本价值:在中国文化链条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在国家图书馆做研究的三年期间,看了一些海源阁收藏的宋刻本、元刻本,以及著名的黄丕烈校跋本、毛氏影抄本等等,也看了一些珍本,觉得非常震撼。
宋元刻本的价值在哪里呢?从学术价值上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论语》《庄子》《楚辞》等,实际上都是从宋刻本整理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宋刻本,我们现在没法看到也无从整理。从文物价值上讲,这些书的价值更无法估量。现在拍卖会上一页宋刻本价值数万元,过去讲“一页宋刻本一两黄金”,现在远远不止一两黄金,所以宋刻本的价值非常大。
一些影宋元抄本的价值也很大。如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氏集》十卷(南朝宋鮑照撰),原宋刻本已经不存于世,海源阁旧藏的这个毛抄本就成了“下宋本一等”的孤本,如果不是这个影宋抄本,我们就无法看到宋刻旧貌了。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海源阁的藏书都能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觉得海源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应该在中国文化的整个链条中占据一席之地。
谈古籍保护修复:应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觉得近期在聊城海源阁举办古籍保护修复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海源阁就是一个收藏古书古籍的地方。
古籍的雕版技术始于隋唐时期,但是真正的发展和繁荣是在两宋时期。两宋时期形成了数万部宋刻本,保存到现在实际上只有3000多部,中国大概有不到2000部,在日本、美国还保存了一些。这些书到现在已经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后来的明刻本清刻本,到现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是民国刻本也有1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雕版书从诞生至今,远的藏了1000年,近的也有100年,有些书破损非常严重,我们如果再不修复,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后,它们可能会消亡。
我调查过很多刻本,自己也有一些藏书,有些破损到什么程度呢?用嘴一吹,书的纸屑就“哗哗”地掉。实际上有很多书已经无法翻阅,要是再不保护、再不修复,这些书就消亡了,书中承载的文化就会消失。所以我觉得古籍修复保护应该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仅是我们山东,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应该重视古籍保护这件事。因为我们的文化目前主要靠书籍来维系,书没了,文化可能就没了,因此书的保护、书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而修复保护是书籍传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古籍修复非常必要。
当下这个阶段,我认为首先要培养古籍修复人才,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关键是大家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人才缺乏的紧迫性。另外对古籍的修复需要进行综合性的培训、研究。古籍修复是技术问题,它有一系列程序,还需要一些培训老师。其次,古籍修复虽然是一门技术,实际上也需要理论支持,需要古典文献学的理论支撑,还要懂版本、懂目录学、懂校勘学、懂文字学,这些知识必须掌握,才能协助搞好古籍修复工作。
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比如某个文字模糊不清,可能通过修复慢慢地使这个字完整,要是不懂,可能会把这个字破坏了,这就需要一定的文字学知识,甚至一些校勘知识。比如古籍的装订虽然是技术问题,但也是学术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都会遇到。人才问题、技术问题、学术支撑,这些都是我们面临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古籍保护需要培养人才、需要技术修复,还需要资金。
古籍保护工作,我觉得应该组织一些活动、搞一些宣传,让人们看见破损的书就主动保护起来,若当时修不了,就先妥善保存。我觉得还是要建立一个机制,真正切实地建立一支古籍修复队伍,吸纳一些专业修复人才真正从事这样一种职业。当前,古籍修复方面虽然有一些人才,但是面对中国500多万册的古籍,人才缺口很大。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培养机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籍修复是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因为修一部书,比如修30册的《后汉书》,往往需要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工作相当辛苦、相当寂寞,甚至可以说枯燥,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项工作还是需要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宣传,引起人们的兴趣,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和事业来做,这项工作才能做下去。
海源阁的书也需要修复,一方面海源阁藏书的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在众多经典古籍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这些书奠定了海源阁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书本身的价值很大。另外就是这些书需要保护和传承,有些书更需要修复。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宋元刻本中我也看了一些,实际上修复得非常好,但是一些流散到民间的海源阁藏书,保护得就差一些,我个人收藏的一些海源阁文献,如刻本就需要修复。
谈古籍工作座谈会:会让人们更加重视海源阁这座藏书楼
这次古籍工作座谈会在聊城召开,肯定会让人们重新认识、更加重视海源阁这座藏书楼。我常讲一句话,海源阁之所以不为人知、不为很多人知,那是因为我们宣传不够,这些年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对海源阁的外宣力度仍有待加强。以这次座谈会为契机,通过访问海源阁、了解海源阁,海源阁的地位肯定会日益受到重视。一旦受到重视,关于海源阁的一系列工作可能就更容易开展,之前启动的一些海源阁的规划就可能实现,比如对海源阁的“归阁工程”就会有实际促进作用,这也是古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最大心愿。
我研究海源阁已经20多年。实际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在1984年曾拜访过李士钊先生,他是聊城最早研究海源阁的学者,他跟杨敬夫关系非常好,杨敬夫的很多资料都给他了。后来我考上博士,专门从事海源阁研究,到现在陆续出了几百万字的研究专著,并培养了一些研究海源阁的人才。我是研究海源阁的,对海源阁非常有感情;我本人是聊城人,十岁左右时就到过古楼,并在附近生活了一段时间。
1984年见了李士钊先生之后,我对海源阁开始有印象,因为看到了李士钊写海源阁的那些手稿,他的床上有一摞一摞的资料,讲到海源阁时他很激动,我个人感觉也很震撼。从那之后对海源阁就产生了一些印象,所以考上博士之后就选择做海源阁研究。我个人收藏了30多件海源阁的刻本、相关文献,这也是对海源阁文化的一种传承。这次全省古籍工作座谈会的成功举办,让海源阁更加受到重视,受到古籍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视,这样对海源阁的宣传力度会更大,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有作用。(本报记者马永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