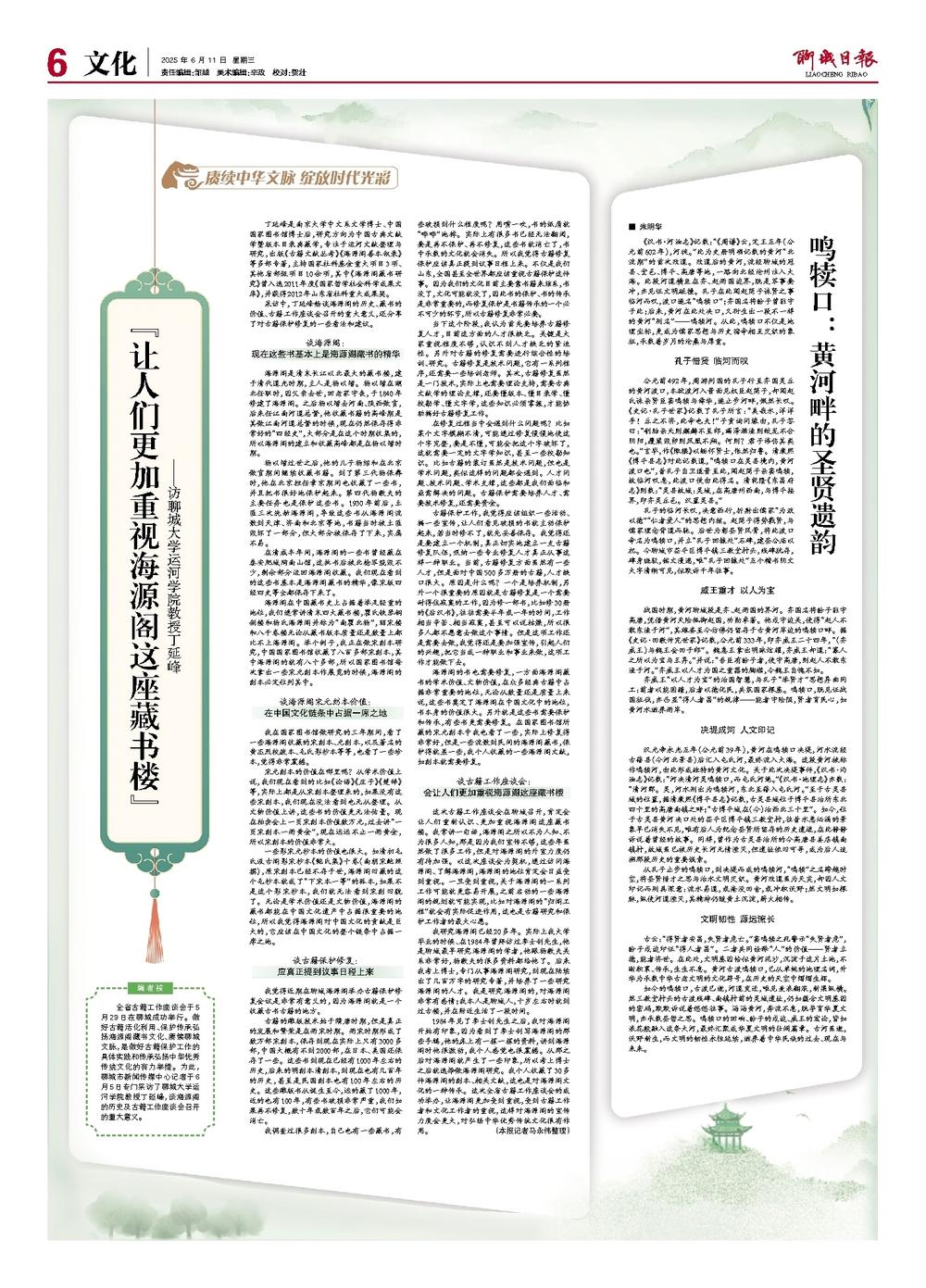鸣犊口:黄河畔的圣贤遗韵
■ 朱明华
《汉书·河洫志》记载:“《周谱》云,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徙。”此为史册明确记载的黄河“北流期”的首次改道。改道后的黄河,流经聊城的冠县、堂邑、博平、高唐等地,一路向北经沧州注入大海。此段河道横亘在齐、赵两国边界,既是军事要冲,亦见证文明碰撞。孔子在此闻赵简子诛贤之事临河而叹,渡口遂名“鸣犊口”;齐国名将盼子曾驻守于此;后来,黄河在此处决口,又衍生出一段不一样的黄河“别名”——鸣犊河。从此,鸣犊口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成为儒家思想与历史宿命相互交织的象征,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厚重。
孔子惜贤 临河而叹
公元前492年,周游列国的孔子行至齐国灵丘的黄河渡口,本欲渡河入晋面见权臣赵简子,却闻赵氏诛杀贤臣窦鸣犊与舜华,遂止步河畔,慨然长叹。《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所言:“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询问缘由,孔子答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言毕,作《陬操》以缅怀贤士,怅然归鲁。清康熙《博平县志》对此记载道,“鸣犊口在灵县境内,黄河渡口也”,昔孔子自卫适晋至此,闻赵简子杀窦鸣犊,故临河叹息,此渡口便由此得名。清乾隆《东昌府志》则载:“灵县故城:灵城,在高唐州西南,与博平接界,即齐灵丘邑。汉置灵县。”
孔子的临河长叹,绝意西行,折射出儒家“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思想内核。赵简子得势戮贤,与儒家理念背道而驰。后世为彰圣贤风骨,将此渡口命名为鸣犊口,并立“孔子回辕处”石碑,建圣公庙以祀。今聊城市茌平区博平镇三教堂村头,残碑犹存,碑身斑驳,铭文漫漶,唯“孔子回辕处”五个楷书阴文大字清晰可见,似默诉千年往事。
威王重才 以人为宝
战国时期,黄河聊城段是齐、赵两国的界河。齐国名将盼子驻守高唐,凭借黄河天险抵御赵国,功勋卓著。他戍守边关,使得“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其雄姿至今仿佛仍留存于古黄河岸边的鸣犊口畔。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公元前333年,即齐威王二十四年,“(齐威王)与魏王会田于郊”。魏惠王拿出明珠炫耀,齐威王却道:“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并说:“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齐威王以人才为国之重器的胸襟,令魏王自愧不如。
齐威王“以人才为宝”的治国智慧,与孔子“举贤才”思想异曲同工:前者以能固疆,后者以德化民,共筑国家根基。鸣犊口,既见证战国征伐,亦凸显“得人者昌”的规律——能者守险隘,贤者育民心,如黄河水滋养两岸。
决堤成河 人文印记
汉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黄河在鸣犊口决堤,河水流经古蓨县(今河北景县)后汇入屯氏河,最终流入大海。这段黄河被称作鸣犊河,由此形成独特的黄河文化。关于此次决堤事件,《汉书·沟洫志》记载:“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汉书·地理志》亦载:“清河郡。灵,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入屯氏河。”至于古灵县城的位置,据清康熙《博平县志》记载,古灵县城位于博平县治所东北四十里的高唐南镇之畔;“古博平城在(今)治西北三十里”。如今,位于古灵县黄河决口处的茌平区博平镇三教堂村,往昔水患汹涌的景象早已消失不见,唯有后人为纪念圣贤所留存的历史遗迹,在此静静诉说着曾经的故事。同样,曾作为古灵县治所的今高唐县姜店镇南镇村,故城虽已被历史长河无情湮灭,但遗址依旧可寻,成为后人追溯那段历史的重要线索。
从孔子止步的鸣犊口,到决堤而成的鸣犊河,“鸣犊”之名跨越时空,将圣贤惜才之思与治水文明交织。黄河改道虽为天灾,却因人文印记而别具深意:流水易道,或淹没田舍,或冲积沃野;然文明如根脉,纵使河道湮灭,其精神仍随黄土沉淀,薪火相传。
文明韧性 源远流长
古云:“得贤者安昌,失贤者危亡。”窦鸣犊之死警示“失贤者危”,盼子戍边印证“得人者昌”。二者共同诠释“人”的价值——贤者立德,能者济世。在此处,文明基因恰似黄河泥沙,沉淀于这片土地,不断积累、传承,生生不息。黄河古渡鸣犊口,已从单纯的地理名词,升华为承载中华古老文明的文化符号,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如今的鸣犊口,古渡已逝,河道变迁,唯见麦浪翻滚,新渠纵横。然三教堂村头的古渡残碑、南镇村前的灵城遗址,仍如蕴含文明基因的密码,默默诉说着悠悠往事。滔滔黄河,奔流不息,既孕育华夏文明,亦承载圣哲之思。鸣犊口的回响、盼子的戍边、威王的宏论,皆如浪花般融入这条大河,最终汇聚成华夏文明的壮阔篇章。古河虽逝,沃野新生,而文明的韧性永恒延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