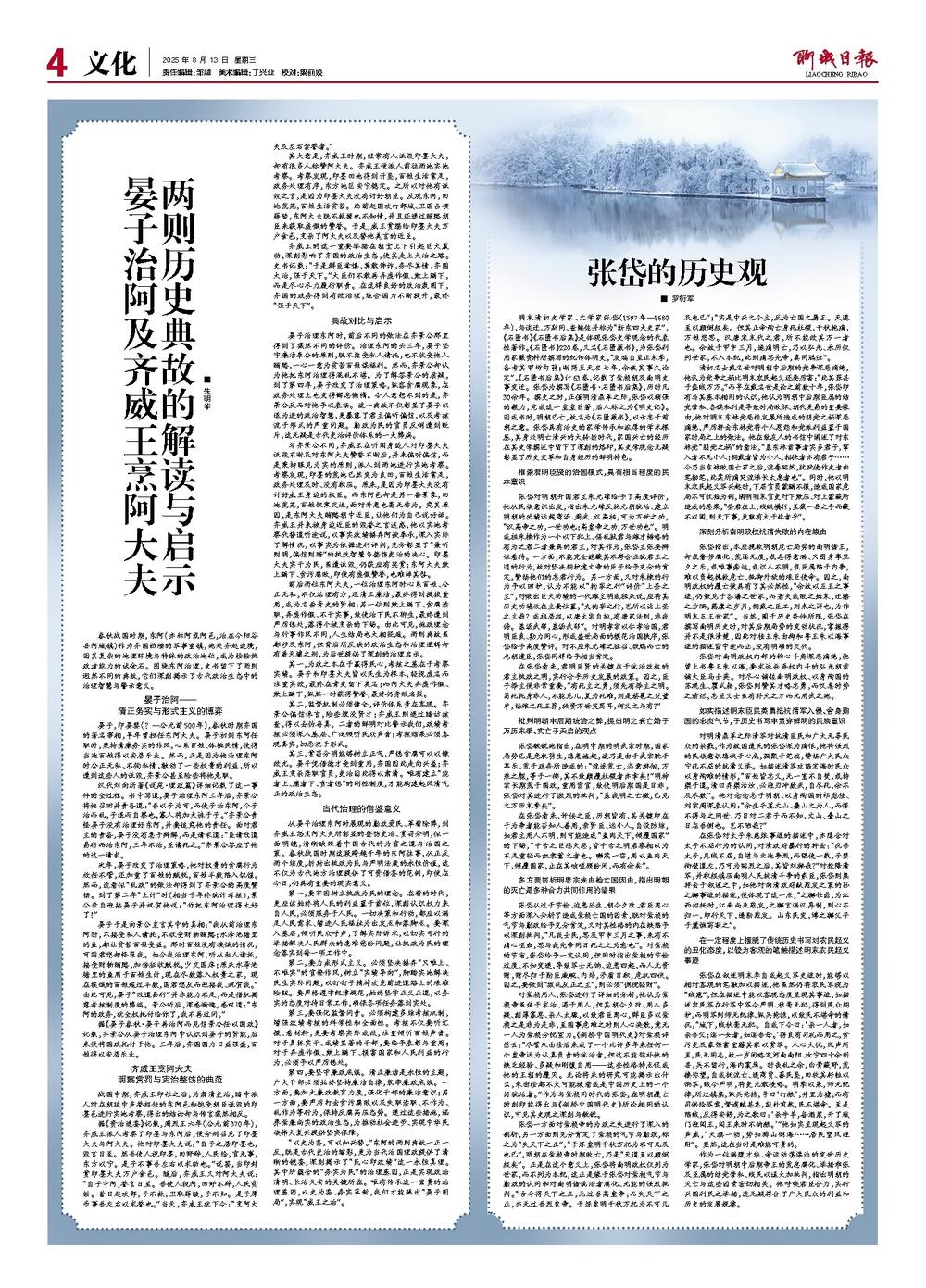张岱的历史观
■ 罗衍军
明末清初史学家、文学家张岱(1597年—1680年),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为“浙东四大史家”,《石匮书》《石匮书后集》是体现张岱史学观念的代表性著作。《石匮书》220卷,又名《石匮藏书》,为张岱利用家藏资料所撰写的纪传体明史,“发端自至正末季,备考其甲坼勾萌;断简至天启七年,余俟其事久论定”。《石匮书后集》计63卷,记载了崇祯朝及南明史事变迁。张岱为撰写《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历时凡30余年。撰史之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张岱以顽强的毅力,完成这一皇皇巨著,后人称之为《明史记》。因成书时,明朝已亡,故名为《石匮藏书》,以示忠于前朝之意。张岱具有治史的家学传承和浓厚的学术根基,其身处明亡清兴的大转折时代,家国兴亡的经历在其史学撰述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史学观念无疑彰显了历史变革和自身经历的鲜明特色。
推崇君明臣贤的治国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本意识
张岱对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从民族意识出发,指出朱元璋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朝的功绩远超商汤、周武、汉高祖,可为万世之功,“汉高帝之功,一世功也;高皇帝之功,万世功也”。明成祖朱棣作为一个以下犯上、倡乱弑君与雄才韬略的有为之君二者兼具的君主,对其作为,张岱主张要辩证看待。一方面,不能完全遮蔽其不符合正统君王之道的行为,故对坚决拥护建文帝的臣子给予充分的肯定,赞扬他们的忠君行为。另一方面,又对朱棣的行为予以回护,认为不能以“拘挛之行”评价“上圣之主”,对做出巨大功绩的一代雄主明成祖来说,应将其历史功绩放在主要位置,“夫拘挛之行,岂所以论上圣之主哉?成祖居极,以唐太宗自拟,有唐家法则,非我俦。盖汤武耶,盖汤武耶”。对明孝宗以仁孝治国,君明臣良、勠力同心,形成盛世局面的模范治国秩序,张岱给予高度赞许。对不应朱元璋之征召、饮鸩而亡的元朝遗臣,张岱同样给予相当肯定。
在张岱看来,君明臣贤的关键在于统治政权的君主执政之明,实行合乎历史发展的政策。因之,臣子择主便非常重要,“有死主之勇,须先有择主之明。苟死托身非人,不能见几,复为死难,则是蔡邕之哭董卓,扬雄之死王莽,徒资万世笑骂耳,何义之与有?”
批判明朝中后期统治之弊,提出明之衰亡始于万历末季、实亡于天启的观点
张岱敏锐地指出,在明中期的明武宗时期,国家局势已是危机萌生,隐患迭起,这乃是由于武宗耽于享乐、荒于政务所造成的:“流连荒亡,恣意游佃,万乘之躯,等于一掷,其不致颠覆社稷者亦幸矣!”明神宗长期荒于国政,重用宦官,致使明后期国是日非,张岱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盖我明之亡徵,已见之万历末季矣”。
在张岱看来,奸佞之臣,历朝皆有,其关键即在于为帝者能否知人善用,亲贤臣、远小人,自设防维,如君主用人不明,则可能造成“鱼肉天下,倾覆国家”的下场,“千古之巨怼大恶,皆千古之明君察相以为不足重轻而奴隶蓄之者也。嚬茂一窃,用以鱼肉天下,倾覆国家,止在其咄嗟顾盼间,而有余矣”。
多方面剖析明思宗朱由检亡国因由,指出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张岱从过于节俭、边患丛生、朝令夕改、君臣离心等方面深入分析了造成崇祯亡国的因素,既对崇祯的气节与勤政给予充分肯定,又对其性格的内在缺陷予以深刻批判,“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对崇祯的节省,张岱给予一定认同,但同时指出崇祯的节俭过度、不知变通,导致军士无饷、边患四起,而人无资财,财尽归于勋臣戚畹、内珰,矛盾日积,危机四伏。因之,要做到“拨乱反正之主”,则必须“倜傥轻财”。
对崇祯用人,张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崇祯帝虽焦于求治、渴于用人,但其朝令夕改、用人多疑、刻薄寡恩、杀人太骤,以致君臣离心,群臣多以崇祯之是非为是非,至国事危难之时则人心涣散,竟无一人为崇祯分忧宣力。《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崇祯评价云:“尽管朱由检后来成了一个比许多年来任何一个皇帝远为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这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促成他的王朝的覆灭。无论将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么,朱由检都不大可能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统治者。”作为与崇祯同时代的张岱,在明朝覆亡时刻即能得出与《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论相同的认识,可见其史观之深刻与敏锐。
张岱一方面对崇祯帝的为政之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另一方面则充分肯定了崇祯的气节与勤政,称之为“失天下之正”,“于烁皇明千秋万祀为不可几及也已”,明朝在崇祯帝时期败亡,乃是“天道至以颠倒极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岱将南明政权仅列为世家,而不列为本纪,这正是缘于张岱对崇祯气节与勤政的认同和对南明诸统治者腐化、无能的强烈批判。“古今得天下之正,无过吾高皇帝;而失天下之正,亦无过吾烈皇帝。于烁皇明千秋万祀为不可几及也已”;“实是中兴之令主,反为亡国之孱王。天道至以颠倒极矣。但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万姓悲思。汉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万一者也。余故于甲申三月,遂痛明亡,乃以弘光、永历仅列世家,不入本纪,此则痛思先帝,真同鹃泣”。
清初名士戴名世对明朝中后期的党争深恶痛绝,他认为党争之祸比明末农民起义还要厉害:“此其罪甚于盗贼万万。”而早在戴名世是论之前数十年,张岱即有与其基本相同的认识,他认为明朝中后期臣属的结党营私、各谋私利是导致时局败坏、朝代更易的重要缘由,他对明末东林党恶性发展所造成的朋党之祸深恶痛绝,严厉抨击东林党将个人恩怨和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时局之上的做法。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阐述了对东林党“朋党之祸”的看法,“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今乃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此某所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同时,他以明末农民起义军兴起时,下层官员蒙瞒不报,造成国家危局不可收拾为例,阐明明末官吏对下欺压、对上蒙蔽所造成的恶果,“圣君在上,残贼横行,至截一县之手而蔽不以闻,则天下事,更孰有大于此者乎”。
深刻分析南明政权抗清失败的内在缘由
张岱指出,本应挽救明朝危亡局势的南明诸王,却或奢侈腐化、荒淫无度,或志得意满、只图身享旦夕之乐,或唯事奔逃,或识人不明,或臣属陷于内争,难以负起挽救危亡、抵御外敌的艰巨使命。因之,南明政权的覆亡便具有了其必然性,“余故以五王之事迹,仍散见于各藩之世家,而若夫成败之始末,迁播之方隅,羁縻之岁月,拥戴之臣工,则未之详也,为作明末五王世家”。当然,囿于历史条件所限,张岱在撰写南明历史时,对其后期局势的变动状况,掌握得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对桂王朱由榔和鲁王朱以海事迹的描述皆中途而止,没有明确的交代。
张岱对南明政权内部的钩心斗角深恶痛绝,他曾上书鲁王朱以海,要求诛杀弄权内斗的弘光朝首辅大臣马士英。对尽心辅佐南明政权、以身殉国的苏观生、瞿式耜,张岱则赞其才略忠勇,而叹息时势之溃烂,忠臣义士虽有补天之才而无用武之地。
如实描述明末臣民英勇抵抗清军入侵、舍身殉国的忠贞气节,于历史书写中贯穿鲜明的民族意识
对明清鼎革之际清军对抗清臣民和广大无辜民众的杀戮,作为故国遗民的张岱深为痛恨,他将强烈的民族意识隐伏于心底,凝聚于笔端,赞扬广大民众宁死不屈的抗清义举。如描述清军攻陷定海时民众以身殉难的情形,“百姓皆忠义,无一室不自焚,或持槊于道,清曰弃槊活汝,必迎刃冲数武,自尽死,余不及尽数”。他对念念忠于明朝、以身殉国的祁彪佳、刘宗周深表认同:“余生平慕文山、叠山之为人,而恨不得与之同世,乃日对二君子而不知,文山、叠山之日在吾侧也。岂不陋哉?”
在张岱对太子朱慈烺事迹的描述中,亦隐含对太子不屈行为的认同,对清政府暴行的抨击:“况吾太子,见贼不屈,自堪与北地争烈,而猥使一载,子婴衔璧道左,乃可为昭烈之后,其皆刘禅哉?”对投降清军,并积极镇压南明人民抗清斗争的贰臣,张岱则集抨击于叙述之中,如他对向清政府献薙发之策的孙之獬事迹的描述,便体现了这一点,“之獬仕卤,为江西招抚时,江南尚未薙发,之獬言满汉异制,则心不归一,即行天下,逼勒薙发。山东民变,缚之獬父子于麓谯脔割之”。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历史书写对农民起义的丑化态度,以较为客观的笔触描述明末农民起义事迹
张岱在叙述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史迹时,能够以相对客观的笔触加以描述,他虽然仍将农民军视为“贼寇”,但在描述中能以客观态度呈现其事迹,如描述农民军在行军中军令严明、秋毫无犯,得到民众拥护,而明军则师无纪律、纵兵抢掠,以致民不堪命的情况,“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蕃民垦,田牧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他如实呈现起义军的声威,“大旗一动,势如排山倒海……居民望风迎附”。显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位满腹才华、命运动荡漂泊的变世历史学家,张岱对明朝中后期帝王的荒怠腐化、举措乖张及臣属的结党营私、残民以逞大加批判,指出明朝的灭亡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他呼唤君臣合力,实行兴国利民之举措,这无疑符合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和历史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