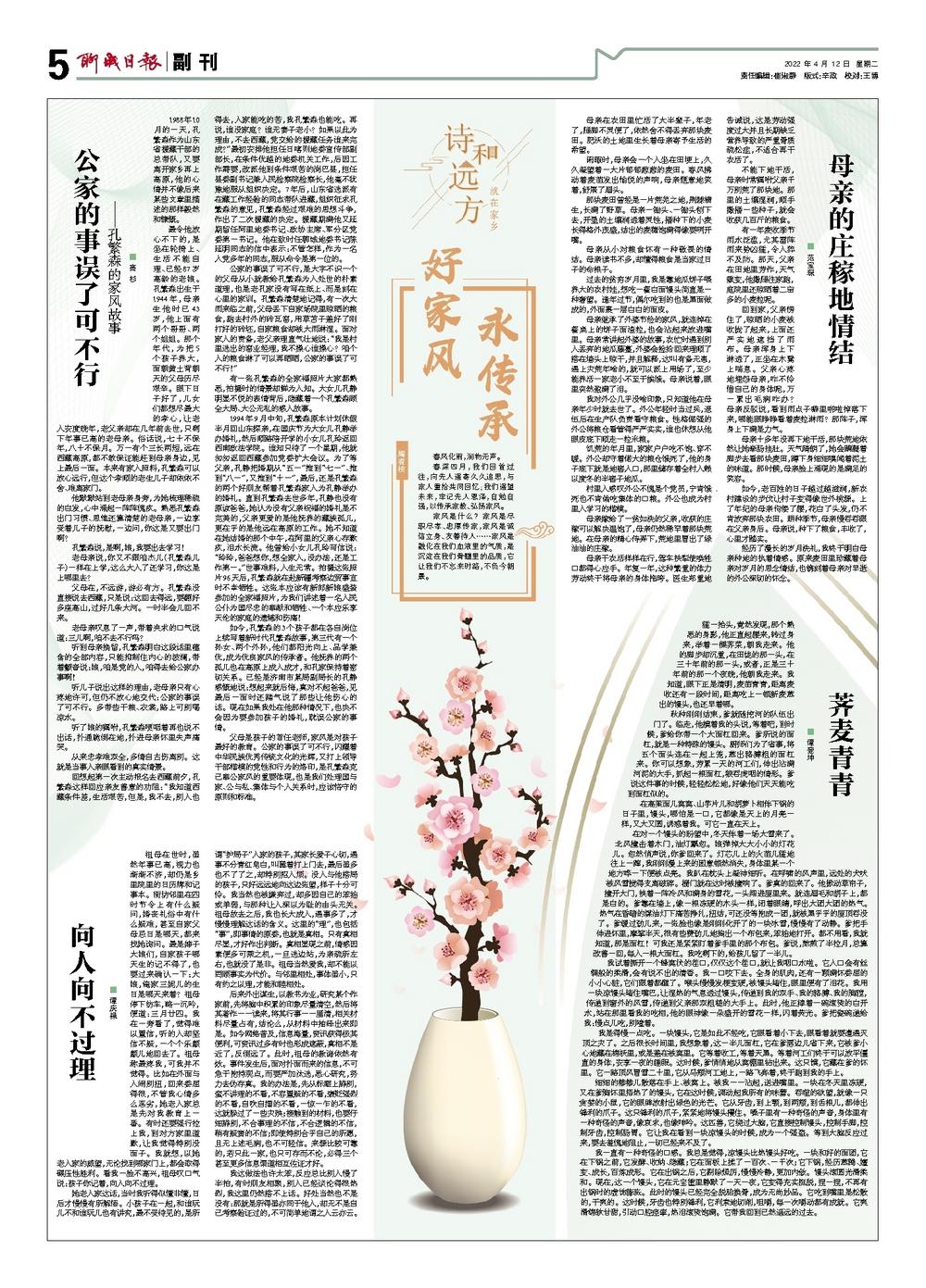好家风 永传承
编者按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春深四月,我们回首过往,向先人遥寄久久追思,与家人重拾共同回忆;我们遥望未来,牢记先人恩泽,自勉自强,以传承家教、弘扬家风。
家风是什么?家风是尽职尽孝、忠厚传家,家风是诚信立身、友善待人……家风是融化在我们血液里的气质,是沉淀在我们骨髓里的品质,它让我们不忘来时路,不负今朝景。
公家的事误了可不行
——孔繁森的家风故事
■ 高 杉
1988年10月的一天,孔繁森作为山东省援藏干部的总带队,又要离开家乡再上高原,他的心情并不像后来某些文章里描述的那样毅然和慷慨。
最令他放心不下的,是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已经87岁高龄的老娘。孔繁森出生于1944年,母亲生他时已43岁,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那个年代,为把5个孩子养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历尽艰辛。眼下日子好了,儿女们都想尽最大的孝心,让老人安度晚年,老父亲却在几年前去世,只剩下年事已高的老母亲。俗话说,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远在西藏高原,都不敢保证能赶到母亲身边,见上最后一面。本来有家人照料,孔繁森可以放心远行,但这个孝顺的老生儿子却依依不舍、难离家门。
他默默站到老母亲身旁,为她梳理稀疏的白发,心中涌起一阵阵愧疚。熟悉孔繁森出门习惯、思维还算清楚的老母亲,一边享受着儿子的抚慰,一边问,你这是又要出门啊?
孔繁森说,是啊,娘,我要出去学习!
老母亲说,你又不跟咱杰儿(孔繁森儿子)一样在上学,这么大人了还学习,你这是上哪里去?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繁森没直接说去西藏,只是说:这回去得远,要翻好多座高山,过好几条大河。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老母亲叹息了一声,带着央求的口气说道:三儿啊,咱不去不行吗?
听到母亲挽留,孔繁森明白这段话里蕴含的全部内容,只能抑制住内心的波澜,带着颤音说:娘,咱是党的人,咱得去给公家办事啊!
听儿子说出这样的理由,老母亲只有心疼地许可,但仍不放心地交代:公家的事误了可不行。多带些干粮、衣裳,路上可别喝凉水。
听了娘的嘱咐,孔繁森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扑通跪倒在地,扑进母亲怀里失声痛哭。
从来忠孝难双全,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就是当事人亲眼看到的真实情景。
回想起第一次主动报名去西藏前夕,孔繁森这样回应亲友善意的劝阻:“我知道西藏条件差,生活艰苦,但是,我不去,别人也得去,人家能吃的苦,我孔繁森也能吃。再说,谁没家庭?谁无妻子老小?如果以此为理由,不去西藏,党交给的援藏任务谁来完成?”最初安排他担任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条件优越的地委机关工作,后因工作需要,改派他到条件艰苦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7年后,山东省选派有在藏工作经验的同志带队进藏,组织征求孔繁森的意见,孔繁森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作出了二次援藏的决定。援藏期满他又延期留任阿里地委书记、政协主席、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在致时任聊城地委书记陈延明同志的信中表示:不管怎样,作为一名入党多年的同志,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
公家的事误了可不行,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父母从小就教给孔繁森为人处世的朴素道理,也是老孔家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刻在心里的家训。孔繁森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大雨来临之前,父母丢下自家场院里晾晒的粮食,跑去村外的砖瓦窑,用草苫子盖好了刚打好的砖坯,自家粮食却被大雨淋湿。面对家人的责备,老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村里选出的窑业经理,我不操心谁操心?咱个人的粮食淋了可以再晒晒,公家的事误了可不行!”
有一张孔繁森的全家福照片大家都熟悉,拍摄时的情景却鲜为人知。大女儿孔静明显不悦的表情背后,隐藏着一个孔繁森顾全大局、大公无私的感人故事。
1994年9月中旬,孔繁森原本计划休假半月回山东探亲,在国庆节为大女儿孔静举办婚礼,然后顺路陪开学的小女儿孔玲返回西南政法学院。谁知只待了一个星期,他就匆匆返回西藏参加党委扩大会议。为了等父亲,孔静把婚期从“五一”推到“七一”、推到“八一”,又推到“十一”,最后,还是孔繁森的两个好朋友帮着孔繁森家人为孔静举办的婚礼。直到孔繁森去世多年,孔静也没有原谅爸爸,她认为没有父亲祝福的婚礼是不完美的,父亲更爱的是他抚养的藏族孤儿,更在乎的是他远在高原的工作。她不知道在她结婚的那个中午,在阿里的父亲心存歉疚,泪水长流。他曾给小女儿孔玲写信说:“玲玲,爸爸想你,想全家人,没办法,还是工作第一。”世事难料,人生无常。拍摄这张照片96天后,孔繁森就在赴新疆考察边贸事宜时不幸牺牲。这张本应该有新郎新娘盛装参加的全家福照片,为我们讲述着一名人民公仆为国尽忠的奉献和牺牲、一个本应乐享天伦的家庭的遗憾和伤痛!
如今,孔繁森的3个孩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续写着新时代孔繁森故事,第三代有一个孙女、两个外孙,他们都阳光向上、品学兼优,成为优良家风的传承者。他抚养的两个孤儿也在高原上成人成才,和孔家保持着密切关系。已经是济南市某局副局长的孔静感慨地说:想起来就后悔,真对不起爸爸,见最后一面时还赌气说了那些让他伤心的话。现在如果我处在他那种情况下,也决不会因为要参加孩子的婚礼,耽误公家的事情。
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家风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公家的事误了可不行,闪耀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又打上领导干部楷模的党性和行为的烙印,是孔繁森克己奉公家风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处理国与家、公与私、集体与个人关系时,应该恪守的原则和标准。
向人向不过理
■ 谭庆禄
祖母在世时,虽然年事已高,视力也渐渐不济,却仍是乡里院里的日历牌和记事本。街坊邻里在四时节令上有什么疑问,婚丧礼俗中有什么疑难,甚至自家父母忌日是哪天,都来找她询问。最是婶子大娘们,自家孩子哪天生的记不得了,也要过来确认一下:大娘,俺家三妮儿的生日是哪天来着?祖母停下纺车,略一沉吟,便道:三月廿四。我在一旁看了,觉得难以置信,听的人却坚信不疑,一个个乐颠颠儿地回去了。祖母称最疼我,可我并不觉得。比如在外面与人闹别扭,回来委屈得很,不管我心情多么恶劣,她老人家总是先对我教育上一番。有时还要强行拉上我,到对方家里道歉,让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想,以她老人家的威望,无论找到哪家门上,都会取得碾压性胜利。看我一脸不高兴,祖母叹口气说:孩子你记着,向人向不过理。
她老人家这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日后才慢慢有所解悟。小孩子在一起,和谁玩儿不和谁玩儿也有讲究,最不受待见的,是所谓“护局子”人家的孩子,其家长爱子心切,遇事不分青红皂白,叫嚣着打上门去,最后虽多也不了了之,却特别招人烦。没人与他搭局的孩子,只好远远地向这边张望,样子十分可怜。我当然也被嫌弃过,却多因自己的笨拙或单弱,与那种让人深以为耻的由头无关。祖母故去之后,我也长大成人,遇事多了,才慢慢理解这话的含义。这里的“理”,也包括“事”,即事情的原委,也就是真相。只有真相尽显,才好作出判断。真相显现之前,情感因素便多可乘之机,一旦选边站,为亲疏所左右,也就没了是非。祖母当然爱我,却不能以罔顾事实为代价。与邻里相处,事体虽小,只有约之以理,才能和睦相处。
后来外出谋生,以教书为业,研究某个作家前,先将脑中积累的印象尽量清空,然后将其著作一一读来,将其行事一一厘清,相关材料尽量占有,结论么,从材料中抽绎出来即是。如今网络普及,信息海量,资讯获得极其便利,可资讯过多有时也形成遮蔽,真相不是近了,反倒远了。此时,祖母的教诲依然有效。事件发生后,面对扑面而来的信息,不可急于抱持观点,而要严加汰选,悉心研究,努力去伪存真。我的办法是,先从标题上辨别,蛮不讲理的不看,不容置疑的不看,褒贬强烈的不看,自吹自擂的不看,一惊一乍的不看,这就躲过了一些灾殃;接触到的材料,也要仔细辨别,不合事理的不信,不合逻辑的不信,稍有疑窦的不信;即使特别合乎自己的所愿,且无上述毛病,也不可轻信。来源比较可靠的,若只此一家,也只可存而不论,必得三个甚至更多信息渠道相互佐证才好。
我这做法也许太笨,反应总比别人慢了半拍,有时朋友相聚,别人已经谈论得很热烈,我这里仍然搭不上话。好处当然也不是没有:那就是所得虽亦同于他人,却无不是自己考察验证过的,不可简单地谓之人云亦云。
母亲的庄稼地情结
■ 范宝琛
母亲在农田里忙活了大半辈子,年老了,腿脚不灵便了,依然舍不得丢弃那块麦田。肥沃的土地里生长着母亲寄予生活的希望。
闲暇时,母亲会一个人坐在田埂上,久久凝望着一大片郁郁葱葱的麦田。春风拂动着麦苗发出愉悦的声响,母亲惬意地笑着,舒展了眉头。
那块麦田曾经是一片荒芜之地,荆棘横生,长满了野草。母亲一锄头、一锄头刨下去,开垦的土壤润透着灵性,播种下的小麦长得格外茂盛,结出的麦穗饱满得像要咧开嘴。
母亲从小对粮食怀有一种敬畏的情结。母亲读书不多,却懂得粮食是当家过日子的命根子。
过去的贫穷岁月里,我是靠地瓜饼子喂养大的农村娃,想吃一餐白面馒头简直是一种奢望。逢年过节,偶尔吃到的也是黑面做成的,外面裹一层白白的面皮。
母亲继承了外婆节俭的家风,就连掉在餐桌上的饼子面渣粒,也会沾起来放进嘴里。母亲常讲起外婆的故事,农忙时遇到别人丢弃的地瓜藤蔓,外婆会捡拾回来理顺了搭在墙头上晾干,并且解释,这叫有备无患,遇上灾荒年啥的,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至少能养活一家老小不至于挨饿。母亲说着,眼里突然盈满了泪。
我对外公几乎没啥印象,只知道他在母亲年少时就去世了。外公年轻时当过兵,退伍后在生产队负责看守粮食。性格倔强的外公将粮仓看管得严严实实,谁也休想从他眼皮底下顺走一粒米粮。
饥荒的年月里,家家户户吃不饱、穿不暖。外公却守着偌大的粮仓饿死了,他的身子底下就是地窖入口,那里储存着全村人赖以度冬的半窖子地瓜。
村里人感叹外公不愧是个党员,宁肯饿死也不肯偷吃集体的口粮。外公也成为村里人学习的楷模。
母亲嫁给了一贫如洗的父亲,收获的庄稼可以解决温饱了,母亲仍然稀罕着那块荒地。在母亲的精心侍弄下,荒地里冒出了绿油油的庄稼。
母亲干农活样样在行,驾车扶犁使唤牲口都得心应手。年复一年,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终于将母亲的身体拖垮。医生郑重地告诫说,这是劳动强度过大并且长期缺乏营养导致的严重骨质疏松症,不适合再干农活了。
不能下地干活,母亲时常嘱咐父亲千万别荒了那块地。那里的土壤湿润,顺手撒播一些种子,就会收获几百斤的粮食。
有一年麦收季节雨水泛滥,尤其雷阵雨来势凶猛,令人猝不及防。那天,父亲在田地里劳作,天气骤变,他撒腿往家跑,庭院里还晾晒着二亩多的小麦粒呢。
回到家,父亲愣住了,晾晒的小麦被收拢了起来,上面还严实地遮挡了雨布。母亲浑身上下淋透了,正坐在木凳上喘息。父亲心疼地埋怨母亲,咋不怜惜自己的身体呢,万一累出毛病咋办?母亲反驳说,看到雨点子噼里啪啦掉落下来,哪能眼睁睁看着麦粒淋雨?那阵子,浑身上下满是力气。
母亲十多年没再下地干活,那块荒地依然让她牵肠挂肚。天气晴朗了,她会蹒跚着脚步去看那块麦田,蹲下身细细嗅闻着泥土的味道。那时候,母亲脸上涌现的是满足的笑容。
如今,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滋润,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让村子变得像世外桃源。上了年纪的母亲佝偻了腰,花白了头发,仍不肯放弃那块农田。耕种季节,母亲慢吞吞跟在父亲身后。母亲说,种下了粮食,丰收了,心里才踏实。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洗礼,我终于明白母亲种地的执着情感。原来麦田里珍藏着母亲对岁月的思念情结,也镌刻着母亲对早逝的外公深切的怀念。
荠麦青青
■ 谭登坤
猛一抬头,竟然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正直起腰来,转过身来,举着一棵荠菜,朝我走来。他的脚步却沉重,在田垅的那一头,在三十年前的那一头,或者,正是三十年前的那一个夜晚,他朝我走来。我知道,眼下正是清明,麦苗青青,距离麦收还有一段时间,距离吃上一顿新麦蒸出的馒头,也还早着哪。
秋种刚刚结束,爹就随挖河的队伍出门了。临走,他摸着我的头说,等着吧,到时候,爹给你带一个大面杠回来。爹所说的面杠,就是一种特殊的馒头。厨师们为了省事,将五个面头连在一起上笼,蒸出胳膊粗的面杠来。你可以想象,劳累一天的河工们,伸出沾满河泥的大手,抓起一根面杠,狼吞虎咽的情形。爹说这件事的时候,轻轻松松地,好像他们天天能吃到面杠似的。
在高粱面儿窝窝、山芋片儿和胡萝卜相伴下锅的日子里,馒头,哪怕是一口,它都像是天上的月亮一样,又大又圆,诱惑着我。可它一直在天上。
在对一个馒头的盼望中,冬天伴着一场大雪来了。北风撞击着木门,油灯飘忽。娘弹掉大大小小的灯花儿。忽然悄声说,你爹回来了。灯芯儿上的火苗儿猛地往上一蹿,我刚刚漫上来的困意顿然消失,身体里某一个地方哗一下便被点亮。我趴在枕头上凝神细听。在呼啸的风声里,远处的犬吠被风雪搅得支离破碎。栅门就在这时被撞响了。爹真的回来了。他掀动草帘子,撞开大门,挟着一阵冷风和满身的雪花,一头闯进屋里来。就连眉毛和胡子上,都是白的。爹靠在墙上,像一根冻硬的木头一样,闭着眼睛,呼出大团大团的热气。热气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痛苦挣扎,扭结,可还没等抱成一团,就被黑乎乎的屋顶吞没了。爹缓过劲儿来,一张脸也像是刚刚化开了的一块冰雪,慢慢有了动静。爹把手伸进怀里,摩挲半天,很有些费劲儿地掏出一个布包来,笨拙地打开。都不用看,我就知道,那是面杠!可我还是紧紧盯着爹手里的那个布包。爹说,熬煎了半拉月,总算改善一回,每人一根大面杠。我吃剩下的,给孩儿留了一半儿。
我试着撕开一个蜂窝状的茬口,仅仅这个茬口,就让我咽口水啦。它入口会有丝绸般的柔滑,会有说不出的清香。我一口咬下去。全身的肌肉,还有一颗满怀委屈的小小心脏,它们跟着都醒了。喉头慢慢发梗变硬,被馒头堵住,眼里便有了泪花。我用一块凉馒头堵住嘴巴,让湿热的气息透过馒头,传递到我的双手、我的胳膊、我的胸膛,传递到窗外的风雪,传递到父亲那双粗糙的大手上。此时,他正捧着一碗滚烫的白开水,站在那里看我的吃相,他的眼神像一朵盛开的雪花一样,闪着荧光。爹把瓷碗递给我:慢点儿吃,别噎着。
我是得慢一点吃。一块馒头,它是如此不经吃,它眼看着小下去,眼看着就要遭遇灭顶之灾了。之后很长时间里,我想象着,这一半儿面杠,它在爹唇边儿省下来,它被爹小心地藏在棉袄里,或是盖在被窝里。它等着收工,等着天黑。等着河工们终于可以放平僵直的身体,安享一夜的睡眠。这时候,爹悄悄地从窝棚里钻出来。这只馍,它藏在爹的怀里。它一路顶风冒雪二十里,它从马颊河工地上,一路飞奔着,终于跑到我的手上。
细细的糁糁儿散落在手上、被窝上。被我一一沾起,送进嘴里。一块在冬天里冻硬,又在爹胸怀里捂热了的馒头,它在这时候,调动起我所有的味蕾。吞噬的欲望,就像一只贪婪的小鼠,它的眼眸放射出绿色的光芒。它从牙齿,到上颚,到两颊,到舌根儿,都伸出锋利的爪子。这只锋利的爪子,紧紧地将馒头攫住。嗓子里有一种奇怪的声音,身体里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像哀求,也像呻吟。这匹兽,它绕过大脑,它直接控制馒头,控制手脚,控制牙齿,控制肠胃。它让我在看到一块凉馒头的时候,成为一个强盗。等到大脑反应过来,要去羞愧地阻止,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口感。我总是觉得,凉馒头比热馒头好吃。一块和好的面团,它在下锅之前,它发酵、收纳、隐藏;它在面板上揉了一百次、一千次;它下锅,经历蒸腾、嬗变、成长,百炼成形。它在出锅之后,它剔除燥厉,慢慢冷静,更加内敛。馒头滚圆光滑柔和。现在,这一个馒头,它在元宝筐里静默了一天一夜,它变得充实挺脱,捏一捏,不再有出锅时的虚饰膨胀。此时的馒头已经完全脱胎换骨,成为无尚妙品。它吃到嘴里是松散的,干爽的。这时候,牙齿也特别锋利,它利索地切削,咀嚼,每一次嚼动都有成就。它爽滑绵软甘甜,引动口腔痉挛,热泪滚烫饱满。它带我回到已然遥远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