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原野漫步
聊城 安格
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着急忙慌,打那之后,冬天的氛围就越来越浓了。周末回老家,午饭后,难得团聚的孩子们在一起嬉戏,家里人喝茶聊天。我说要到地里看看;爹娘说地里的庄稼都已收割,没啥好看的。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思。酒后微醺的我,径自往村南走去……
冬日里的白杨树卸下华丽的妆容,在小路边站成两列,在荒野里排成方队,更显威武;树干和枝丫一律向上,坦诚地迎接温暖的日光;零星的叶子在风中飘摇,抒发着依恋的咏叹调。长尾喜鹊竟然成群地落在树林里的地面上,鸣声嘈杂,闹得耳朵不敢相信原野的静谧。“哦吼——”冲它们大声喊上一嗓子,它们倏然飞起,在半空中盘旋片刻,又吵嚷着栖于枝头。
我喜欢一种纤细、安静且文雅的植物,它们在低洼的水塘边,春天萌绿,夏日旖旎,秋日丰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写尽它们的空灵缥缈;“一枝持赠朝天人,愿比蓬莱殿前雪”,夸赞其花穗之圣洁。瞧啊,四野凋零,冬天的芦苇聚在一起,毫不在意褴褛的衣衫,任白絮飘零,沉默、庄严、倔强地挺立在鲁西大地,等待季节的轮回。
芦苇不孤独,和它们做伴的,除了白杨树,还有麦苗儿。冬小麦的青苗,手挽手从土里钻出来,给光秃秃的土地一点颜色,尽管不怎么茁壮,尽管远望去若隐若现。但,这些苗儿关乎农人对生活的殷切期望。前几日,新开的一家餐厅,门口摆着“大麦”花篮,寓意着“大卖”、生意兴隆。老婆孩子享受着精美的食物,我却在回忆着少年时候饿肚子的时光。小时候,顿顿能吃白面馒头,就是我最大的奢望。父母的念想,却不止于此。他们巴望着每一个孩子都好好读书,到遥远的城里工作。的确,每一个孩子,都像麦收时节农村打麦场里的麦糠,被爹娘拼尽力气高高扬起,然后尽可能地乘风而去、远走高飞。
哦,我的爹娘!
麦苗儿颤动,萧瑟朔风吹酒醒,微冷。关于村子南边这片田野的记忆,一下子鲜活起来。就是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晨露曾经打湿我的鞋子和裤管儿,爷爷的羊群啃着草,惊起草丛中的蚂蚱;曾经,邻村的黄狗铆足了劲,追着狂奔的野兔;曾经,小伙伴刚刚刨出来的地瓜、撸下来的黄豆,被火苗包围起来,终成香喷喷的食物;曾经,晚秋的落日映照着回家的羊牛驴骡,颇有点“牧人驱犊返”的意蕴……曾经挎着篮子拾麦子,以换来几块冰糕祛暑;曾经拿着三齿(一种农具)翻出来的地瓜,放到炉子边焖烤一夜,早晨就是美味。曾经的美味,还有软嫩的鸡蛋荷包、成串的烤蚂蚱、老屋后面井边的杜梨儿、冬天吃也吃不完的腌豆豉……
这份记忆不仅仅属于我,还属于我所有儿时的伙伴,属于我的亲人,属于村子里的乡亲,属于生活在这片热土以及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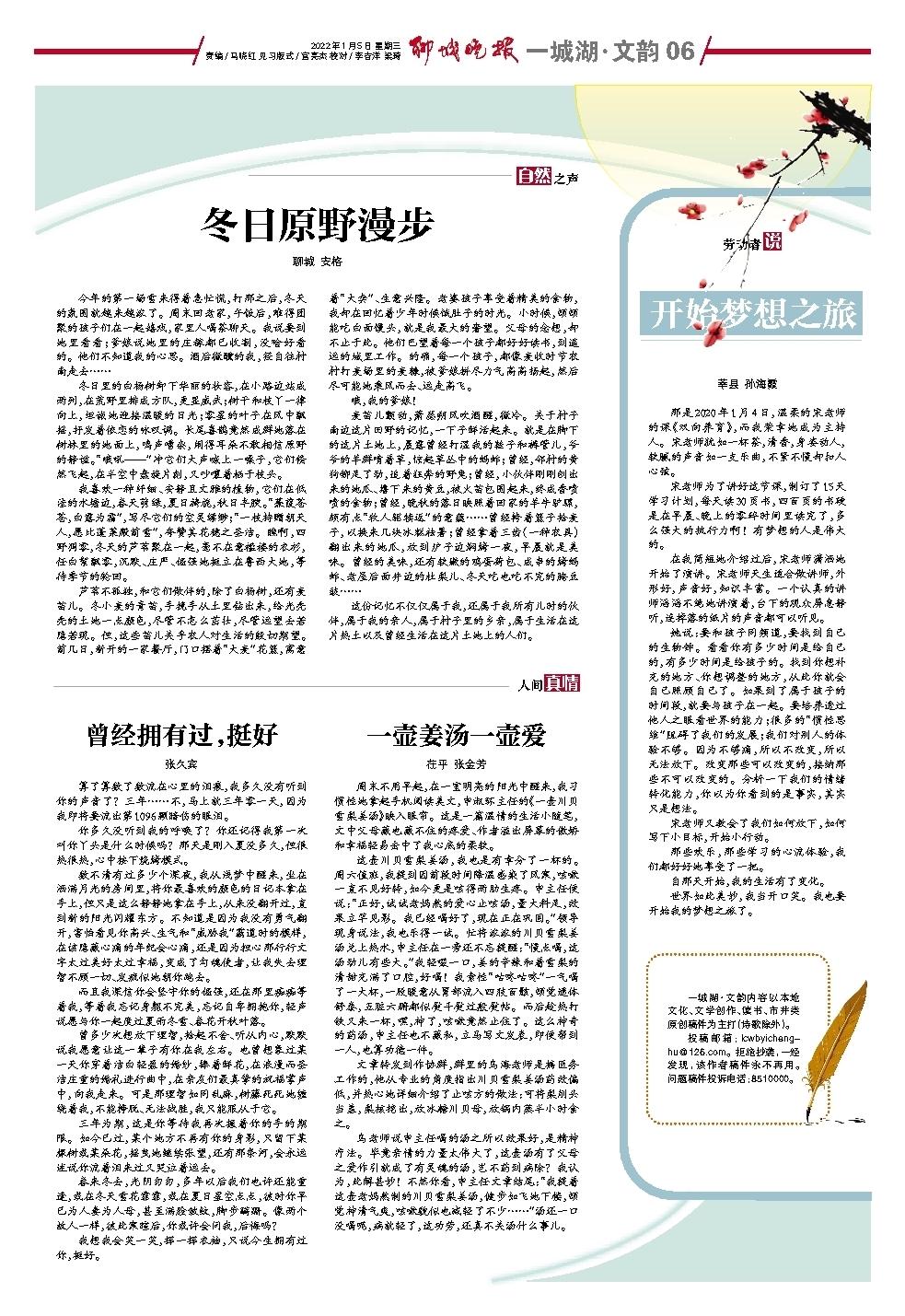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