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儿时端午
○ 张清明
桌上摆放的油炸鱼鳅粑、桐子叶麦粑、麦粑回锅肉,曾是我家的传统菜。这都是我儿时的最爱,如今成了“思母菜”。
我的童年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度过的。父母挣工分,艰难拉扯着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我是家里的小六。我们家劳力少,挣不齐工分。父亲是大队瓦窑的煤炭采购员,也是一名烧窑师,可以挣些钱补贴家用,加上母亲的精打细算,一家人勉强度日,过节时才能吃上肉。
那些年,春节过后,正是青黄不接之时。端午节前几天,各家各户才能分点小麦、菜籽油,才能“打牙祭”。
从我记事起,家家户户的端午节都很热闹,以吃麦粑为主。一大早,父亲去大队开会,大哥、二姐、三哥出早工,四哥背着麦子去磨面粉。母亲则带我到田边,割一些根壮叶茂的艾蒿、菖蒲回来,挂在门框上。
之后,我按照母亲的吩咐去肉摊拿猪肉。回来后,我和哥哥们爬树摘桐子叶,将鲜嫩宽大的桐子叶清洗后放在筲箕里晾干,用来包桐子叶麦粑。
母亲在木盆里和麦粉,用发酵粉发面炸鱼鳅粑,又在另一个木盆里和面粉,做桐子叶麦粑。姐姐们烧锅煮肉,哥哥们清洗蒸笼,忙得不亦乐乎。
母亲找出钥匙打开木柜的锁,揭开油罐盖,小心翼翼地将菜籽油倒入钵儿里。菜籽油是生产队把油草籽榨成油,按一人一斤分给每户,我家分得8斤。母亲倒油入锅,等到油热,从木盆里抓一小坨面,扯扯捏捏,轻轻放入锅中,一个两个……不一会儿,锅中浮起一个个胖嘟嘟的鱼鳅粑。母亲用筷子夹起熟了的粑,我抓起一个,左手换右手,咬一口,好烫好香。
母亲炸出两大筲箕鱼鳅粑后又烙麦粑,此时桐子叶麦粑已蒸好。切好的肉片装了三大碗,母亲将肉片倒入锅中爆出油,倒入麦粑,锅铲反复铲后,加蒜、辣椒、花椒,厨房里香气四溢。
母亲让我看父亲和哥哥姐姐有没有回来。看到母亲把麦粑回锅肉铲入碗中,我从碗里捏起一块肥肉,跑出厨房。
一家人坐上桌,桌上是黄灿灿的鱼鳅粑、桐子叶麦粑、麦粑回锅肉。父亲倒了一碗雄黄酒,说喝雄黄酒能祛毒,让我们每人喝一口。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生活的好转,鱼鳅粑、桐子叶麦粑、麦粑回锅肉不再是端午的主打菜。平时,母亲若想吃,我做,母亲当烧锅匠。
如今,看到老屋门框上挂的艾蒿、菖蒲,桌上摆着鱼鳅粑、麦粑回锅肉,桌旁却不见慈祥的母亲。
又是一年端午至。我左手端着酒杯,右手夹起一个鱼鳅粑,儿时母亲爱说的话在耳旁回荡:“小六子啊,慢点吃,别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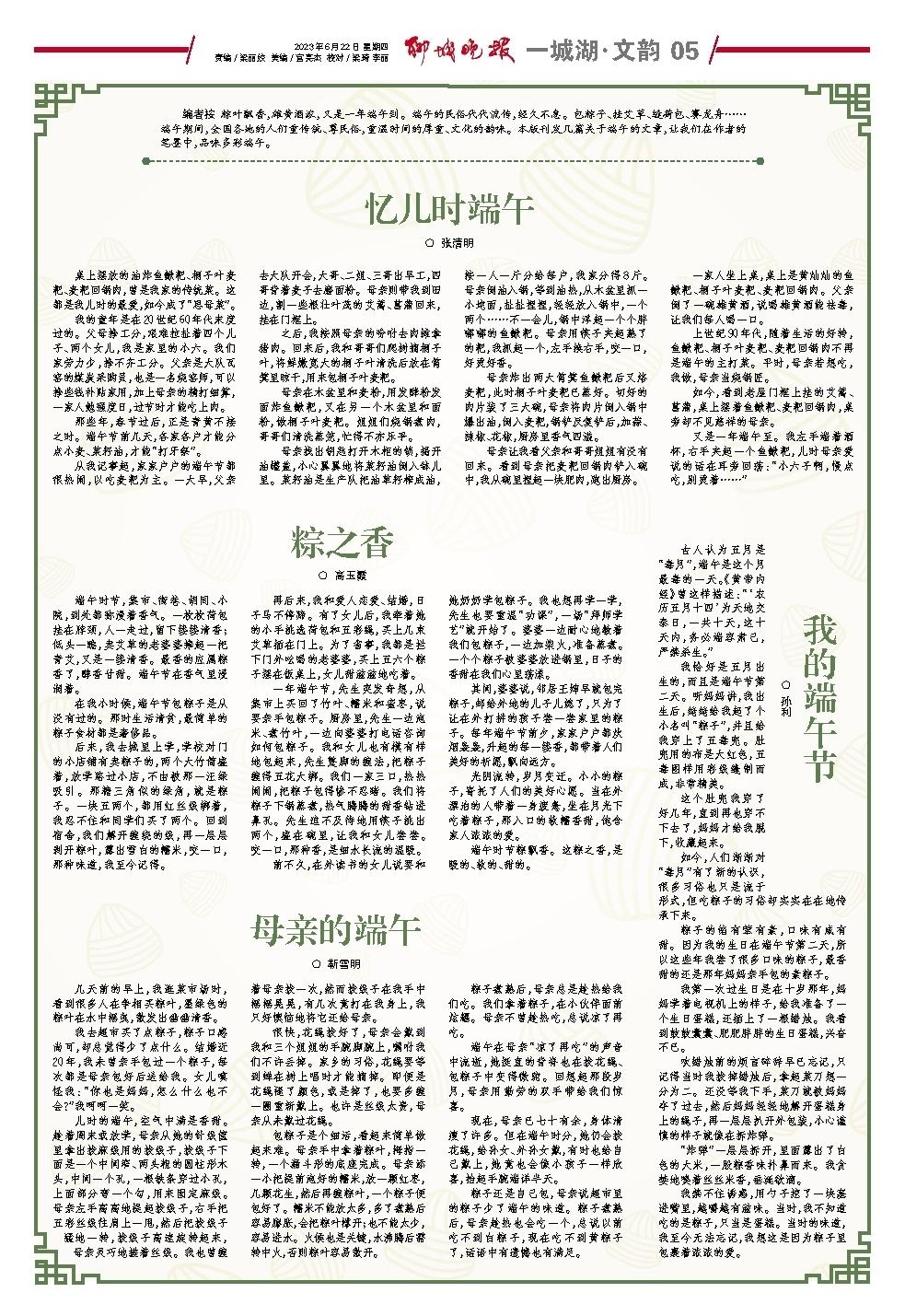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