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绳
□ 刘旭东
20世纪60年代,临清市原文化局副局长、我的老领导和恩师王子华先生,曾经作词、谱曲过一首《打绳歌》。那首歌当年荣获上海之春音乐会一等奖,之后在全国传唱,被山东歌舞剧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保留节目演播多年,并进京到中南海特地为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演唱,受到好评。可见打绳这件事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有过多么重要的意义,受到过怎样的重视。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自古以来就与绳子形影不离。不论是拾柴打草、耕地播种,还是夏收秋收时用大小车辆运送庄稼等,都离不开绳子。现在各种场合使用的绳子,除了钢丝绳,大多是机制的塑料绳,而之前使用的绳子都是用苘麻打成的麻绳。
其实,我的祖辈,尤其是我父亲当年就曾以打麻绳在我们当地知名。我自己也学会了这项手艺,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本人情况的变化,我没有把这项手艺利用起来,也没有传承给我的儿女们。祖传下来的打绳用的工具,如今也只剩下一辆纺经子的车子,和两个打绳时用的木瓜了。
打绳需要用麻经子(我们俗称“经子”)。作为麻绳的半成品,经子是用苘麻茎皮纤维(也称“苘麻”)纺成的。纺经子是打绳前一道重要的工序。其过程是:先将一大缕苘麻用水洒湿一些,使其变得柔软,再将苘麻的细头用一两块条砖压住,然后坐下来,将一两根苘麻系在纺车上。接着,左手按顺时针向怀里方向转动纺车,右手将一根根麻批子接续上去。纺到一定长度,随着纺车的转动,拿着经子的手往右下方一拉一送,就将纺好的这一段经子缠绕在纺车上了。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待纺车上绕满了,绕成一个大圆滚子,就开始卸车子。将经子头从一小节竹筒里穿过来,一手抓着竹筒牵动纺车倒转,一手将纺好的这些经子不断地缠绕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圆球,以备打绳用。
打绳的工具和名称各地不一。我家打绳用的主要有木瓜、大晃板、小晃板、吊钩、大框、大拖、小拖等。除了拴经子用的吊钩是铁制的,其他都是采用质地硬实的枣木、槐木等所制。打绳是两边相对进行。这一边,有两根深埋于地下的短粗的木桩,木桩上安着钻有十几个孔的大框,根据需要在孔上穿入若干“乙”字形吊钩,以备拴经子用。一条大晃板上,留有和大框上数目相同的孔,有弯度的吊钩分别伸入各个孔中。在相距若干米的另一边,是一个能被牵引的木制大拖,大拖后面压上配重用的砖石,大拖的横梁上也钻有几个孔,但比对面大框上的孔要少得多,也根据需要插入若干吊钩。待把经子在两边的吊钩上拴好以后,就开始打绳了。
打绳,是需要先给经子上劲儿的。大框那边按顺时针方向摇动晃板,带动吊钩一块儿转动,经子便一点点被拧上了劲儿,越来越紧。其间在几条经子上放入若干个串在一根短竹条上而带有沟槽的木瓜。木瓜一般是三四道沟槽,有几道沟槽打出来就是几股的绳。这一串夹着经子的木瓜放在一个后面有配重的小拖上。待经子上到合适的紧度(一个人用手随时捻动经子感受着松紧度),大拖这一头就开始摇动小晃板。就这样,两边一起哗啦哗啦打起绳来。当然,都是按顺时针方向,并且尽量保持所转的圈数一致。小拖就在两边摇动晃板产生的力的作用下,缓缓往前移动着,一根绳或数根麻绳到头儿以后停下晃板,解下新绳的两头。至此,一根根粗细长短不等的新绳就打成了。
我父亲干活仔细,又非常勤奋。一年四季,每天,他都早早起床,点燃屋里的油灯。油灯下,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纺经子。他纺的经子粗细均匀,紧实有度。缠起来的经子团也特别浑圆美观。绳打好之后,他不先把它们解下来,而是拿着一个旧鞋底子把整条新绳从头至尾用力勒一遍,除去毛刺儿,这样绳就更加光滑平顺。然后,再整整齐齐地挽好,放在一起。每逢赶集卖绳的前一天,他还把新绳用硫黄熏一遍,既结实耐用又白亮顺眼。那制作好的一根根新绳就像是一串算盘珠子均匀地排在一起,宛若一件件艺术品,煞是好看。
当年,我父亲的打绳技术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他是跟我爷爷学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有五六家学会了这门手艺,干起了这个行当。尽管我没有将这门技艺继承下来,但很是佩服爷爷和父亲两代人的工匠精神。
父亲身体非常壮实,精神头儿也好,一年四季穿得干干净净,80多岁了还一直坚持打绳赶集。逢集一大早,他便带着自己精心打好的绳去集市展示和交易。打绳除了用来贴补家用,还是他精神上的享受。他早先是骑着一辆“国防”牌自行车,驮着货去赶集,后来又换成了小驴车。过了80岁,父亲还在打绳、赶集,我怎么也阻挡不住,干脆尽量配合他。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手脚渐渐变得迟钝起来,耳朵也有些背了。在我的极力劝告和阻止下,他才不赶集了,但还是不断有买经子买绳的人到家里来。88岁那年,他老人家安安静静地去世了,是当时我们村最高寿的一位老人。他走后,里屋地上留下了一些没有卖完、长短粗细不等的绳和套,我都陆续送给了父亲的外甥们,他们做活用得着。
我怀念早年那忙碌而欢快的打绳场面,我也敬佩老一辈人那勤勉细致、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那绳、那人,带着浓浓的乡愁,是我内心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图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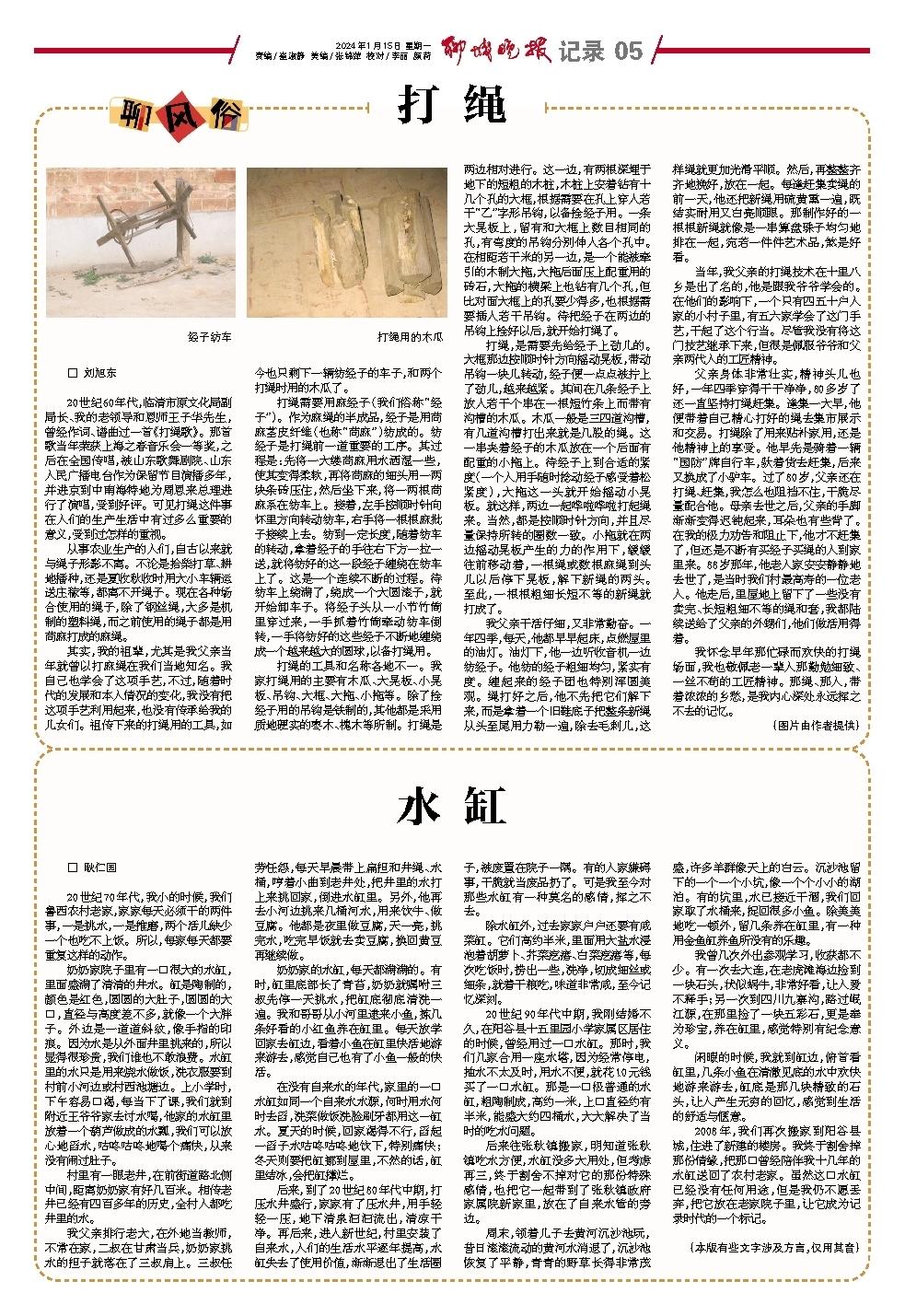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