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缸
□ 耿仁国
20世纪70年代,我小的时候,我们鲁西农村老家,家家每天必须干的两件事,一是挑水,一是推磨,两个活儿缺少一个也吃不上饭。所以,每家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动作。
奶奶家院子里有一口很大的水缸,里面盛满了清清的井水。缸是陶制的,颜色是红色,圆圆的大肚子,圆圆的大口,直径与高度差不多,就像一个大胖子。外边是一道道斜纹,像手指的印痕。因为水是从外面井里挑来的,所以显得很珍贵,我们谁也不敢浪费。水缸里的水只是用来烧水做饭,洗衣服要到村前小河边或村西池塘边。上小学时,下午容易口渴,每当下了课,我们就到附近王爷爷家去讨水喝,他家的水缸里放着一个葫芦做成的水瓢,我们可以放心地舀水,咕咚咕咚地喝个痛快,从来没有闹过肚子。
村里有一眼老井,在前街道路北侧中间,距离奶奶家有好几百米。相传老井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全村人都吃井里的水。
我父亲排行老大,在外地当教师,不常在家,二叔在甘肃当兵,奶奶家挑水的担子就落在了三叔肩上。三叔任劳任怨,每天早晨带上扁担和井绳、水桶,哼着小曲到老井处,把井里的水打上来挑回家,倒进水缸里。另外,他再去小河边挑来几桶河水,用来饮牛、做豆腐。他都是夜里做豆腐,天一亮,挑完水,吃完早饭就去卖豆腐,换回黄豆再继续做。
奶奶家的水缸,每天都满满的。有时,缸里底部长了青苔,奶奶就嘱咐三叔先停一天挑水,把缸底彻底清洗一遍。我和哥哥从小河里逮来小鱼,拣几条好看的小红鱼养在缸里。每天放学回家去缸边,看着小鱼在缸里快活地游来游去,感觉自己也有了小鱼一般的快活。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家里的一口水缸如同一个自来水水源,何时用水何时去舀,洗菜做饭洗脸刷牙都用这一缸水。夏天的时候,回家渴得不行,舀起一舀子水咕咚咕咚地饮下,特别痛快;冬天则要把缸挪到屋里,不然的话,缸里结冰,会把缸撑烂。
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打压水井盛行,家家有了压水井,用手轻轻一压,地下清泉汩汩流出,清凉干净。再后来,进入新世纪,村里安装了自来水,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水缸失去了使用价值,渐渐退出了生活圈子,被废置在院子一隅。有的人家嫌碍事,干脆就当废品扔了。可是我至今对那些水缸有一种莫名的感情,挥之不去。
除水缸外,过去家家户户还要有咸菜缸。它们高约半米,里面用大盐水浸泡着胡萝卜、芥菜疙瘩、白菜疙瘩等,每次吃饭时,捞出一些,洗净,切成细丝或细条,就着干粮吃,味道非常咸,至今记忆深刻。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刚结婚不久,在阳谷县十五里园小学家属区居住的时候,曾经用过一口水缸。那时,我们几家合用一座水塔,因为经常停电,抽水不太及时,用水不便,就花10元钱买了一口水缸。那是一口极普通的水缸,粗陶制成,高约一米,上口直径约有半米,能盛大约四桶水,大大解决了当时的吃水问题。
后来往张秋镇搬家,明知道张秋镇吃水方便,水缸没多大用处,但考虑再三,终于割舍不掉对它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把它一起带到了张秋镇政府家属院新家里,放在了自来水管的旁边。
周末,领着儿子去黄河沉沙池玩,昔日滚滚流动的黄河水消退了,沉沙池恢复了平静,青青的野草长得非常茂盛,许多羊群像天上的白云。沉沙池留下的一个一个小坑,像一个个小小的湖泊。有的坑里,水已接近干涸,我们回家取了水桶来,捉回很多小鱼。除美美地吃一顿外,留几条养在缸里,有一种用金鱼缸养鱼所没有的乐趣。
我曾几次外出参观学习,收获都不少。有一次去大连,在老虎滩海边捡到一块石头,状似蜗牛,非常好看,让人爱不释手;另一次到四川九寨沟,路过岷江源,在那里捡了一块五彩石,更是奉为珍宝,养在缸里,感觉特别有纪念意义。
闲暇的时候,我就到缸边,俯首看缸里,几条小鱼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缸底是那几块精致的石头,让人产生无穷的回忆,感觉到生活的舒适与惬意。
2008年,我们再次搬家到阳谷县城,住进了新建的楼房。我终于割舍掉那份情缘,把那口曾经陪伴我十几年的水缸送回了农村老家。虽然这口水缸已经没有任何用途,但是我仍不愿丢弃,把它放在老家院子里,让它成为记录时代的一个标记。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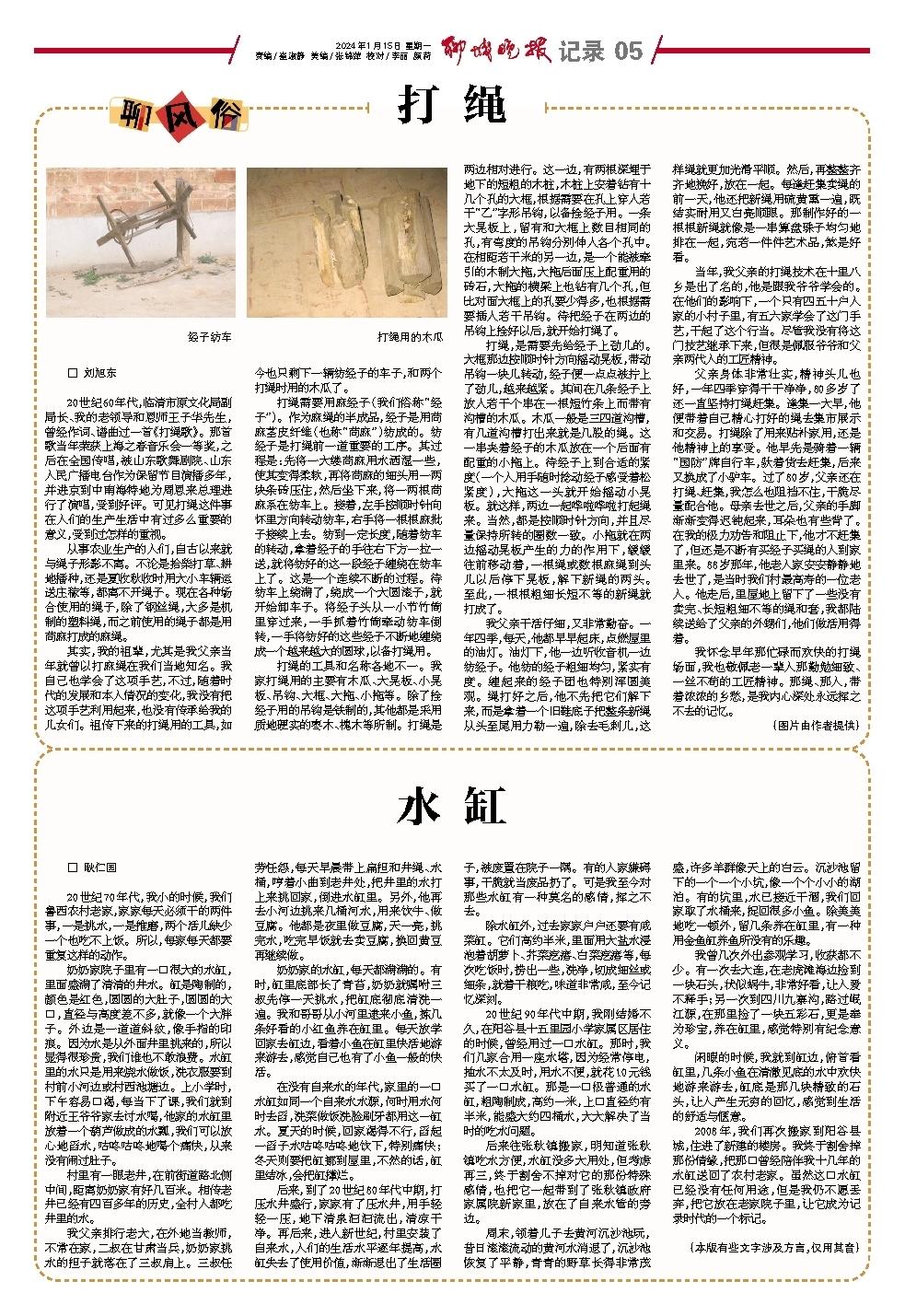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