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焦枣
□ 高明久
小时候,每当我嘴馋了,母亲就抓给我一小把焦枣(即乌枣,老家一带习惯称焦枣),吃在嘴里清香甘甜,很是筋道,越嚼越有滋味。那时总是吃了还想要,母亲不给就馋得直咽唾沫,至今想起来,嘴里还流口水呢!
一
我的老家顾官屯镇高少宇村,东、南距离黄河二十多公里,西距运河不足十公里,交织出两河文化风韵。明末清初年间,祖辈在村子四周栽下大量的枣树。儿时的我好奇心强,总喜欢走到大枣树旁,搂搂这棵,抱抱那棵。树干太粗,搂不过来,就和哥哥两个人手拉手合抱。
“这是谁栽的树?多久才能长这么粗?”我问爷爷。
爷爷捋捋花白的胡子笑着说:“听说这是我的老爷爷那一辈栽的,你算一算多长时间才能长这么粗?”
老枣树的树干粗糙,鼠耳般的叶子里挂满了青红相间的大枣。我站在树下出神,从我的爷爷到爷爷的老爷爷,掰着指头怎么也算不出是哪年哪月栽的。我愣愣地望着颗颗大枣,就盼着打枣、做焦枣。
二
七月十五枣红肚,八月十五枣上屋。每到家里挂了锄钩(庄稼已经长起来,不用再锄草)的时候,村子四周尤其是路口就会有张贴的“告示”:收购红枣,收购劈柴。
白露前后开始打枣,青壮劳力拿着长长的白蜡杆子打枣。老人和妇女蹲在树下拾枣,少年儿童则在两侧拾那些落到远处的。大家一边拾,一边把又大又圆的枣放在嘴里吃个不停,遇着个“酸枣”,甘甜中带有一丝酸味,别提那个爽!
地上堆起一堆堆大枣,装满一个个大麻袋,小伙子们用地排车飞快地运往焦枣场。
三
焦枣场里,有熏制焦枣经验的四叔一边收购劈柴,一边指挥挖枣炕。
劈柴以枣木为最佳,木质硬实,火旺烟少,余温时间长。熏出来的焦枣色泽光亮,无烟火味。榆木、柳木次之。杜绝松木和果木,它们含有油脂,燃烧时容易出异味,影响焦枣的质量。
枣炕由若干个窑洞组成。洞宽两米左右,两洞之间的山墙有半米高,下宽上窄,顶部圆滑,利于通火透烟。山墙顶部架有檩条,两根檩条间隔一米左右,翻炕时人需要叉开脚站在上面。檩条上面铺有秫秸箔。
收购的红枣以我们自己村里的为主。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村里的枣树多、产量大,更重要的是我们村是黏土地,结的枣个儿大肉多、紫红透黑,做出来的焦枣成色好。沙土地里的枣色鲜艳,肉少、水分多,熏制过后成色较差。
焦枣场西边是一溜儿敞棚,里面是一排枣炕,足足有三十几米长,敞棚顶上是一溜儿高耸的烟囱。
东面由北向南是一溜儿生产线,一堆堆红枣形似一座座小山包。板凳上支起秫秸箔,围坐一圈的老妇逐个挑枣,剔除青枣、有疤的枣和失去水分的干巴枣。
南面是一口口大锅,里面是滚烫的开水。村里人把挑好的红枣分批倒入锅中,两位年富力强的壮丁,拿着木锨不停地搅拌,让其均匀受热。煮8至10分钟看准火候捞出,再放进盛有温水的大缸里,浸泡半个多小时,使其表皮松软易皱。然后捞出放在筛子里轻轻地筛,筛出纹路晾在秫秸箔上。
四
煮泡过的枣晾干水分就开始上炕。村里人用簸箕把枣端到炕上摊开约15厘米厚,便开始点火熏制。
为使枣熏制均匀,每12个小时就要上炕翻一次,是为“翻炕”。我在寂静的夜晚常听到“四叔,来翻炕哩”的呼叫声。
枣需要熏制三遍,每遍熏制三到四天,每遍都需要下炕挑拣,确保个个完好无损,然后再晾在箔上。熏制完成再换下一批上炕。
焦枣熏制完成,得历时半个月。然后,村里人对其分类、打包。
一级为枣头,个儿大肉多且松软,易咀嚼;二级叫中身,个头儿中等,纹路细腻匀实,口感筋道;三级忘记了名字,个头儿较小,肉质干硬。
等外是枣皮,枣皮并非字面意思,它是指在熏制过程中破损了的枣或是混进去的青枣。
前三级焦枣统一由土产杂品站收购,销售到全国各地或出口东南亚国家,这给我们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枣皮留下来分给各家各户,就是这些焦枣,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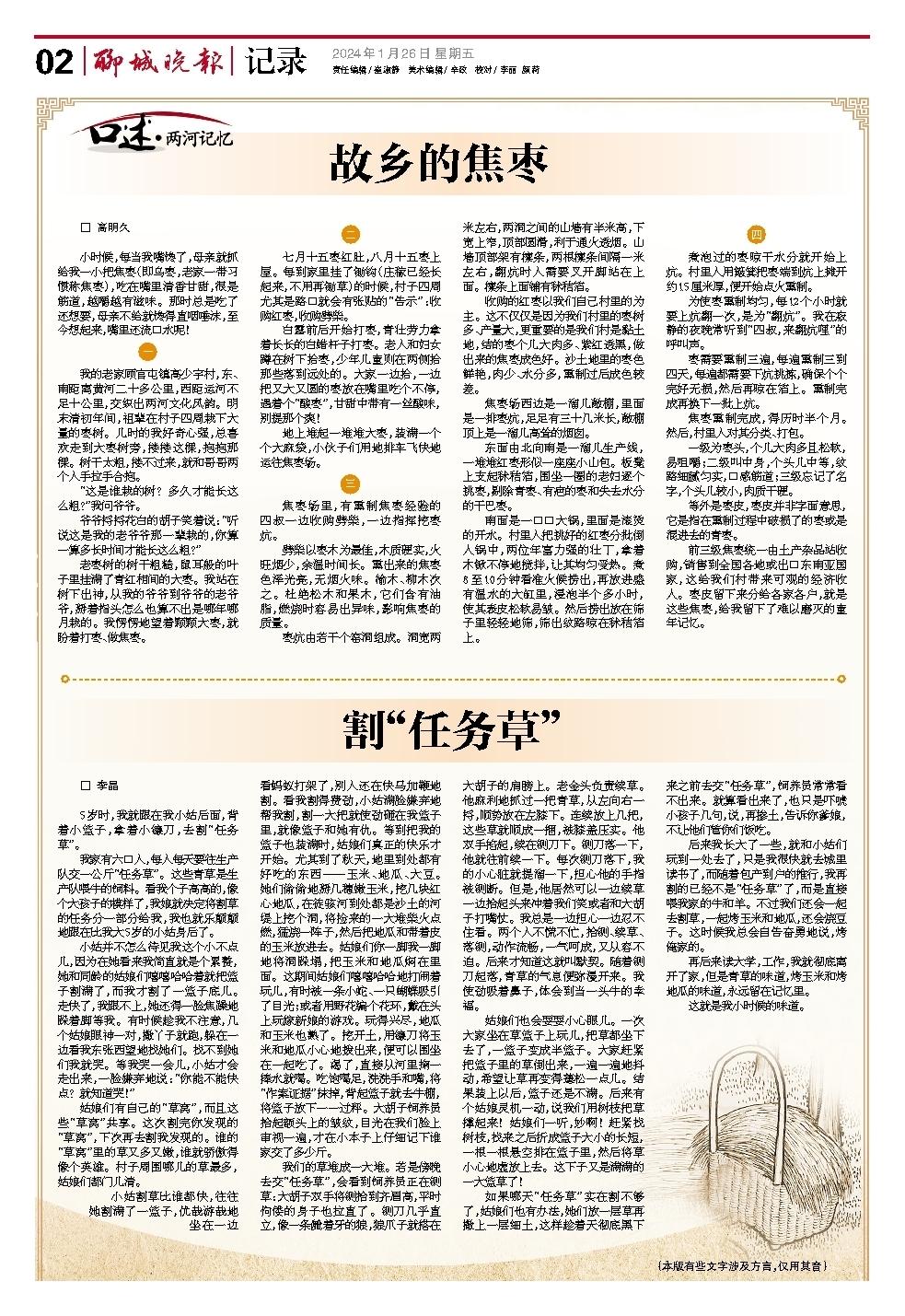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