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泪
○ 袁冰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年轻时剑眉星目,鼻梁高挺,踏实稳重,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小伙。那个年代的农村,参军入伍是几乎所有青年向往的事。父亲也不例外,光荣参军入伍,在惠民地区无棣县(现滨州市无棣县)服役。
听父亲讲,他的部队驻地,是一个美丽的滨海村庄。村主任50岁左右,是一个朴实的渔民,在他眼里这些十七八岁的战士还都是孩子,有时捕鱼回来,村主任会叫战士们去家里吃饭。村主任的独生女儿,十六七岁,美丽善良,心灵手巧,偷偷给父亲做过好几双布鞋,村主任也有意撮合,但因为祖母已为父亲在家乡定了亲,所以父亲选择了与之疏远,退伍后和我母亲结婚。现在母亲有时还拿这件事打趣父亲,说父亲当年如果娶了村主任的女儿,现在肯定发达了,父亲总是笑而不语。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是他脑子聪明,入伍后刻苦学习,一年后已经能够读书读报,给家里写信。父亲退役后回家做了一辈子农民,因为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他下决心一定要供孩子读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尽管包产到户后农村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但鲁西平原还普遍是小农经济,农民大都不富裕。我打记事起,父母终日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辛勤劳作,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我们姐弟三个年龄相差都只有一岁,吃的、穿的、用的都要花钱,后来又相继上学,家里经济更是拮据。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们考上,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
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每次交学费时,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心照不宣地拖到最后期限才会给父母说。这时候每每是家庭气氛最压抑的时候。父母总是在我们面前尽量装出轻松的样子,年幼的我们还是能体会到父母心里的那份沉重。
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一个读到高中,一个读到中专,因为她们执意不再读书,父亲也没有再坚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我身上。
2002年,我第一次高考失败,很受打击。父亲只说了一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愿意,咱们再去复读一年。”
父亲的宽容给了我力量,也激发了我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我毅然选择了去县城复读。我在学校外面租了一间杂物间,每天坚持学习15个小时以上,除了吃饭、睡觉外,一心都扑到学习上。为了节省时间,有时啃方便面、喝点白开水就是一顿饭。由于长时间缺乏营养,休息不充分,我的身体不好,需要经常吃药,最瘦时只有53公斤。
复读期间,父亲很少去学校看我。只有一次,父亲作为我们村的党员代表到县里开会,正好赶上我们每月一次的两天假期。父亲开完会就顺便到学校接我一起回家。我记得父亲站在学校门外看到我走出来后,眼中闪过了一丝很复杂的目光,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坐公共汽车回到家时已接近傍晚。母亲像往常一样,给我做了爱吃的菜,还做了我最爱吃的手擀面。那天,从来不喝酒的父亲破天荒喝起了酒。我一阵狼吞虎咽后,就去里屋躺着看书。在我迷迷糊糊想入睡的时候,突然隐约听到低沉的哭声,开始只是抽泣,后来慢慢变成了痛哭。
仔细一听是父亲在哭,父亲边哭边向母亲说:“为什么孩子那么瘦,是不是不舍得花钱买吃的?今天儿子从学校出来时我看到他那么瘦,真是心疼啊……”我当时没有出去劝慰父亲,当时也不知该如何劝慰,只是躺在床上默默听着,泪水湿透了枕头。
2003年,我再次参加高考,这次没有令父亲失望,以高分考上了心仪的本科高校。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听邻居说送录取通知书的来了,放下农活,和母亲一起匆匆从地里赶回家,洗干净手后,用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掌捧着录取通知书来回摩挲,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多少年的付出和期待都凝聚在这小小的一封通知书里。
本科毕业后,我考入县法院工作,两年后又考上研究生,毕业后被选调到北京工作,成了村里人学习的榜样,父母也很欣慰。今年过年,我携妻儿回家探亲,问起父亲是否还记得当年从学校接我回家,酒后心疼我而掉泪的事情,父亲扭头望了望窗外,反问了一句:“有吗?我记不得了。”
我分明又看到了父亲眼里泛起晶莹的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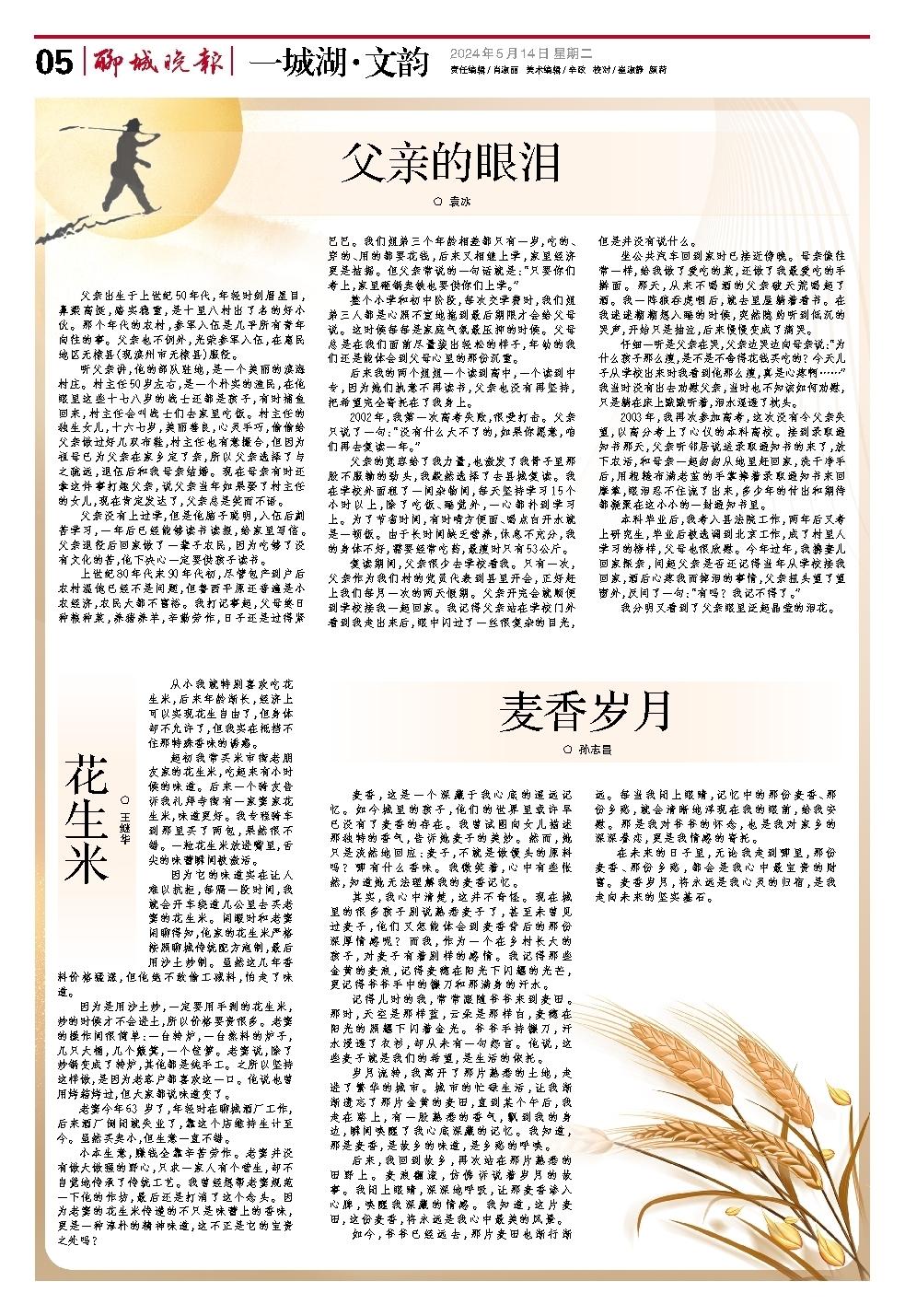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