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父亲
○李欣欣
在20世纪北方的农村,贫瘠而宽广的土地孕育出许多粗糙的汉子,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承担着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在乡土气息的浸润下,北方男子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他们不善言谈、脾气暴躁,为了生计在外赚钱,很少过问家里的琐事,对待家里人尤其是自己的老婆,经常呼来喝去。我的父亲是这样,前院的二大伯、后院的三大伯也是这样。
20世纪60年代,父亲出生于农村一个贫穷的家庭,童年时就失去了母亲。老舍在《我的母亲》里这样写:“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可怜的父亲便如同夹缝中生存的野草,早早便遭遇了来自人世间的凄风苦雨,体会到了人情冷暖,这也使父亲养成了敏感倔强的性格。
在我六七岁时,父亲由于勤劳、肯钻研,和人合伙做起了轴承生意。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父亲南至广东、福建,北至吉林、黑龙江,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我们家成为村里少有的“万元户”,家里配置了摩托车、电话等。可是好景不长,在我上初中时,父亲和人合伙开纱厂,由于多种原因,纱厂的生意一落千丈,父亲也赔得血本无归。
自此,家里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景气。母亲身体孱弱,无力维持生计,父亲沉沦颓废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振作,外出跑生意。我和哥哥一直努力学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父母再难,也一直供我们读书,一直到我和哥哥研究生毕业,家里才算宽裕一点。接下来,就是哥哥和我的婚姻之事,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父母的心事才算了了。
母亲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骨子里倔强不服输。自从我的小侄女出生后,这些年,母亲一直奔波在四川和山东之间,帮我和哥哥看孩子。而已过耳顺之年、习惯被母亲伺候的父亲,突然间成了“留守老人”,一个人在家种地、生活。
母亲不在家的这些年,父亲一开始不适应,后来逐渐适应。他一个人做饭、种地、收拾菜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周末我回去后,他会给我包包子、烙盒子、蒸花卷……之前从来不做这些的父亲,好像变得无所不能。不知是年龄的缘故还是心态的变化,这两年,父亲好像平和了很多。
我心里牵挂父亲,周末没事时都会回去看看,我开始庆幸留在了老家。古人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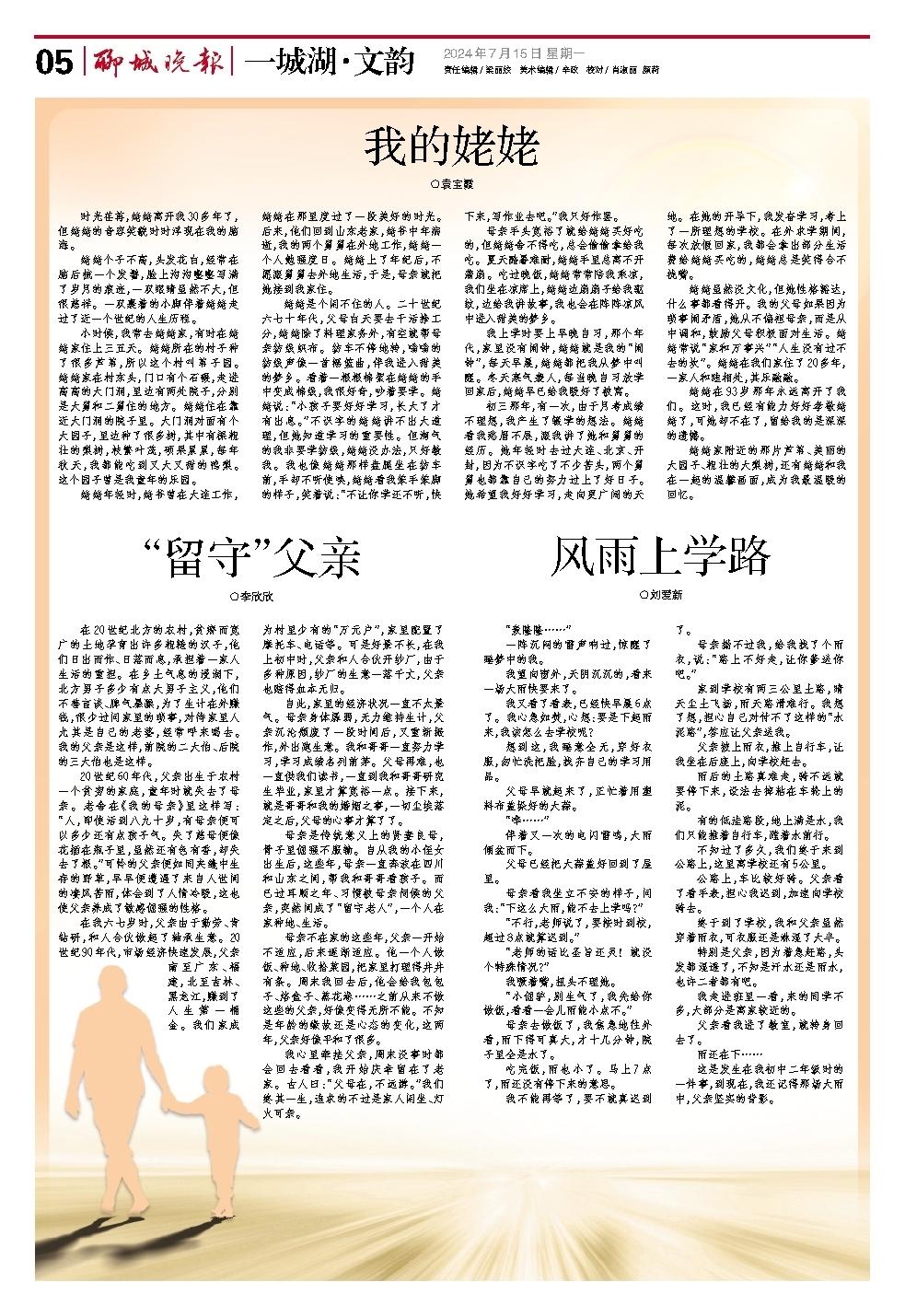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