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房子变奏曲
□ 刘晓东
40多年来,我家先后5次换房子,一次比一次宽敞,一次比一次住得舒服。
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家人在农村老家生活。那时候我们的家是前后各有三间土坯房的小院子,由前院进入,通过客厅的北门进入后院。爷爷奶奶住前面三间房,我们姐弟几个和父母则住在后面三间房里。院子虽小,可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能互相照顾,也是其乐融融。土坯房既矮又窄,采光全靠前面的窗户,后墙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吊窗。窗户被木条隔成一个个不大的四方格子,最初是用白纸糊上的,再后来用的是薄塑料布。风一吹,一鼓一收,非常好玩。墙皮是用白灰、麻线混合后泥成的,上面除了姐姐们的奖状就是我的涂鸦。土坯房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那时候的冬天格外冷,路面都冻得裂开了一条条缝。门前池塘的水全冻成了冰,大人在上面行走也不会出现意外。厚厚的墙体能够把寒冷的北风挡在外面,在屋里再点上一些柴火,便能暖和很长时间。坏处则是经常从墙上、房顶上落土。一觉醒来,被子上就会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地面是用土夯成的,非常坚硬,并泛出泥土特有的光亮。时间长了,会出现一个个小疙瘩。穿着布鞋走在上面会硌脚,大人们就会用铁铲铲去一层,并取名为“削山头”。
1982年左右,上级号召调整种植结构,农民不再单纯种植小麦、玉米,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一车白花花的棉花就能换到一沓厚厚的钱,农民仿佛在一夜之间富起来,村里的万元户越来越多。于是农村掀起了盖新房的热潮,前出厦几乎成了新房的代名词。我家也不例外,父亲找了几个邻居,一天时间就把土坯房推倒收拾干净了。爷爷脸上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但更多的是期盼的眼光。几天后,新房便建设完毕,明亮的窗户、雪白的墙壁、散发着松树特有香味的檩条,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头一天搬进去,我和姐姐们兴奋得一夜没睡。
几年后,父亲在县城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了一处小院。为了照顾我们姐弟几个读书,父亲将家搬到县城,而母亲和爷爷奶奶继续留在农村。这处小院其实就是原来的办公室改造的,院子不大,一间正房、一间伙房。可是我们感觉十分满足,至少在城里有立足之地了。每天放学回来,把院门一关,方寸大的天地就是我们的乐园。那时候父亲既得工作,又得照顾我们,非常辛苦。我和父亲住在厨房里,每天早上睁开眼,就看到父亲忙碌着为我们准备早饭。我们回报父母的只有一张张奖状和满是对号的试卷。
时间不长,爸爸所在的单位新盖了家属楼,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县城是件新鲜事,引起了很大轰动。当时,大家都住在平房里,四层的楼房简直是“鹤立鸡群”。一片喜乐氛围中,我们家和其他十多家一起喜迁新居。新家八十多平方米,三室一厅,空气流通、采光好,十分宽敞舒适。我最喜欢没事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趴在阳台上,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一楼邻居院子里的花草。当时,家里还安装了电话,实现了老人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然而,这还不是最好的房子。2015年,我们姐弟几个给父母新买了一处160多平方米的楼房。新房子三室两厅两卫,完全能够满足老人的生活需要。新房子所在小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楼前楼后都是花园。冬天有地暖,家里温暖如春。重要的是新楼房有电梯,下面有车库,非常方便老人出行。父亲没事的时候,就开着电动车带着母亲和奶奶四处游览一番,看看小城的变化。
“住这样的房子就蛮好了,以后可别再换房子了!”100多岁的奶奶非常知足,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有好的,我们再换。您就等着享福吧,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说。“好,好,听你们的。有更好的咱再换!”奶奶说着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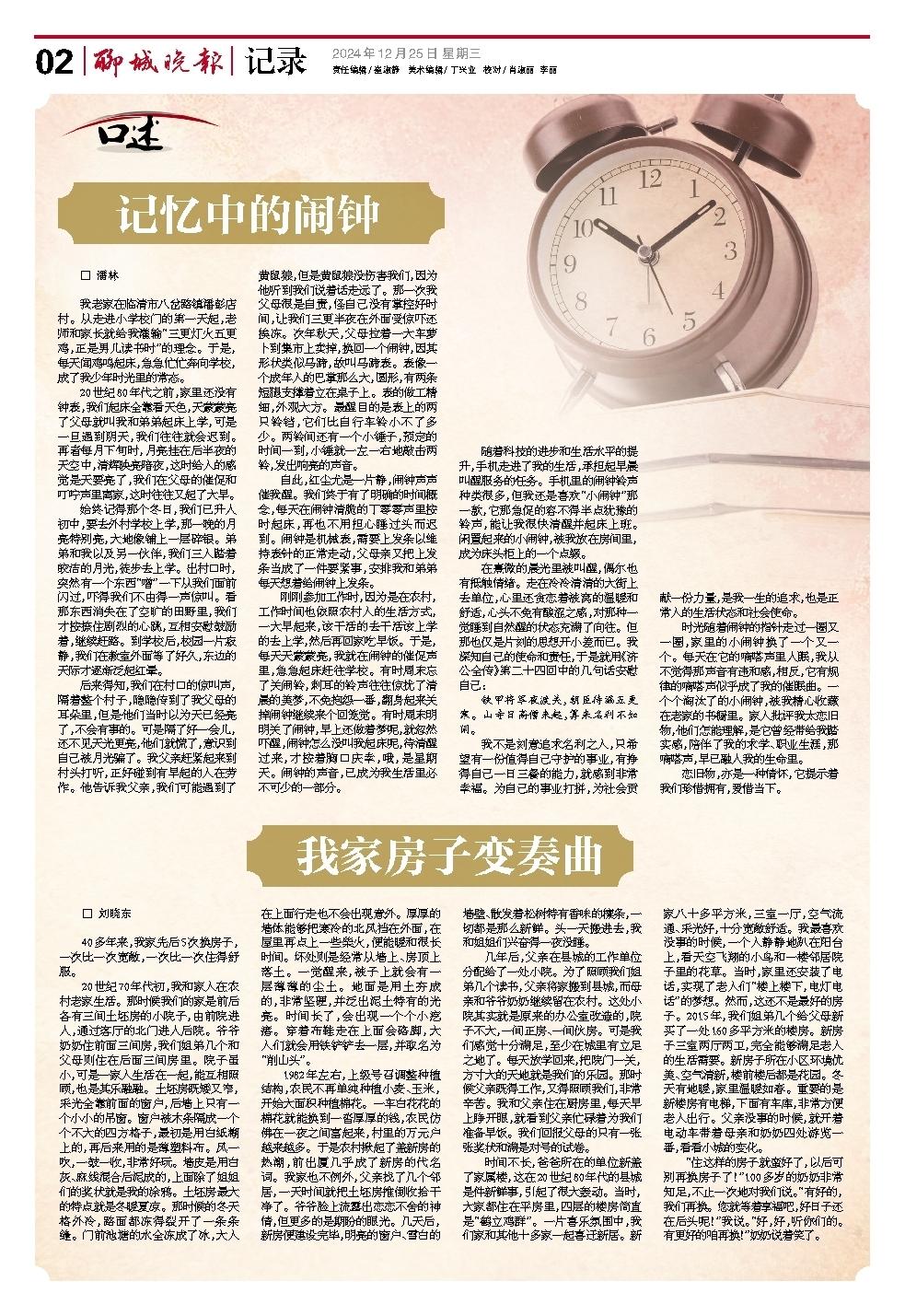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