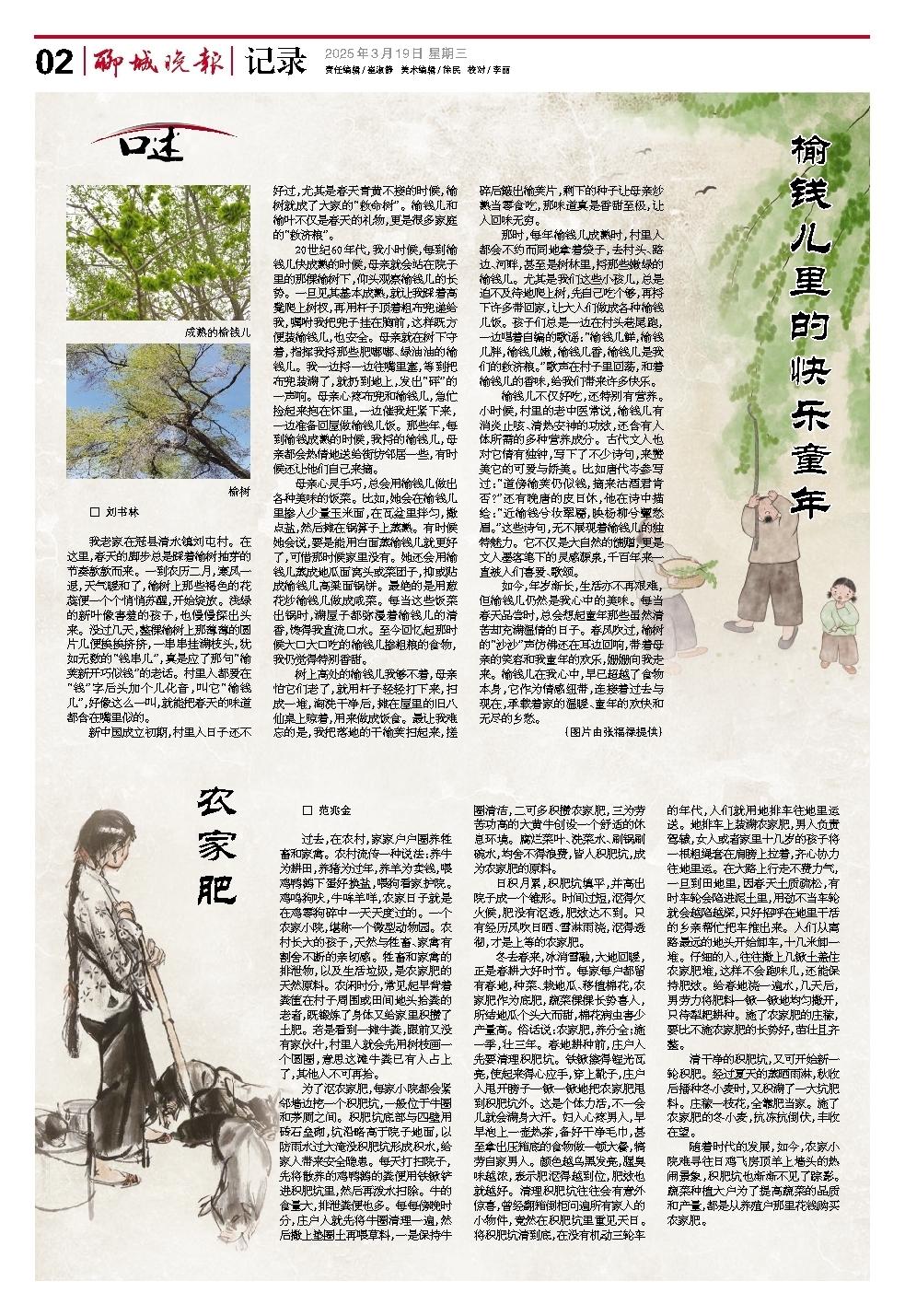榆钱儿里的快乐童年
□ 刘书林
我老家在冠县清水镇刘屯村。在这里,春天的脚步总是踩着榆树抽芽的节奏款款而来。一到农历二月,寒风一退,天气暖和了,榆树上那些褐色的花蕊便一个个悄悄苏醒,开始绽放。浅绿的新叶像害羞的孩子,也慢慢探出头来。没过几天,整棵榆树上那薄薄的圆片儿便挨挨挤挤,一串串挂满枝头,犹如无数的“钱串儿”,真是应了那句“榆荚新开巧似钱”的老话。村里人都爱在“钱”字后头加个儿化音,叫它“榆钱儿”,好像这么一叫,就能把春天的味道都含在嘴里似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村里人日子还不好过,尤其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榆树就成了大家的“救命树”。榆钱儿和榆叶不仅是春天的礼物,更是很多家庭的“救济粮”。
20世纪60年代,我小时候,每到榆钱儿快成熟的时候,母亲就会站在院子里的那棵榆树下,仰头观察榆钱儿的长势。一旦见其基本成熟,就让我踩着高凳爬上树杈,再用杆子顶着粗布兜递给我,嘱咐我把兜子挂在胸前,这样既方便装榆钱儿,也安全。母亲就在树下守着,指挥我捋那些肥嘟嘟、绿油油的榆钱儿。我一边捋一边往嘴里塞,等到把布兜装满了,就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响。母亲心疼布兜和榆钱儿,急忙捡起来抱在怀里,一边催我赶紧下来,一边准备回屋做榆钱儿饭。那些年,每到榆钱成熟的时候,我捋的榆钱儿,母亲都会热情地送给街坊邻居一些,有时候还让他们自己来摘。
母亲心灵手巧,总会用榆钱儿做出各种美味的饭菜。比如,她会在榆钱儿里掺入少量玉米面,在瓦盆里拌匀,撒点盐,然后摊在锅箅子上蒸熟。有时候她会说,要是能用白面蒸榆钱儿就更好了,可惜那时候家里没有。她还会用榆钱儿蒸成地瓜面窝头或菜团子,抑或贴成榆钱儿高粱面锅饼。最绝的是用葱花炒榆钱儿做成咸菜。每当这些饭菜出锅时,满屋子都弥漫着榆钱儿的清香,馋得我直流口水。至今回忆起那时候大口大口吃的榆钱儿掺粗粮的食物,我仍觉得特别香甜。
树上高处的榆钱儿我够不着,母亲怕它们老了,就用杆子轻轻打下来,扫成一堆,淘洗干净后,摊在屋里的旧八仙桌上晾着,用来做成饭食。最让我难忘的是,我把落地的干榆荚扫起来,搓碎后簸出榆荚片,剩下的种子让母亲炒熟当零食吃,那味道真是香甜至极,让人回味无穷。
那时,每年榆钱儿成熟时,村里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拿着袋子,去村头、路边、河畔,甚至是树林里,捋那些嫩绿的榆钱儿。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孩儿,总是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先自己吃个够,再捋下许多带回家,让大人们做成各种榆钱儿饭。孩子们总是一边在村头巷尾跑,一边唱着自编的歌谣:“榆钱儿鲜,榆钱儿胖,榆钱儿嫩,榆钱儿香,榆钱儿是我们的救济粮。”歌声在村子里回荡,和着榆钱儿的香味,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
榆钱儿不仅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小时候,村里的老中医常说,榆钱儿有消炎止咳、清热安神的功效,还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古代文人也对它情有独钟,写下了不少诗句,来赞美它的可爱与娇美。比如唐代岑参写过:“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还有晚唐的皮日休,他在诗中描绘:“近榆钱兮妆翠靥,映杨柳兮颦愁眉。”这些诗句,无不展现着榆钱儿的独特魅力。它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灵感源泉,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喜爱、歌颂。
如今,年岁渐长,生活亦不再艰难,但榆钱儿仍然是我心中的美味。每当春天品尝时,总会想起童年那些虽然清苦却充满温情的日子。春风吹过,榆树的“沙沙”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带着母亲的笑容和我童年的欢乐,姗姗向我走来。榆钱儿在我心中,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它作为情感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家的温暖、童年的欢快和无尽的乡愁。
(图片由张福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