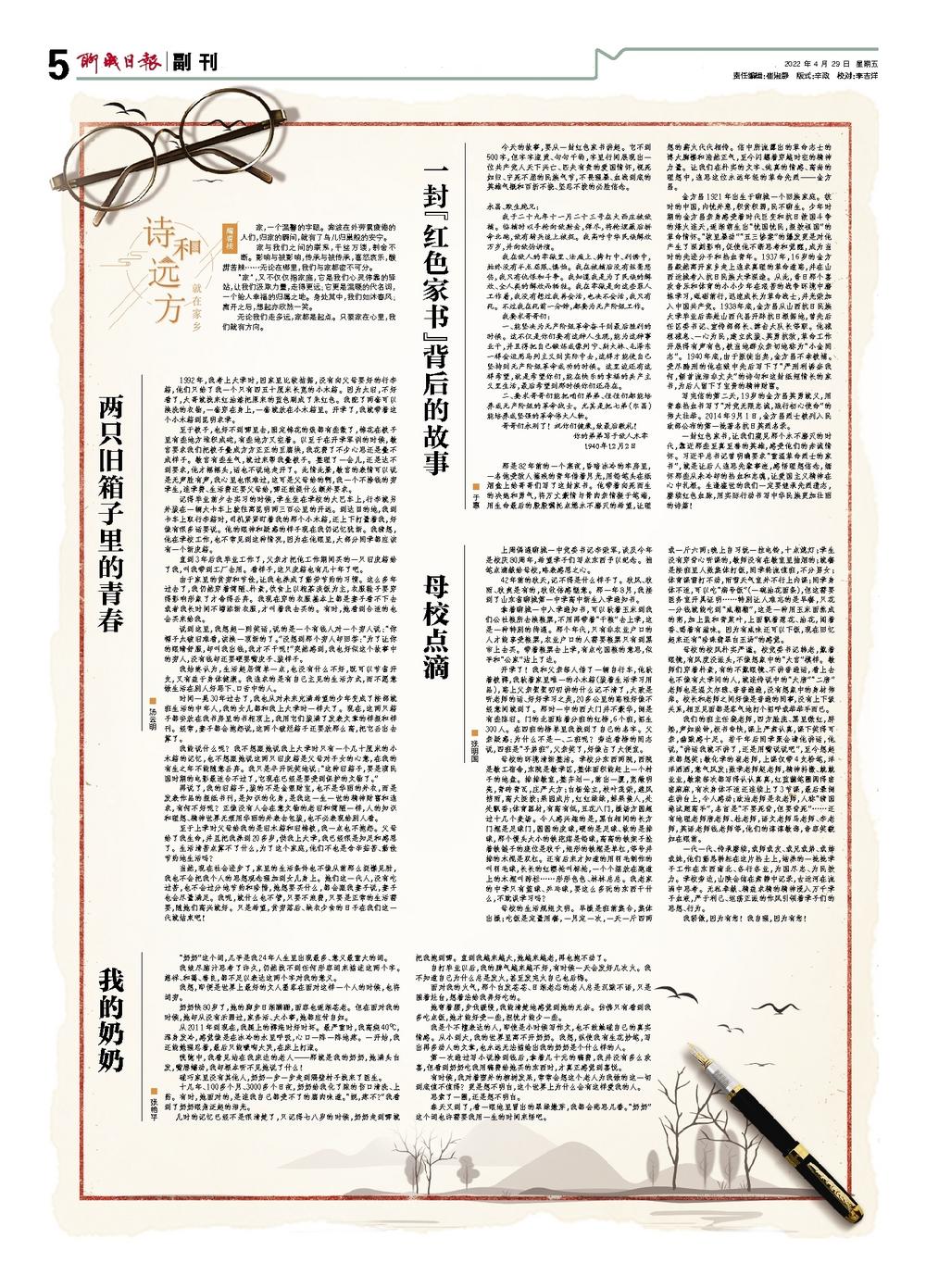母校点滴
■ 张明国
上周偶遇聊城一中党委书记李荣军,谈及今年是校庆80周年,希望学子们写点东西予以纪念。拙笔点滴献给母校,略表感恩之心。
42年前的秋天,记不得是什么样子了。秋风、秋雨、秋爽是有的,秋收倍感惬意。那一年8月,我接到了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高中新生入学通知书。
拿着聊城一中入学通知书,可以驮着玉米到我们公社粮所去换粮票,不用再带着“干粮”去上学,这是一种特别的待遇。那个年代,只有非农业户口的人才能享受粮票,农业户口的人需要粮票只有到黑市上去买。带着粮票去上学,有点吃国粮的意思,似乎和“公家”沾上了边。
开学了!我和父亲每人借了一辆自行车,他驮着被褥,我驮着家里唯一的小木箱(装着生活学习用品),路上父亲絮絮叨叨讲的什么记不清了,大致是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之类,20多公里的路程好像不经意间就到了。那时一中的西大门并不豪华,倒是有些陈旧。门的北面贴着分班的红榜,6个班,招生300人。在四班的榜单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父亲疑惑:为什么不是一、二班呢?旁边看榜的同志说,四班是“子弟班”,父亲笑了,好像占了大便宜。
母校的环境清新整洁。学校分东西两院,西院是教工宿舍,东院是教学区,整体面积能赶上一个村子的地盘。排排教室,整齐划一,前出一厦,宽敞明亮,青砖青瓦,庄严大方;白杨耸立,枝叶茂荣,遮风挡雨,高大挺拔;果园成片,红红绿绿,鲜果羡人,处处飘香;体育器材,有高有低,五花八门,操场方圆超过十几个麦场。令人感兴趣的是,黑白相间的长方门框是足球门,圆圆的皮球,硬的是足球、软的是排球,那个馒头大小的铁疙瘩是铅球,高高的铁架子拴着铁链子的座位是秋千,矩形的铁框是单杠,等号并排的木棍是双杠。还有后来才知道的用羽毛制作的叫羽毛球,长长的红缨枪叫标枪,一个个摆放在跑道上的木框叫跨栏……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我老家的中学只有篮球、乒乓球,要这么多玩的东西干什么,不耽误学习吗?
母校的生活规矩文明。早操是班前集合,集体出操;吃饭是定量用餐,一月定一次,一天一斤四两或一斤六两;晚上自习统一拉电铃,十点熄灯;学生没有穿背心听课的,教师没有在教室里抽烟的;就餐是按班里人数集体打饭,同学轮流值班,不分男女;体育课雷打不动,雨雪天气室外不行上内课;同学身体不适,可以吃“病号饭”(一碗油花面条),但这需要医务室开具证明……特别让人难忘的是早餐,只花一分钱就能吃到“咸糊糊”,这是一种用玉米面熬成的粥,加上盐和青菜叶,上面飘着葱花、油花,闻着香、喝着有滋味。因为有咸味还可以下饭,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感觉。
母校的校风朴实严谨。校党委书记韩老,戴着眼镜,有风度没派头,不像想象中的“大官”模样。教师们穿着朴素,有的不戴眼镜、不讲普通话,看上去也不像有大学问的人,就连传说中的“大唐”“二唐”老师也是温文尔雅、普普通通,没有想象中的身材伟岸。校长和老师之间好像是普通的同事,没有上下级关系,相互见面都是客气地打个招呼或举举手而已。
我们的班主任裴老师,四方脸庞、黑里微红,胖矮,声如洪钟,板书奇快,课上严肃认真,课下笑得可亲,幽默感十足。若干年后同学聚会请他讲话,他说,“讲话我就不讲了,还是用嘴说说吧”,至今想起来都想笑;教化学的崔老师,上课仅带4支粉笔,洋洋洒洒,意气风发;数学老师赵老师,精神抖擞、兢兢业业,教案每次都写得认认真真,红蓝蘸笔圈阅得密密麻麻,有次身体不适还连续上了3节课,最后晕倒在讲台上,令人感动;政治老师是衣老师,人称“猜国卷试题高手”,名言是“不要死背,但要背死”……还有地理老师唐老师、杜老师,语文老师马老师、李老师,英语老师钱老师等,他们的谆谆教诲,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一代一代、传承赓续,或师或友、或兄或弟、或姊或妹,他们勤恳耕耘在这片热土上,培养的一批批学子工作在东西南北、各行各业,为国尽忠、为民效力。学校旁边,山陕会馆在肃静中记录,古运河在流淌中思考。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浸入万千学子血液,严于利己、坦荡正派的作风引领着学子们的思想、行为。
我骄傲,因为有您!我自强,因为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