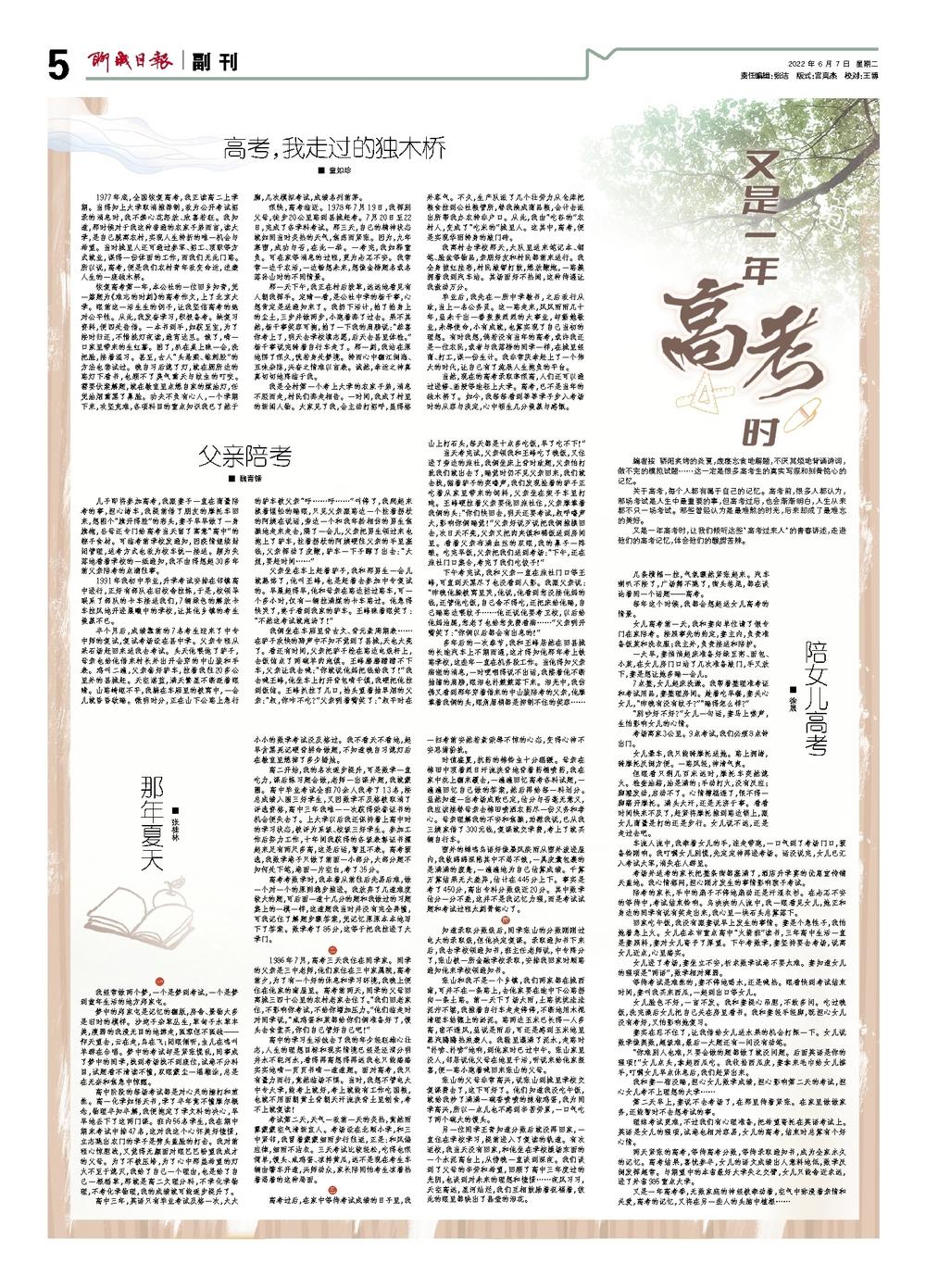高考,我走过的独木桥
■ 童如珍
1977年底,全国恢复高考,我正读高二上学期。当得知上大学取消推荐制,改为公开考试招录的消息时,我不禁心花怒放、欣喜若狂。我知道,那时候对于我这种普通的农家子弟而言,读大学,是自己脱离农村,实现人生转折的唯一机会与希望。当时城里人还可通过参军、招工、顶职等方式就业,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我们无此门路。所以说,高考,便是我们农村青年改变命运,逆袭人生的一座独木桥。
恢复高考第一年,本公社的一位回乡知青,凭一篇题为《难忘的时刻》的高考作文,上了北京大学。眼前这一活生生的例子,让我坚信高考的绝对公平性。从此,我发奋学习,积极备考。缺复习资料,便四处告借。一本书到手,如获至宝,为了按时归还,不惜挑灯夜读,通宵达旦。饿了,啃一口家里带来的生红薯。困了,趴在桌上眯一会,洗把脸,接着温习。甚至,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方法也尝试过。晚自习后熄了灯,就在厕所边的路灯下看书,也顾不了臭气熏天与蚊虫的叮咬。需要伏案解题,就在教室里点燃自家的煤油灯,任凭油烟熏黑了鼻脸。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学期下来,攻坚克难,各项科目的重点知识我已了然于胸,几次模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很快,高考临近。1978年7月19日,我挥别父母,徒步20公里路到县城赶考。7月20日至22日,完成了各学科考试。那三天,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如同当时炎热的天气,焦虑而紧张。因为,九年寒窗,成功与否,在此一举。一考完,我如释重负。可在家等消息的过程,更为忐忑不安。我常常一边干农活,一边畅想未来,想像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时的不同情景。
那一天下午,我正在村后拔草,远远地看见有人朝我挥手。定睛一看,是公社中学的杨干事,心想肯定是送通知来了。我扔下活计,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三步并做两步,小跑着奔了过去。果不其然,杨干事笑容可掬,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恭喜你考上了,明天去学校填志愿,后天去县里体检。”杨干事说完骑着自行车走了。那一刻,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恍若身处梦境。转而心中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诚然,幸运之神真真切切地降临于我。
我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奔走相告。一时间,我成了村里的新闻人物。大家见了我,会主动打招呼,显得格外客气。不久,生产队派了几个壮劳力从仓库把粮食拉到公社粮管所,替我换成商品粮,会计去派出所帮我办农转非户口。从此,我由“吃谷的”农村人,变成了“吃米的”城里人。这其中,高考,便是实现华丽转身的敲门砖。
我离村去学校那天,大队里送来笔记本、钢笔、脸盆等物品,亲朋好友和村民都前来送行。我全身披红挂彩,村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路簇拥着我到汽车站。其场面好不热闹,这种待遇让我激动万分。
毕业后,我先在一所中学教书,之后改行从政,当上一名公务员。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几十年,虽未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却勤勉敬业,未辱使命,小有成就,也算实现了自己当初的理想。有时我想,倘若没有当年的高考,或许我还是一位农民,或者与我落榜的同学一样,在城里经商、打工,谋一份生计。我非常庆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让自己有了施展人生抱负的平台。
当然,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很高,人们还可以通过进修、函授等途径上大学。高考,已不是当年的独木桥了。如今,我每每看到莘莘学子步入考场时的从容与淡定,心中顿生几分羡慕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