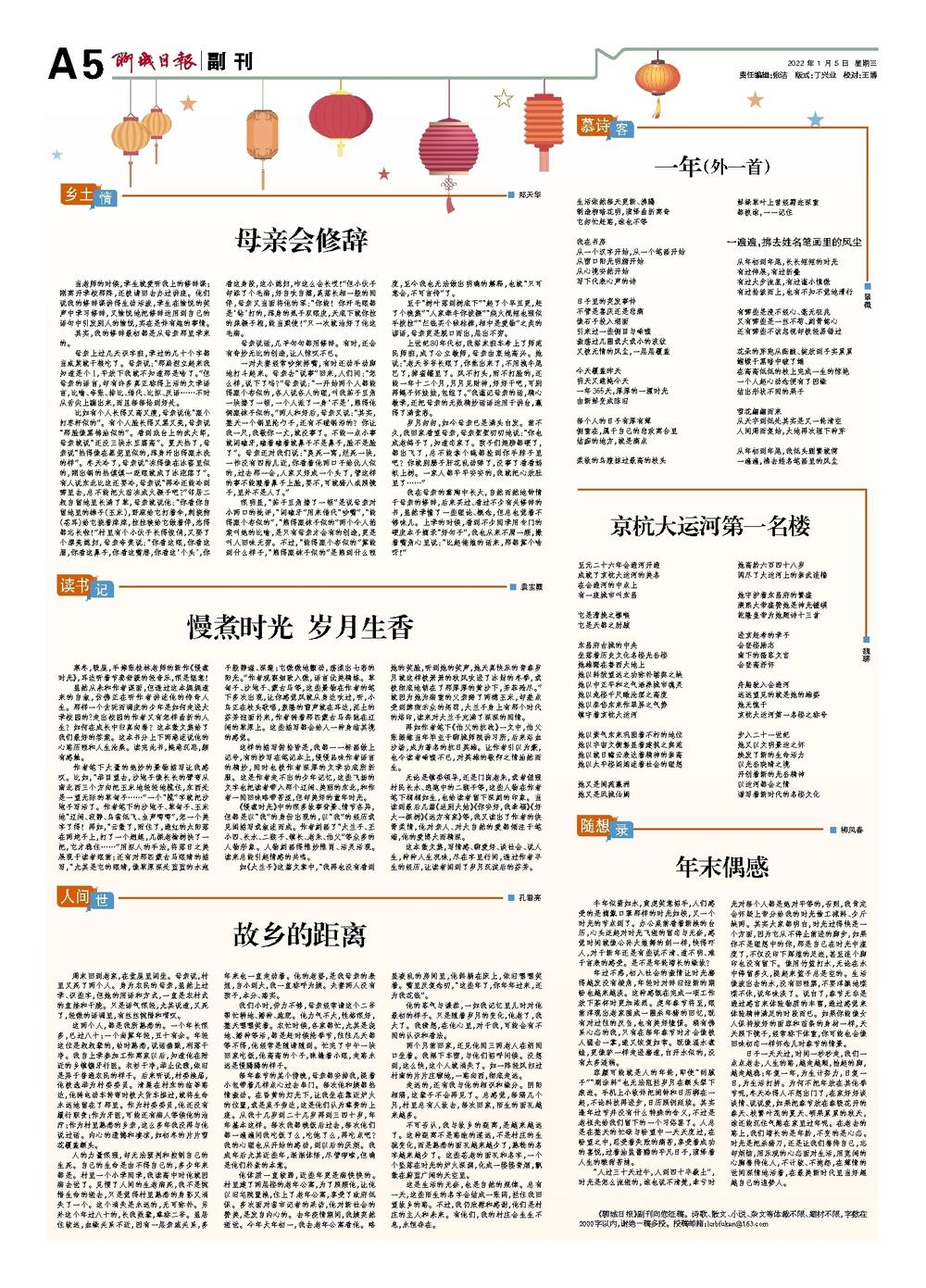母亲会修辞
■ 郑天华
当老师的时候,学生就爱听我上的修辞课;刚离开学校那阵,还被请回去办过讲座。他们说我的修辞课讲得生动活泼,学生在愉悦的笑声中学习修辞,又愉悦地把修辞运用到自己的语句中引发别人的愉悦,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的修辞最初都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上过几天识字班,学过的几十个字都当咸菜就干粮吃了。母亲说:“那扁担立起来我知道是个1,平放下我就不知道那是啥了。”但母亲的语言,却有许多真正称得上活的文学语言,比喻、夸张、排比、借代、比拟、反语……不时从舌尖上蹦出来,而且每每恰到好处。
比如有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母亲说他“跟个打枣杆似的”。有个人脸长得又黑又亮,母亲说“那脸像黑棉油似的”。看到戏台上的武大郎,母亲就说“还没三块水豆腐高”。夏天热了,母亲说“热得像在蒸笼里似的,浑身汗出得跟水洗的样”。冬天冷了,母亲说“冻得像在冰窖里似的,刚出锅的热馍馍一眨眼就成了冰疙瘩了”。有人说东北比这还要冷,母亲说“再冷还能冷到哪里去,总不能把火苗冻成火橛子吧?”邻居二叔自留地里长满了草,母亲就说他:“你看你自留地里的棒子(玉米),野麻给它打着伞,刺挠狗(苍耳)给它挠着痒痒,拉拉秧给它做着伴,恣得都忘长啦!”村里有个小伙子长得俊俏,又娶了个漂亮媳妇,母亲夸奖说:“你看这眼,你看这眉,你看这鼻子,你看这嘴唇,你看这‘个头’,你看这身段,这小媳妇,咋这么会长哎!”但小伙子却添了个毛病,好自吹自擂,奚落长相一般的同伴,母亲又当面将他的军:“你能!你汗毛眼都是‘钻’打的,浑身的虱子双眼皮,天底下就你拉的屎橛子粗,能当梁使!”只一次就治好了他这毛病。
母亲说话,几乎句句都用修辞。有时,还会有奇妙无比的创造,让人惊叹不已。
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拌嘴,有时还动手动脚地打斗起来。母亲去“说事”回来,人们问:“怎么样,说下了吗?”母亲说:“一开始两个人都能得跟个杏似的,各人说各人的理,叫我茄子豆角一块撸了一顿,一个人派了一身‘不是’,熊得他俩跟袜子似的。”两人和好后,母亲又说:“其实,整天一个锅里抡勺子,还有不碰锅沿的?你让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就没事了。不能一点小事就闲磕牙,磕着磕着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母亲还对我们说:“臭死一窝,烂死一块,一拃没有四指儿近,你看着他两口子给仇人似的,过去那一会,人家又好成一个头了,管这样的事不能蹬着鼻子上脸,要不,可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很明显,“茄子豆角撸了一顿”是说母亲对小两口的批评,“闲磕牙”用来借代“吵嘴”,“能得跟个杏似的”,“熊得跟袜子似的”两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创造,更是叫人回味无穷。不过,“能得跟个杏似的”算能到什么样子,“熊得跟袜子似的”是熊到什么程度,至今我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解释,也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至于“树叶落到树底下”“起了个早五更,赶了个晚集”“人家牵牛你拔橛”“烧火棍短也强似手拨拉”“仨钱买个秫秸裤,相中是爱物”之类的谚语,母亲更是脱口而出,层出不穷。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搭末班车考上了师范民师班,成了公立教师,母亲由衷地高兴。她说:“老天爷爷长眼了,你熬出来了,不用拽牛尾巴了,掉蜜罐里了。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还能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见财神,好好干吧,可别再蝇子怀娃娃,包蛆了。”我谨记母亲的话,精心教学,还把母亲的无数精妙话语运用于讲台,赢得了满堂彩。
岁月匆匆,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前不久,我回家看望母亲,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你也成老鸽子了,知道恋家了。孩子们翅膀都硬了,都出飞了,总不能拿个绳都拴到你手脖子里吧?你就别肠子肝花乱动弹了,没事了看看蚂蚁上树。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就把心放肚里了……”
我在母亲的熏陶中长大,自然而然地钟情于母亲的修辞,后来买过、看过不少有关修辞的书,虽然学懂了一些理论、概念,但总也觉着不够味儿。上学的时候,看到不少同学用专门的硬皮本子摘录“好句子”,我也从来不屑一顾,撇着嘴角心里说:“比起俺娘的话来,那都算个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