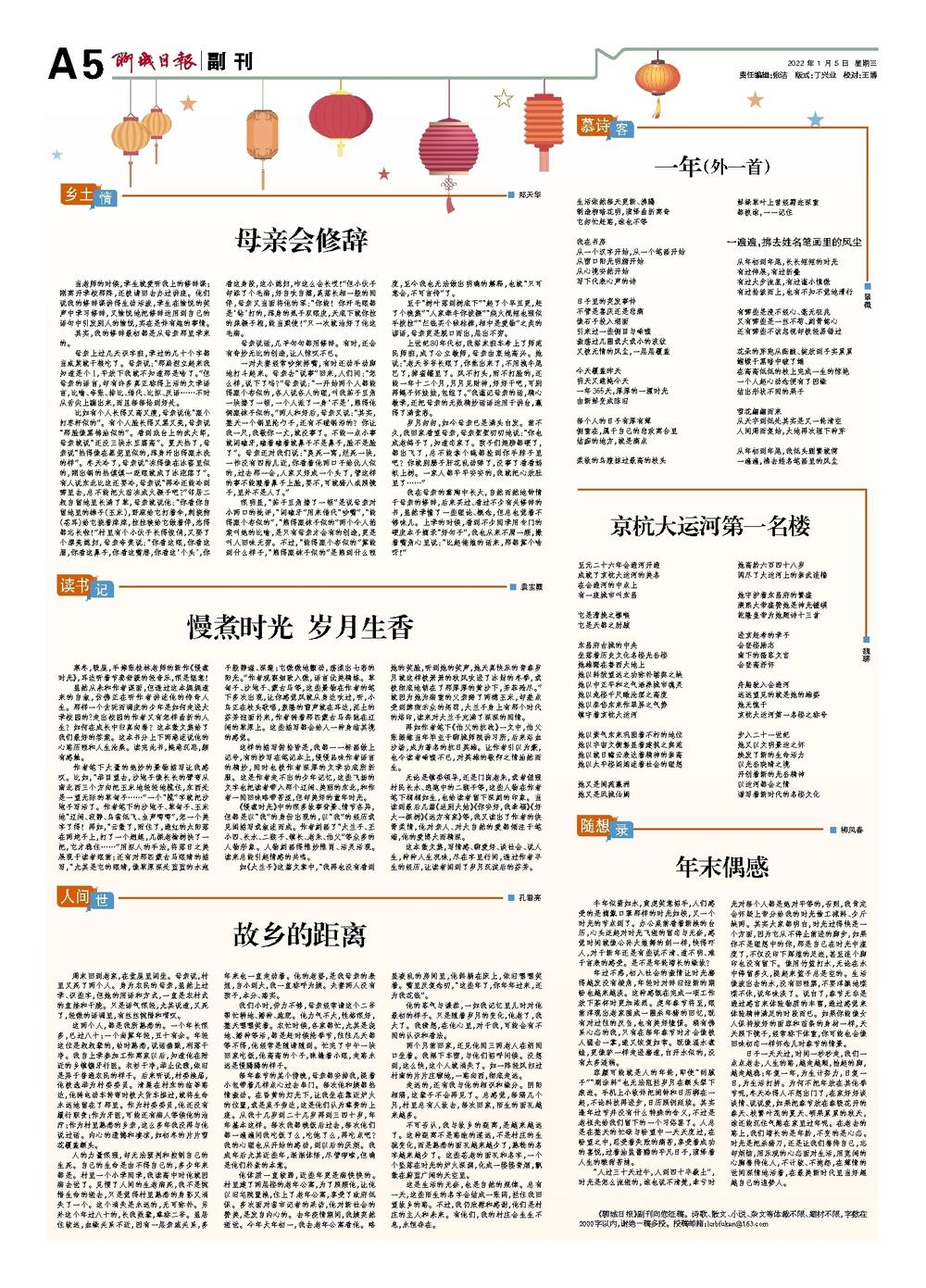故乡的距离
■ 孔垂亮
周末回到老家,在堂屋里闲坐。母亲说,村里又死了两个人。身为农民的母亲,虽然上过学、识些字,但她的用语和方式,一直是农村式的直接和干脆。只是语气很轻,尤其说道,又死了,轻微的语调里,有丝丝惋惜和喟叹。
这两个人,都是我所熟悉的。一个年长很多,已过八十;一个尚算年轻,五十有余。年轻这位是叔叔辈的,幼时熟悉,说话幽默,利落干净。我自上学参加工作离家以后,知道他在附近的乡镇镶牙行医。衣衫干净,举止优雅,依旧是异于普通农民的样子。后来听说,村委换届,他被选举为村委委员。清晨在村东的临莘路边,他骑电动车转弯时被大货车擦过,就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里。作为村委委员,他还没有履行职责;作为牙医,可能还有病人等候他的治疗;作为村里熟悉的乡亲,这么多年我没再与他说过话。内心的遗憾和凄凉,如初冬的片片雪花覆盖额头。
人的力量很强,却无法预判和控制自己的生死。自己的生命是由不得自己的,多少年来都是。村里一个小学同学,我读高中时他就因病去世了。见惯了人间的生老病死,我不是惋惜生命的逝去,只是觉得村里熟悉的身影又消失了一个。这个消失是永远的,无可弥补。另外这个年过八十的,长我数辈,尊称二爷。虽居住较远,血缘关系不近,因有一层亲戚关系,多年来也一直走动着。他的老婆,是我母亲的表姐,自小到大,我一直称呼为姨。夫妻两人没有孩子,本分、踏实。
我们小时,劳力不够,母亲经常请这个二爷帮忙耕地、播种、施肥。他力气不大,性格很好,整天嘿嘿笑着。农忙时候,各家都忙,尤其是浇地、播种等活,都是赶时候抢季节,往往几天都等不得,他经常是随请随到。忙完了中午一块回家吃饭,他高高的个子,眯缝着小眼,走路永远是慢腾腾的样子。
每年春节的某个傍晚,母亲都安排我,提着小包带着几样点心过去串门。每次他和姨都热情激动。在昏黄的灯光下,让我坐在靠近炉火的位置,或是桌子旁边,这是他们认为尊贵的上座。从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再到三四十岁,年年基本这样。每次我都晚饭后过去,每次他们都一遍遍问我吃饭了么,吃饱了么,再吃点吧?我的心理也从开始的感动,到以后的厌烦。我成年后尤其近些年,渐渐体悟,尽管啰嗦,但确是他们朴素的本意。
他体质一直较弱,近些年更是病怏怏的。村里建了两层楼的老年公寓,为了照顾他,让他以旧宅院置换,住上了老年公寓,享受了政府低保。多次面对省市记者的采访,他对新社会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去年疫情期间,我姨突然逝世。今年大年初一,我去老年公寓看他。略显凌乱的房间里,他斜躺在床上,依旧嘿嘿笑着。嘴里反复念叨,“这些年了,你年年过来,还为我花钱”。
他的客气与谦恭,一如我记忆里儿时对他最初的样子。只是随着岁月的变化,他老了,我大了。我猜想,在他心里,对于我,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两个月前回家,还见他同三两老人在胡同口坐着。我摇下车窗,与他们招呼问候。没想到,这么快,这个人就消失了。如一阵轻风扫过村南的片片庄稼地,一路向西,彻底走远。
走远的,还有我与他的相识和缘分。阴阳相隔,这辈子不会再见了。总感觉,每隔几个月,村里总有人故去,每次回家,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
不可否认,我与故乡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这种距离不是路途的遥远,不是村庄的生疏变化,而是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了,熟稔的名字越来越少了。这些苍老的面孔和名字,一个个坠落在时光的炉火深渊,化成一缕缕青烟,飘散在蔚蓝广阔的天空里。
这是生活的无奈,也是自然的规律。总有一天,这些陌生的名字会结成一张网,拦住我回望故乡的路。不过,我仍欣慰和感谢,他们是村庄的主人和未来。有他们,我的村庄会生生不息,永恒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