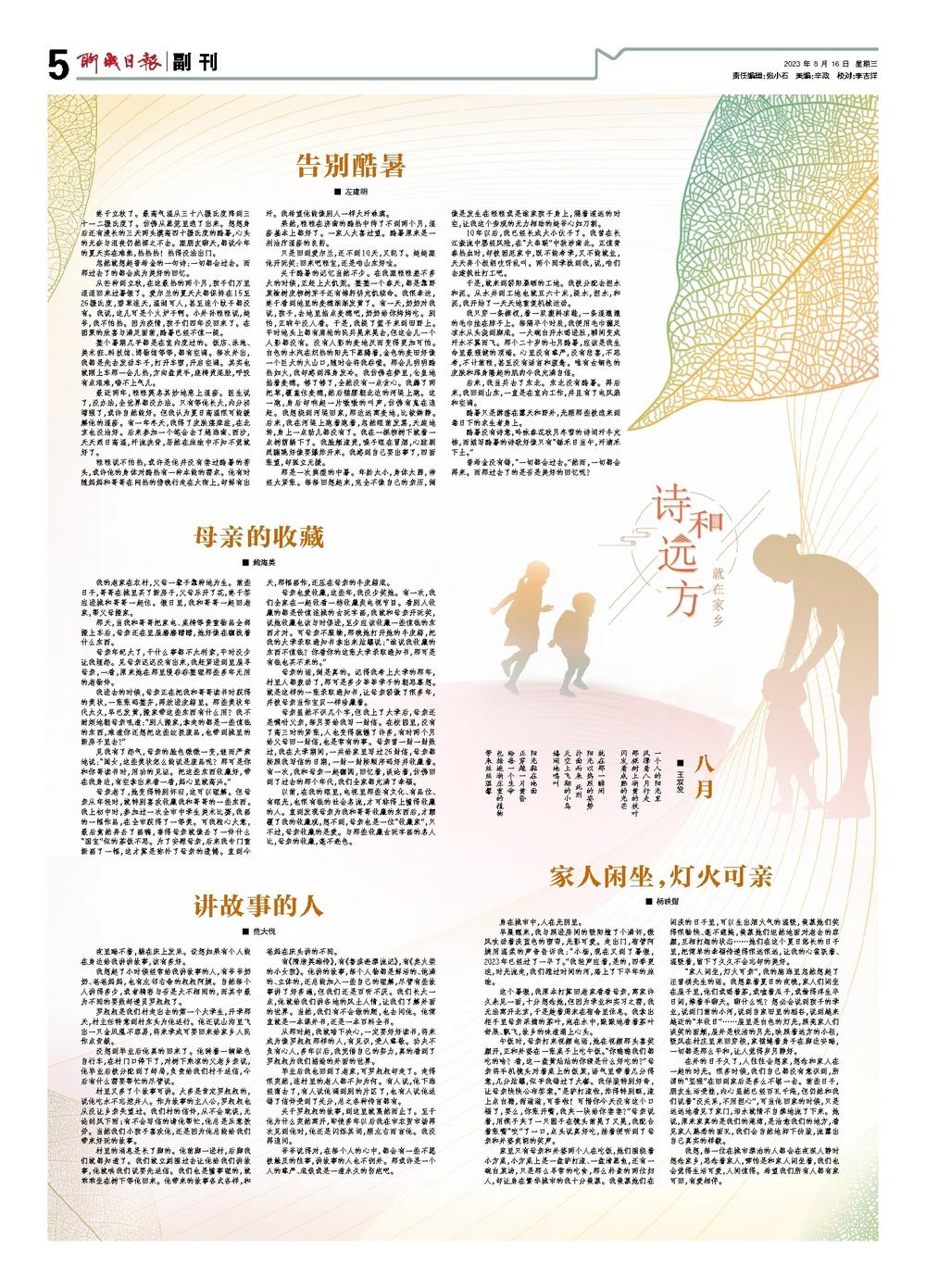告别酷暑
■ 左建明
终于立秋了。最高气温从三十八摄氏度降到三十一二摄氏度了。仿佛从蒸笼里逃了出来。想想身后还有漫长的三天两头摸高四十摄氏度的酷暑,心头的无奈与沮丧仍然挥之不去。跟朋友聊天,都说今年的夏天实在难熬,热热热!热得没法出门。
忽然就想起普希金的一句诗: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
从芒种到立秋,在这最热的两个月,孩子们万里迢迢回来过暑假了。爱尔兰的夏天大都保持在15至26摄氏度,碧草连天,温润可人,甚至连个蚊子都没有。我说,这儿可是个火炉子啊。小外孙程程说,姥爷,我不怕热。因为疫情,孩子们四年没回来了。在团聚的欣喜与满足面前,酷暑已经不值一提。
整个暑期几乎都是在室内度过的。饭店、泳池、美术班、科技馆、博物馆等等,都有空调。每次外出,我都是先去发动车子,打开车窗,开启空调。其实也就刚上车那一会儿热,方向盘烫手,座椅烫屁股,呼吸有点艰难,喘不上气儿。
最近两年,程程莫名其妙地患上湿疹。医生说了,没办法,全世界都没办法。只有等他长大,内分泌增强了,或许自然能好。但我认为夏日高温很可能缓解他的湿疹。有一年冬天,我得了皮肤瘙痒症,在北京也没治好。后来参加一个笔会去了趟海南、西沙,天天烈日高温,汗流浃背,居然在旅途中不知不觉就好了。
程程说不怕热,或许是他并没有尝过酷暑的苦头,或许他的身体对酷热有一种本能的需求。他有时随妈妈和哥哥在闷热的傍晚行走在大街上,却鲜有出汗。我希望他能像别人一样大汗淋漓。
果然,程程在济南的酷热中待了不到两个月,湿疹基本上都好了。一家人大喜过望。酷暑原来是一剂治疗湿疹的良药。
只是回到爱尔兰,还不到10天,又犯了。姥姥跟他开玩笑:回来吧程宝,还是咱山东好哇。
关于酷暑的记忆当然不少。在我跟程程差不多大的时候,正赶上大饥荒。整整一个春天,都是靠野菜榆树皮柳树芽子还有棉籽饼充饥续命。我很幸运,终于看到地里的麦穗渐渐发黄了。有一天,奶奶对我说,孩子,去地里掐点麦穗吧,奶奶给你烤烤吃。别怕,正晌午没人看。于是,我提了篮子来到田野上。平时地头上都有肩枪的民兵晃来晃去,但这会儿一个人影都没有。没有人影的麦地反而变得更加可怕。白色的水汽在炽热的阳光下蒸腾着,金色的麦田好像一个巨大的火山口,随时会将我吞噬。那会儿明明酷热如火,我却感到浑身发冷。我仿佛在梦里,仓皇地掐着麦穗。够了够了,全然没有一点贪心。我薅了两把草,覆盖住麦穗,然后猫腰朝北边的河堤上跑。这一跑,身后却响起一片嗷嗷的叫声,仿佛有鬼在追赶。我想绕到河堤回家,那边远离麦地,比较僻静。后来,我在河堤上跑着跑着,忽然眼前发黑,天旋地转,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在一棵柳树下就着一点树荫躺下了。我脸颊滚烫,嗓子眼在冒烟,心脏剧烈蹦跳好像要爆炸开来。我感到自己要出事了,四面张望,却孤立无援。
那是一次典型的中暑。年龄太小,身体太弱,神经太紧张。每每回想起来,完全不像自己的亲历,倒像是发生在程程或是谁家孩子身上,隔着遥远的时空,让我这个旁观的无力相助的姥爷心如刀割。
10年以后,我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曾在长江激流中屡经风险,在“大串联”中跋涉南北。正值青春热血时,却被困厄家中,既不能考学,又不能就业,天天弄个板胡吱呀乱叫。两个同学找到我,说,咱们去建筑社打工吧。
于是,就来到骄阳暴晒的工地。我被分配去担水和泥。从水井到工地也就五六十米,提水,担水,和泥,我开始了一天天地重复机械运动。
我只穿一条裤衩,着一双塑料凉鞋,一条湿漉漉的毛巾挂在脖子上。每隔半个时辰,我便用毛巾蘸足凉水从头浇到脚底。一大碗白开水喝进肚,瞬间变成汗水不翼而飞。那个二十岁的七月酷暑,应该是我生命里最强健的顶端。心里没有尊严,没有悲喜,不思考,不计前程,甚至没有语言和疲惫。唯有古铜色的皮肤和浑身隆起的肌肉令我充满自信。
后来,我当兵去了东北。东北没有酷暑。再后来,我回到山东,一直是在室内工作,并且有了电风扇和空调。
酷暑只是游荡在露天和野外,光顾那些被迫来到毒日下的求生者身上。
酷暑没有诗意,吟咏春花秋月冬雪的诗词汗牛充栋,而描写酷暑的诗歌好像只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普希金没有错,“一切都会过去。”然而,一切都会再来。而那过去了的是否是美好的回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