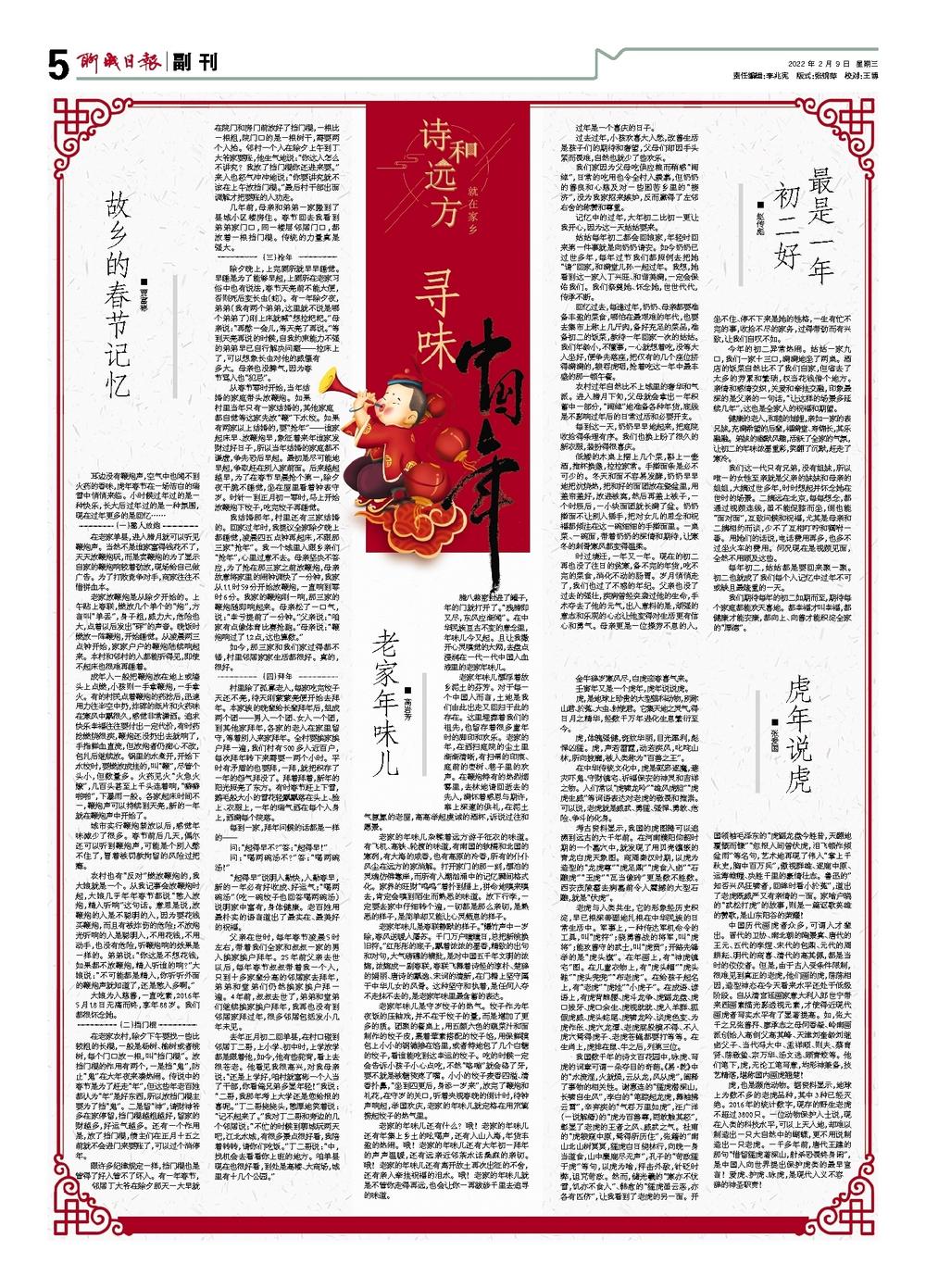最是一年初二好
■ 赵传彪
过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过去过年,小孩欢喜大人愁,改善生活是孩子们的期待和奢望,父母们却因手头紧而畏难,自然也就少了些欢乐。
我们家因为父母吃供应粮而稍感“阔绰”,日常的吃用也令全村人羡慕,但奶奶的善良和心慈及对一些困苦乡里的“接济”,没为我家招来嫉妒,反而赢得了左邻右舍的称赞和尊重。
记忆中的过年,大年初二比初一更让我开心,因为这一天姑姑要来。
姑姑每年初二都会回娘家,年轻时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向奶奶请安。如今奶奶已过世多年,每年过节我们都照例去把她“请”回家,和满堂儿孙一起过年。我想,她看到这一家人丁兴旺、和谐美满,一定会保佑我们。我们祭奠她、怀念她,世世代代,传承不断。
回忆过去,每逢过年,奶奶、母亲都要准备丰盈的菜食,哪怕在最艰难的年代,也要去集市上称上几斤肉,备好充足的菜品,准备初二的饭菜,款待一年回家一次的姑姑。我们年龄小,不懂事,一心就想着吃,没等大人坐好,便争先落座,把仅有的几个座位挤得满满的,狼吞虎咽,抢着吃这一年中最丰盛的那一顿午餐。
农村过年自然比不上城里的奢华和气派。进入腊月下旬,父母就会拿出一年积蓄中一部分,“阔绰”地准备各种年货,底线是不影响过年后的日常过活和必要开支。
每到这一天,奶奶早早地起来,把庭院收拾得条理有序。我们也换上盼了很久的新衣服,装扮得很喜庆。
低矮的木桌上摆上几个菜,斟上一壶酒,推杯换盏,拉拉家常。手擀面条是必不可少的。冬天和面不容易发酵,奶奶早早地把炕烧热,把和好的面团放在瓷盆里,用盖帘盖好,放进被窝,然后再盖上被子,一个时辰后,一小块面团就长满了盆。奶奶擀面不让别人插手,把对女儿的思念和祝福都倾注在这一碗细细的手擀面里。一桌菜、一碗面,带着奶奶的深情和期待,让寒冬的刺骨寒风都变得温柔。
时过境迁,一年又一年。现在的初二再也没了往日的贫寒,备不完的年货,吃不完的菜食,消化不动的肠胃。岁月悄悄走了,我们也过了不惑的年纪。父亲也没了过去的强壮,疾病曾经突袭过他的生命,手术夺去了他的元气,出人意料的是,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让他变得对生活更有信心和勇气。母亲更是一位操劳不息的人,坐不住、停不下来是她的性格,一生有忙不完的事,收拾不尽的家务,过得带劲而有兴致,让我们自叹不如。
今年的初二异常热闹。姑姑一家九口,我们一家十三口,满满地坐了两桌。酒店的饭菜自然比不了我们自家,但省去了太多的劳累和繁琐,权当花钱借个地方。亲情和感情交织,关爱和牵挂交融,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一句话,“让这样的场景多延续几年”,这也是全家人的祝福和期望。
健康的老人,和睦的妯娌,亲如一家的表兄妹,充满希望的后辈,福满堂、寿绵长,其乐融融。弟妹的幽默风趣,活跃了全家的气氛,让初二的年味浓墨重彩,笑翻了沉默,赶走了寒冷。
我们这一代只有兄弟,没有姐妹,所以唯一的女性至亲就是父亲的妹妹和母亲的姐姐,大姨过世多年,时时想起并怀念她在世时的场景。二姨远在北京,每每想念,都通过视频连线,虽不能促膝而坐,倒也能“面对面”,互致问候和祝福,尤其是母亲和二姨相约而谈,少不了互相叮咛和嘱咐一番。用她们的话说,电话费用再多,也多不过坐火车的费用。何况现在是视频见面,全然不用顾及这些。
每年初二,姑姑都是要回来聚一聚。初二也就成了我们每个人记忆中过年不可或缺且最隆重的一天。
我们期待每年的初二如期而至,期待每个家庭都能欢天喜地。都幸福才叫幸福,都健康才能安康,都向上、向善才能积淀全家的“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