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鱼山
■ 冯彩霞
寒冬腊月,冬风萧索,行至鱼山,一座孤墓比冬风更加萧索。
鱼山在山东东阿境内,属泰山西来余脉,海拔仅82.1米。相传,因其形似甲鱼,或曰古建鱼姑庙于山顶,故名鱼山。
鱼山之所以闻名,得益于东阿王(后称陈思王)曹植。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文学批评家钟嵘称赞曹植的诗“词采华茂,骨气奇高”;南宋文学家谢灵运也赞其“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就是这样一位才子,却郁郁不得志,颠沛流离多地,年纪轻轻就病逝异乡,时年仅41岁。因生前常有“登鱼山,临东阿,谓然有终焉之心”。于是,在曹植去世后的第二年,其子曹志遵其遗愿将其遗骸迁葬鱼山。
小小的鱼山,毗邻黄河,视野开阔。登临山顶,沐风而立,看黄河水滔滔东去,豪迈之情自会油然而生,但慨叹之声也更深重。
东阿县政府对曹植墓的保护,可谓呕心沥血。目前的鱼山,已是东阿著名的一大景区。大门庄严而阔大,厚重而肃穆。进得门来,远远就能看到曹植墓冷竣地矗立在那里。
墓室分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出土了不少文物,有些在子建祠中展览。
墓的四周有子建祠、曹植墓碑、七步桥、羊茂台、洗砚池、闻梵处、梵音洞、仙人脚印、鱼姑庙等景观相偎傍,企图安抚子建悲苦孤寂的灵魂,但不得不说,这些努力徒然无功,子建骨子里的孤独让他拒绝融入。寂寥,不仅是鱼山的气质,更是子建一生弃之不去的气质。即使喧嚣,即使繁杂,都侵入不了这寂寥。
不断有文人墨客前来拜谒子建,来人无不高抬脚、轻落步、窃窃语,生怕惊动了子建。也许,长眠的子建才是安宁的,才是平静的。
子建在东阿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年零两个月。两年之于一生,按人生的长度来计,确实太过短暂。但就是这短暂的两年,却让子建念念不忘,并愿死后以身相许,以平息内心之幽怨,以安抚灵魂之悲苦。对于此,历代赋予了他诸多传说,流传最广的是他与鱼山的鱼姑惺惺相惜。但传说终归是传说,谁能解其中奥秘?唯子建本人。
登得闻梵处,梵音袅袅,清澈空灵之声悠然绵长,直抵人心灵深处,犹如涓涓清流缓缓流淌。此时,双目轻阖,不见尘世。疲惫、烦忧与狂躁悄然而去,宁静与平和施施然而至。
子建在此始创的梵呗之音(今全称“鱼山梵呗”,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广泛流传,今在日本、韩国仍然盛行。鱼山梵呗不仅是对中国佛教音乐的巨大贡献,更可能是子建在创作之时心灵得到了片刻的安宁。也许,这才是子建立志要安葬于此的奥秘吧!
奥秘解与不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子建在死后终于顺遂了心愿。这对子建来说,应是极大的安慰。
子建的一生从少年因才情受宠,到立嗣之争,到洛水感怀,再到忧生之嗟,可谓令人唏嘘。
子建少年因才情奇高,深得曹操宠爱,并三次随父出征,曹操曾有意立其为太子。然,才子性情率直,任性而行,在心机深重且自律的曹丕面前实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更有其擅自打开司马门和临征酒醉不能受命令其彻底失宠。
建安十二年,曹植随父北征柳城(今辽宁朝阳)时,尚有《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报国之雄心;到立嗣之争败北后,即有了著名的七步诗“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伤无奈;到恍然偶遇洛神的“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的怅然若失;到曹睿继位后多次上书,仍不得重用,并屡被贬迁各地的生命之忧。
才情在性情面前一败涂地!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富含哲理的话被今人一再提起并自勉。但性情使然,又有几人能改变得了?倘若子建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改变,那他的命运是否会改写?因为前因不能确定,所以结果也未知。
人的一生,无非爱情和事业。好的爱情能让事业如虎添翼,不好的爱情能让事业雪上加霜。曹植著名的《洛神赋》在曹睿继位前叫作《感鄄赋》,据传与曹丕的甄姬有关(古时鄄与甄同音),曹丕利用甄姬之美色让曹植痛失继位之机。这爱情是有毒的。但爱情就是爱情,即使有毒,也不见曹植的痛恨与埋怨,他有的只是爱而不得的怅然,故才有了经典之作《洛神赋》。子建虽无治国之才,但仍有谦谦君子之风范。
无论后人如何感怀,子建依然是子建,子建只能是子建。他留下的诗篇,在任何时代都熠熠生辉。
如今,登临鱼山山顶,仍能听闻子建的喟叹之声。黄河依然在鱼山脚下奔涌,它翻涌的波浪上还有子建的诗句在闪亮。
一恍惚,好像看见子建正乘一匹白马飞奔而去,背影飘逸而孤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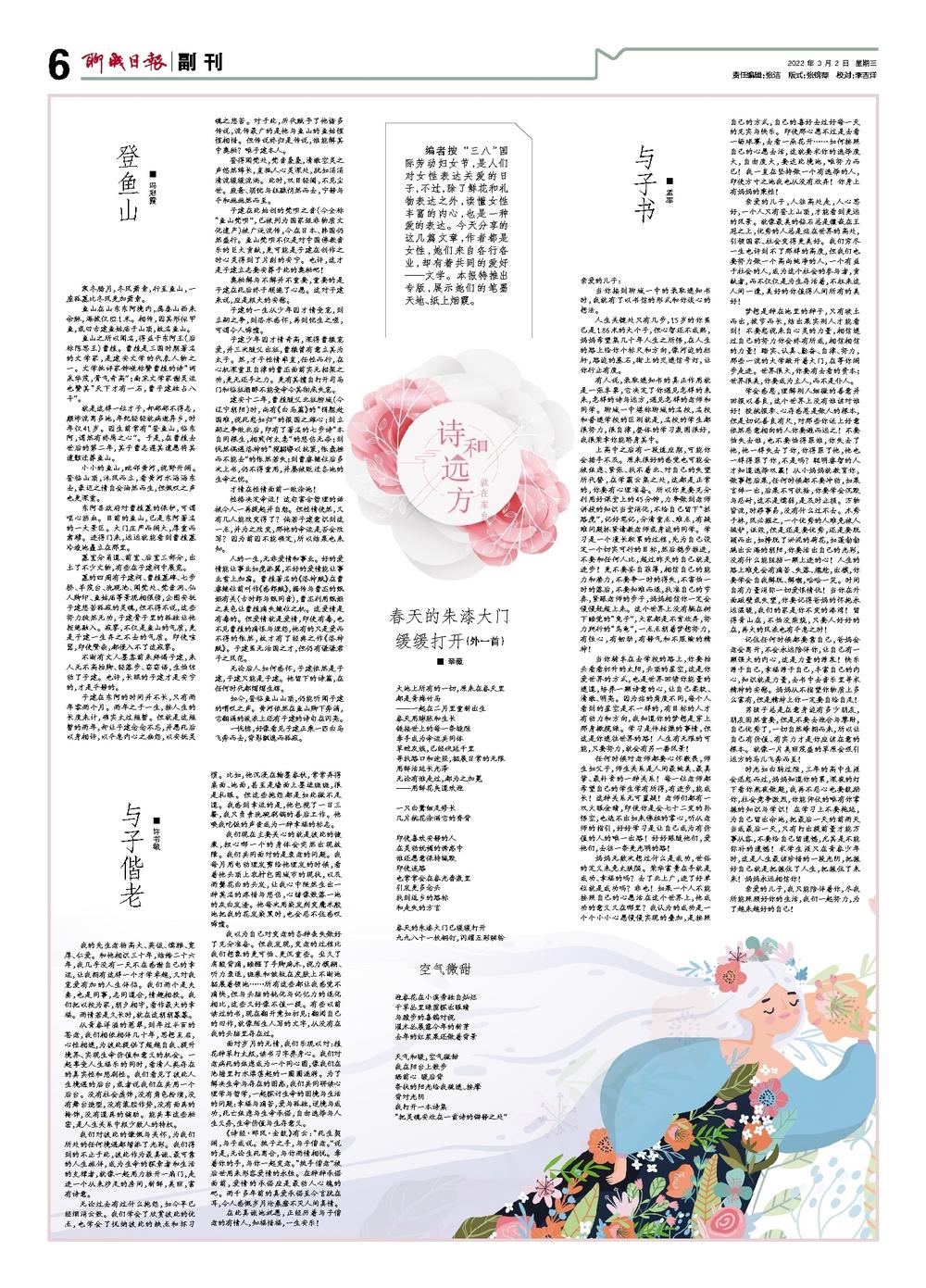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