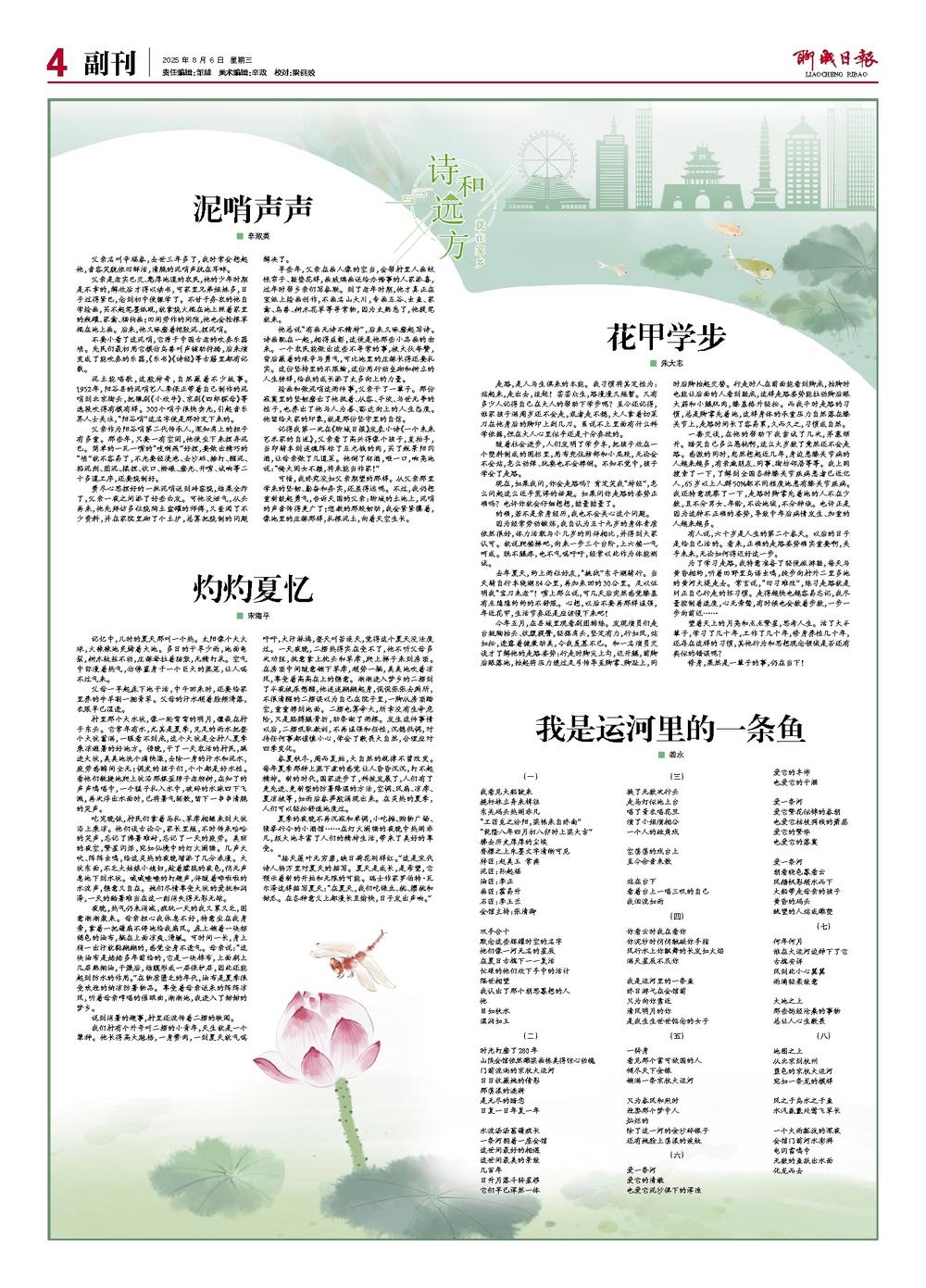泥哨声声
■ 辛淑英
父亲名叫辛福春,去世三年多了,我时常会想起他,音容笑貌依旧鲜活,清脆的泥哨声犹在耳畔。
父亲是老实巴交、憨厚地道的农民,他的少年时期是不幸的,解放后才得以读书,可家里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紧巴,念到初中便辍学了。不甘于务农的他自学绘画,买不起笔墨纸砚,就拿烧火棍在地上照着家里的瓶罐、家禽、猫狗画;田间劳作的间隙,他也会捡根草棍在地上画。后来,他又琢磨着挖胶泥、捏泥哨。
不要小看了这泥哨,它源于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埙。先民们最初用它模仿鸟兽叫声辅助狩猎,后来演变成了能吹奏的乐器,《乐书》《诗经》等古籍里都有记载。
泥土能唱歌,这般神奇,自然藏着不少故事。1952年,阳谷县的泥哨艺人李保正带着自己制作的泥哨到北京街头,把豫剧《小放牛》、京剧《四郎探母》等选段吹得有模有样。300个哨子很快卖光,引起音乐界人士关注,“阳谷哨”这名字便是那时定下来的。
父亲作为阳谷哨第二代传承人,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那些年,只要一有空闲,他便坐下来捏弄泥巴。简单的一孔一嘴的“吱喇燕”好捏,要做出精巧的“埙”就不容易了,不光要经浸泡、去沙砾、捶打、醒泥、掐泥剂、团泥、揉捏、收口、擀碾、磨光、开嘴、试响等二十多道工序,还要烧制好。
费尽心思捏好的一批泥哨送到砖窑烧,结果全炸了,父亲一夜之间添了好些白发。可他没泄气,从头再来,他先拜访多位烧陶土盆罐的师傅,又查阅了不少资料,并在家院里砌了个土炉,总算把烧制的问题解决了。
早些年,父亲在画人像的空当,会帮村里人画蚊帐帘子、鞋垫花样,画玻璃画送给办婚事的人家添喜,过年时帮乡亲们写春联。到了老年时期,他才真正在宣纸上绘画创作,不画名山大川,专画五谷、虫鱼、家禽、鸟兽、树木花草等寻常物,因为太熟悉了,他提笔就来。
他总说“有画无诗不精神”,后来又琢磨起写诗。诗画配在一起,相得益彰,这便是他那些小品画的由来。一个农民能做出这些不寻常的事,被大伙夸赞,背后藏着的艰辛与勇气,可比地里的庄稼长得还要扎实。这份坚持里的不服输,这份用行动垒砌和树立的人生榜样,给我的成长添了太多向上的力量。
绘画和做泥哨这两件事,父亲干了一辈子。那份寂寞里的坚韧磨出了他执着、从容、平淡、与世无争的性子,也养出了他与人为善、豁达向上的人生态度。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那份坚守里的自信。
记得我第一次在《聊城日报》发表小诗《一个未来艺术家的自述》,父亲看了高兴得像个孩子,直拍手,当即骑车到迷魂阵称了五元钱的肉,买了瓶景阳冈酒,让母亲做了几道菜。他倒了杯酒,咂一口,响亮地说:“俺大闺女不赖,将来能当作家!”
可惜,我终究没如父亲期望的那样。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坚韧、勤奋和务实,还差得远呢。不过,我仍想重新鼓起勇气,告诉天国的父亲:聊城的土地上,泥哨的声音传得更广了;您教的那股韧劲,我会紧紧攥着,像地里的庄稼那样,扎根泥土,向着天空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