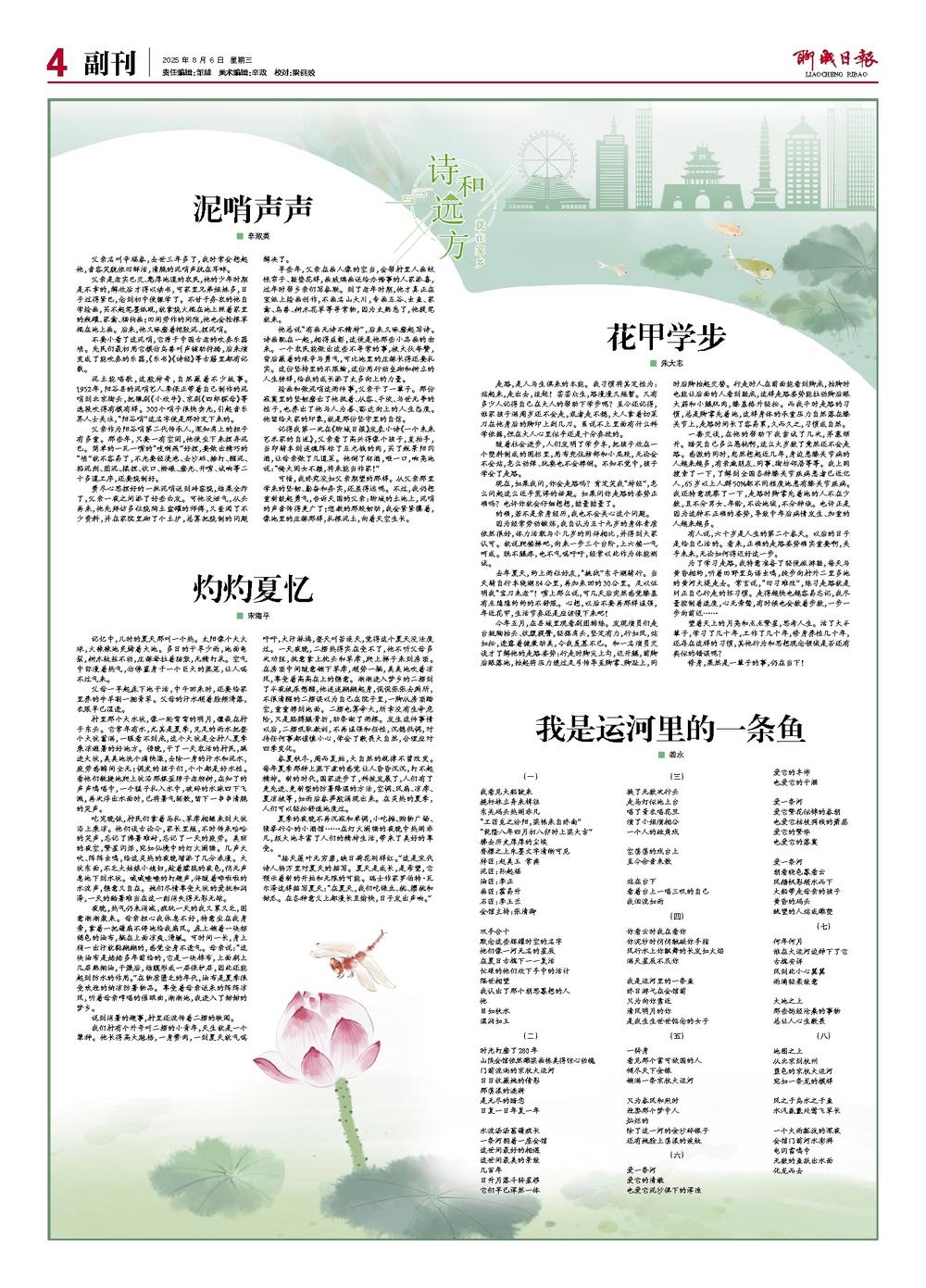灼灼夏忆
■ 宋海平
记忆中,儿时的夏天那叫一个热。太阳像个大火球,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多日的干旱少雨,地面龟裂,树木纹丝不动,庄稼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空气中弥漫着热气,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让人喘不过气来。
父母一早起床下地干活,中午回来时,还要给家里养的牛羊割一捆青草。父母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衣服早已湿透。
村里那个大水坑,像一轮弯弯的明月,镶嵌在村子东头。它常年有水,尤其是夏季,充足的雨水把整个大坑蓄满,一眼看不到底,这个大坑是全村人夏季乘凉避暑的好地方。傍晚,干了一天农活的村民,跳进大坑,美美地洗个痛快澡,去除一身的汗水和泥水,疲劳感瞬间全无;调皮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水性。看他们敏捷地爬上坑沿那棵歪脖子老柳树,在知了的声声鸣唱中,一个猛子扎入水中,破碎的水珠四下飞溅,再次浮出水面时,已将暑气驱散,留下一串串清脆的笑声。
吃完晚饭,村民们拿着马扎、草席相继来到大坑沿上乘凉。他们谈古论今,家长里短,不时传来哈哈的笑声,忘记了溽暑难耐,忘记了一天的疲劳。美丽的夜空,繁星闪烁,宛如仙境中的灯火阑珊。几声犬吠、阵阵虫鸣,给这炎热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浪漫。大坑东面,不乏大姑娘小媳妇,趁着朦胧的夜色,悄无声息地下到水坑。嘁嘁喳喳的打趣声,伴随着哗啦啦的水流声,惬意又自在。她们尽情享受大坑的爱抚和润泽,一天的酷暑难当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晚,热气仍未消减,疯玩一天的我又累又乏,困意渐渐袭来。母亲担心我休息不好,特意坐在我身旁,拿着一把蒲扇不停地给我扇风。床上铺着一块棕褐色的油布,躺在上面凉爽、滑腻。可时间一长,身上稍一出汗就黏糊糊的,感觉全身不透气。母亲说:“这块油布是姥姥多年前给的,它是一块棉布,上面刷上几层熟桐油,干燥后,结膜形成一层保护层,因此还能起到防水的作用。”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油布是夏季很受欢迎的纳凉防暑物品。享受着母亲送来的阵阵凉风,听着母亲哼唱的催眠曲,渐渐地,我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说到消暑的趣事,村里还流传着二楞的轶闻。
我们村有个外号叫二楞的小青年,天生就是一个犟种。他长得高大魁梧,一身赘肉,一到夏天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整天叫苦连天,觉得这个夏天没法度过。一天夜晚,二楞热得实在受不了,他不听父母多次劝阻,执意拿上枕头和草席,爬上梯子来到房顶。在房顶中间随意铺下草席,顺势一躺,美美地吹着凉风,享受着高高在上的惬意。渐渐进入梦乡的二楞到了半夜被尿憋醒,他迷迷糊糊起身,慌慌张张去厕所,不很清醒的二楞误以为自己在院子里,一脚从房顶踏空,重重摔到地面。二楞也算命大,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胳膊腿骨折,肋条断了两根。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二楞吸取教训,不再逞强和任性,沉稳低调,对待任何事都谨慎小心,学会了敬畏大自然,合理应对四季变化。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大自然的规律不曾改变。每年夏季那种上蒸下煮的感觉让人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新的时代,国家进步了,科技发展了,人们有了更先进、更新型的防暑降温的方法,空调、风扇、凉席、夏凉被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炎热的夏季,人们可以轻松舒适地度过。
夏季的夜晚不再沉寂和单调,小吃摊、购物广场、猜拳行令的小酒馆……在灯火阑珊的夜晚中热闹非凡,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美好的享受。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对夏天的描写。夏天是成长,是希望,它预示着新的开始和无限的可能。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这样描写夏天:“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