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 收
◇ 吴怀国
我的故乡在鲁西北,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每年芒种时节,田野里一片片金黄的麦浪,微风吹来阵阵清新的麦香。
现在的麦收速度很快。我村有3000多亩麦田,在收割机和播种机的穿梭下,七天左右就能完成收种。可是,20世纪70年代的麦收完全不同,所有的活都需要人工,割麦子、送往打谷场就得半个月左右。麦子运到场里后,全体社员摊、翻、晒干后,再让牛马拉着石碾碾压,然后拾场、堆场、扬场。人工割麦,地里免不了落下一些麦子。于是,拾麦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少年身上。
当时,我在村里读三四年级,学校每年放三次假——麦假、秋假、寒假。放麦假时,老师就领着我们生产队的十四五个学生去地里拾麦子。当时我们队里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吴纪勋老师,一个是吴纪坤老师,他俩都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都比较清瘦。吴纪勋老师个子较矮,但很有精神。
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里的青壮劳力就出工了,他们每人一垄,争先恐后地割起来。我们吃了早饭后在生产队的草屋(饲养场)集合,由老师带队去地里。这时太阳已升起一竿多高,向平原尽头望去,田间地头上插着许多红旗,数百名男女劳力分布在不同的地块劳作。大路上行人不断,有往打谷场运麦子的年轻人,还有给割麦人送饭的老人。
我们唱着歌来到地头上,割麦人大多在地头上歇着,等着家人来送饭。他们的头上热气腾腾,衣衫紧贴在脊背上,有的喘着粗气,有的蹲在一起说笑,有的磨着镰刀。满脸皱纹的老队长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嘶哑的嗓音掩不住收获的喜悦。他是老贫农出身,从小就给地主当长工,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翻了身。如今他精神焕发,操心着割麦子、捆麦子、运麦子。
起初几天,我们都感觉很新鲜,很有干劲。但渐渐地,我们的身体就吃不消了。日头火热时,我们拾上一会儿,老师就领我们到树荫下歇一会儿,给我们发几块薄荷片。薄荷片吃到嘴里凉凉甜甜的,这都是老队长买的,说孩子们受不惯热。
我们在路边树荫下歇息的时候,老师还给我们讲故事,或者教我们唱歌。吴纪勋老师是学区校长,要不断去开政治会、教育会,不常带我们拾麦子。
吴纪坤老师个子略高些,他常带着我们劳动,歇息时,他教我们唱“学大寨歌”“学毛选”……他虽不专业,但非常用心,一边教,一边挥舞着双手,清瘦的脸上神情专注,双目炯炯有神。路边大树上一幅标语是“学大寨,赶昔阳,快马加鞭过长江”,我们十几双眼睛盯着老师学,唱了一遍又一遍,再望望树上的大红标语,深感拾麦责任重大。
夕阳西下,我们收工了,就又排起长队,唱着歌回家。一晃40多年过去了,儿时麦收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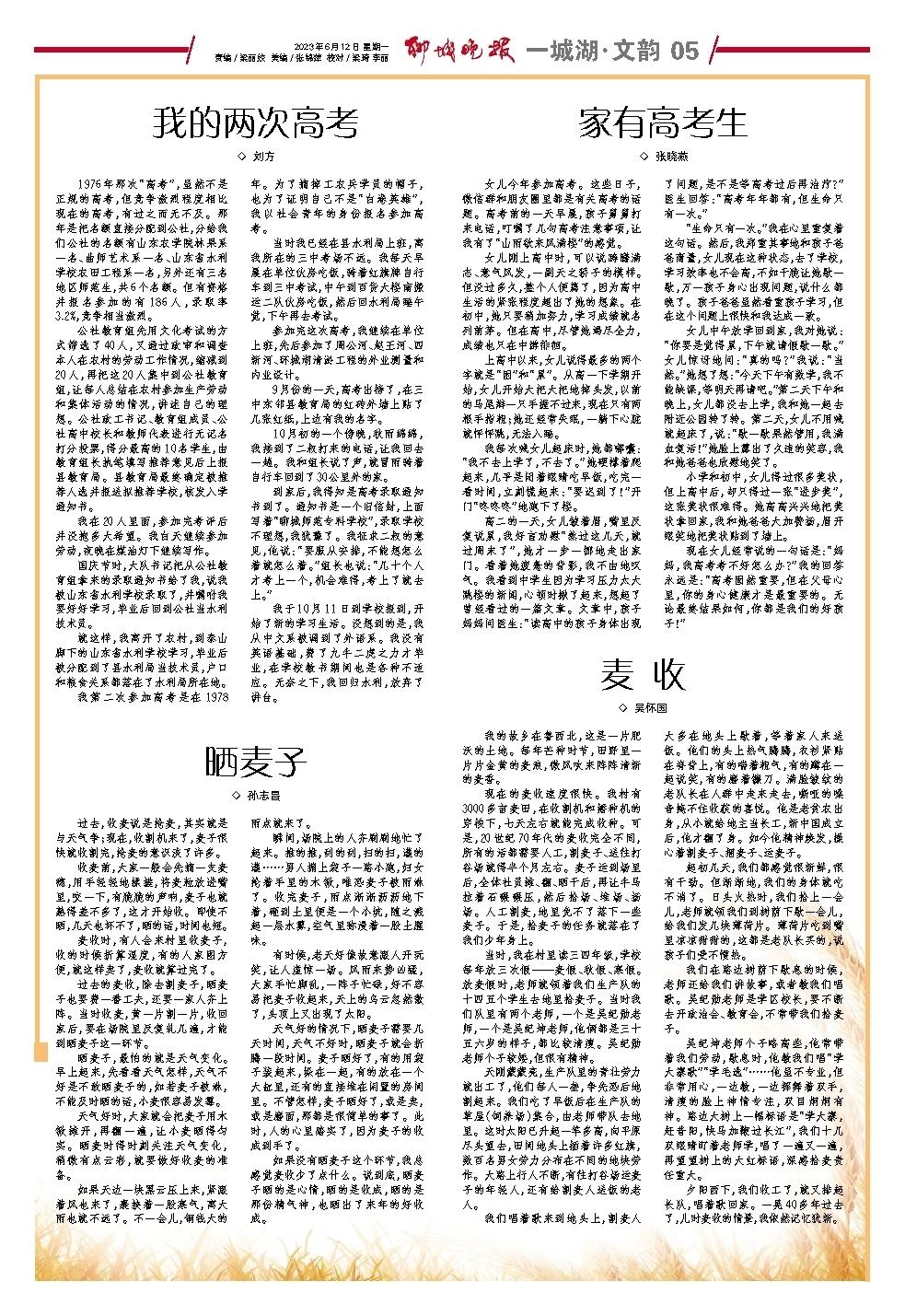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