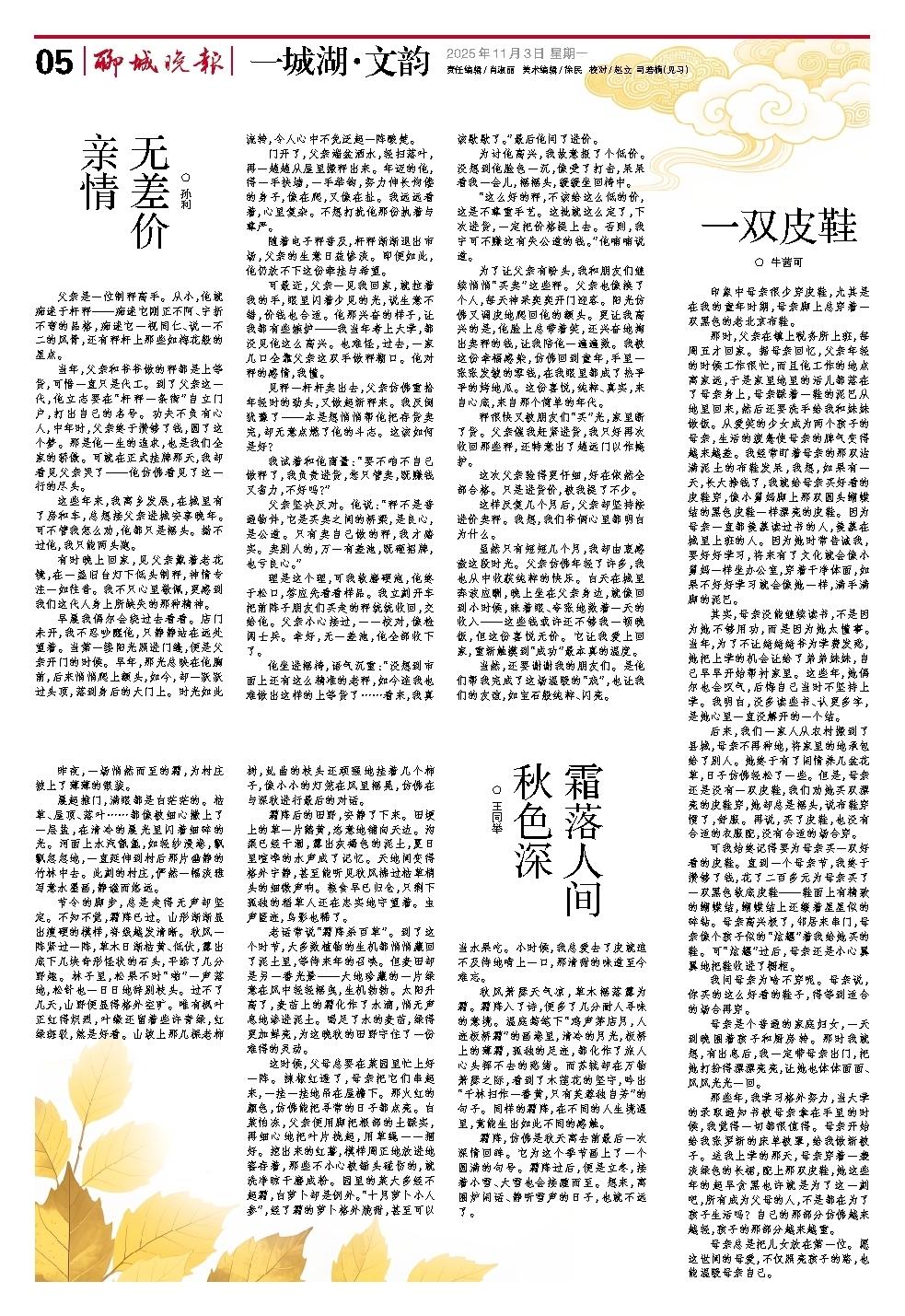亲情无差价
○ 孙利
父亲是一位制秤高手。从小,他就痴迷于杆秤——痴迷它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品格,痴迷它一视同仁、说一不二的风骨,还有秤杆上那些如梅花般的星点。
当年,父亲和爷爷做的秤都是上等货,可惜一直只是代工。到了父亲这一代,他立志要在“杆秤一条街”自立门户,打出自己的名号。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年时,父亲终于攒够了钱,圆了这个梦。那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可就在正式挂牌那天,我却看见父亲哭了——他仿佛看见了这一行的尽头。
这些年来,我离乡发展,在城里有了房和车,总想接父亲进城安享晚年。可不管我怎么劝,他都只是摇头。拗不过他,我只能两头跑。
有时晚上回家,见父亲戴着老花镜,在一盏旧台灯下低头制秤,神情专注一如往昔。我不只心里敬佩,更感到我们这代人身上所缺失的那种精神。
早晨我偶尔会绕过去看看。店门未开,我不忍吵醒他,只静静站在远处望着。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门缝,便是父亲开门的时候。早年,那光总映在他胸前,后来悄悄爬上额头,如今,却一跃跃过头顶,落到身后的大门上。时光如此流转,令人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酸楚。
门开了,父亲端盆洒水,轻扫落叶,再一趟趟从屋里搬秤出来。年迈的他,得一手扶墙,一手举钩,努力伸长佝偻的身子,像在爬,又像在扯。我远远看着,心里复杂。不想打扰他那份执着与尊严。
随着电子秤普及,杆秤渐渐退出市场,父亲的生意日益惨淡。即便如此,他仍放不下这份牵挂与希望。
可最近,父亲一见我回家,就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少见的光,说生意不错,价钱也合适。他那兴奋的样子,让我都有些嫉妒——我当年考上大学,都没见他这么高兴。也难怪,过去,一家几口全靠父亲这双手做秤糊口。他对秤的感情,我懂。
见秤一杆杆卖出去,父亲仿佛重拾年轻时的劲头,又做起新秤来。我反倒犹豫了——本是想悄悄帮他把存货卖完,却无意点燃了他的斗志。这该如何是好?
我试着和他商量:“要不咱不自己做秤了,我负责进货,您只管卖,既赚钱又省力,不好吗?”
父亲坚决反对。他说:“秤不是普通物件,它是买卖之间的桥梁,是良心,是公道。只有卖自己做的秤,我才踏实。卖别人的,万一有差池,既砸招牌,也亏良心。”
理是这个理,可我软磨硬泡,他终于松口,答应先看看样品。我立刻开车把前阵子朋友们买走的秤统统收回,交给他。父亲小心接过,一一校对,像检阅士兵。幸好,无一差池,他全部收下了。
他坐进摇椅,语气沉重:“没想到市面上还有这么精准的老秤,如今连我也难做出这样的上等货了……看来,我真该歇歇了。”最后他问了进价。
为讨他高兴,我故意报了个低价。没想到他脸色一沉,像受了打击,呆呆看我一会儿,摇摇头,缓缓坐回椅中。
“这么好的秤,不该给这么低的价,这是不尊重手艺。这批就这么定了,下次进货,一定把价格提上去。否则,我宁可不赚这有失公道的钱。”他喃喃说道。
为了让父亲有盼头,我和朋友们继续悄悄“买卖”这些秤。父亲也像换了个人,每天神采奕奕开门迎客。阳光仿佛又调皮地爬回他的额头。更让我高兴的是,他脸上总带着笑,还兴奋地掏出卖秤的钱,让我陪他一遍遍数。我被这份幸福感染,仿佛回到童年,手里一张张发皱的零钱,在我眼里都成了热乎乎的烤地瓜。这份喜悦,纯粹、真实,来自心底,来自那个简单的年代。
秤很快又被朋友们“买”光,家里断了货。父亲催我赶紧进货,我只好再次收回那些秤,还特意出了趟远门以作掩护。
这次父亲验得更仔细,好在依然全部合格。只是进货价,被我提了不少。
这样反复几个月后,父亲却坚持按进价卖秤。我想,我们爷俩心里都明白为什么。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我却由衷感激这段时光。父亲仿佛年轻了许多,我也从中收获纯粹的快乐。白天在城里奔波应酬,晚上坐在父亲身边,就像回到小时候,眯着眼、夸张地数着一天的收入——这些钱或许还不够我一顿晚饭,但这份喜悦无价。它让我爱上回家,重新触摸到“成功”最本真的温度。
当然,还要谢谢我的朋友们。是他们帮我完成了这场温暖的“戏”,也让我们的友谊,如宝石般纯粹、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