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乘凉二门下
■ 王庆国
盛夏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处处都像是有火在熊熊燃烧,人们除非迫不得已绝不出门,闭关在家吹空调。傍晚在小区散步,就听有老年人感慨,现在有空调还热得叫人受不了,以前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那些酷暑炎夏也没觉得有这么热!
我不由想起老家大院子里有穿堂风吹过的二门。二门以里是内院,有正房叫北屋,有偏房为东屋西屋。二门外是外院,跟内院差不多大,东西两侧长着大槐树、榆树、枣树,西北墙角处还有羊圈、鸡窝。
二门的作用,有书上说:止,观是。它对内院起隐蔽作用,有客人突然来访,进来大门,隔着二门喊一声,主人听到,能及时抻抻衣服,理一下乱丝,擦一把脸,绝不至于蓬头垢面,慌乱无措。于我,印象最深的是炎炎夏日它的屋檐下有凉风吹过。
由于我们是跟太爷爷太奶奶住一处,北屋是正房,自然是太爷爷太奶奶住,父母、妹妹和我则只能住在偏房里。
儿时,每当我在外面玩耍回来,进屋就喊热死了,这时忙着做饭的母亲在东屋顺手扔给我一个用玉米皮编织的蒲团,“到二门下去凉快会儿,饭一会儿就好了。”我就喝着一碗凉开水,坐在蒲团上,在二门下吹风,舒服得很。凉飕飕的小风竟能吹走饥饿感,还没听到肚子咕噜叫,母亲那里就喊吃饭了。我进屋端一碗面条,里面拌上母亲切得细碎的红萝卜、香椿芽和滴了几滴棉油调好的咸菜,有时是左手玉米饼子右手一根腌红萝卜,有时也双手捧着一个大菜荠馏,坐在小风里“吧嗒吧嗒”地吃得那个香甜,难以言喻。
白天,二门下是太奶奶的地盘。太奶奶的脚是三寸金莲,没法下田干活,一天三餐、家务活、缝缝补补,便成了太奶奶天天干不败的活。等太爷爷吃罢饭抽袋烟,扛上农具下田去后,太奶奶便端出针线筐子,坐在小凳子上,在二门下开始缝补。针线活就像是太奶奶绵长的日子,什么时候也做不完。母亲也下地干活去了,我就跟着太奶奶玩。那时太奶奶六十多岁的年纪,头发花白,在脑后梳一个髻,用一个黑色的发网罩着,干净利落。她常穿一件乳白色的质地柔软的短袖汗衫,二门的穿堂小风一吹,汗衫便似水波荡漾,轻轻飘摆,衣角飞扬。每当这时,太奶奶的针线上下翻飞得最快。太奶奶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讲她沉淀了大半辈子的民间故事。
夜晚的乘凉则是二门每天的“大戏”。吃罢晚饭,太爷爷来到二门下,把那张竹子躺椅撑开,圆柱形白底红花的茶壶放在一旁的石墩上,手摇着一把蒲扇躺下来。太奶奶刷洗完,也会拿把蒲扇搬个小凳子坐过来,东家长西家短地聊一阵子。母亲是最忙碌的,她的精力和力气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偶尔活干完得早一点,她便坐过来,与太奶奶聊些生活的事,什么样的柴好烧、起火,什么样的柴没劲、虚;向锅壁上贴饼子,什么火候最好,不溜锅,还不焦糊……母亲也跟太爷爷说说庄稼地里的事,玉米地该施肥了,花生地到锄草时了,棉花要收花了……
我则早早地将蛇皮袋子缝制的大包布靠着太爷爷铺下,上面铺个薄褥子,再铺上一张草席,既凉快隔潮还不硌,舒服极了。我光着脚丫子在草席上拿小树枝为太爷爷太奶奶表演孙猴子,抓耳挠腮,耍弄“金箍棒”,还翻“筋斗云”,折腾得差不多了,就为家人唱戏。那时农村的娱乐除了农闲时放场电影就是流动剧团到镇上唱戏。我喜欢戏里的小生、花旦、青衣,他们干净漂亮,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美。我跟着也学几句戏词,就“咿咿呀呀”地“卖”给大家。虽无调无腔,也五音不全,可太爷爷太奶奶看着就是高兴。等折腾得累了,就躺在凉席上,吹着晚风,有一句没一句地听太奶奶和母亲说话。
外院的树木像被风挠了胳肢窝“哗哗啦啦”地笑得停不下来,阵阵清风送来惬意的凉爽,还带着墙外荷塘里的阵阵荷香。我就在阵阵清香里,在浓浓的亲情氛围里,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醒来时,已在屋里的蚊帐里。
后来,太爷爷太奶奶住的北屋历经岁月,墙壁腐蚀得斑驳陆离,需要翻新。爷爷奶奶又不在家,父亲便出资,推倒老屋重新盖了一座宽敞漂亮的新房。二门虽然也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父亲没舍得推倒它,而是重新修葺加固了它,依然保持着它的原貌。
现在,40多年过去了。老院子的房子在风雨剥蚀中躺在了岁月里,二门也陪着一同睡去了。可二门始终完整保存在我的乡愁里,矗立在我的思乡情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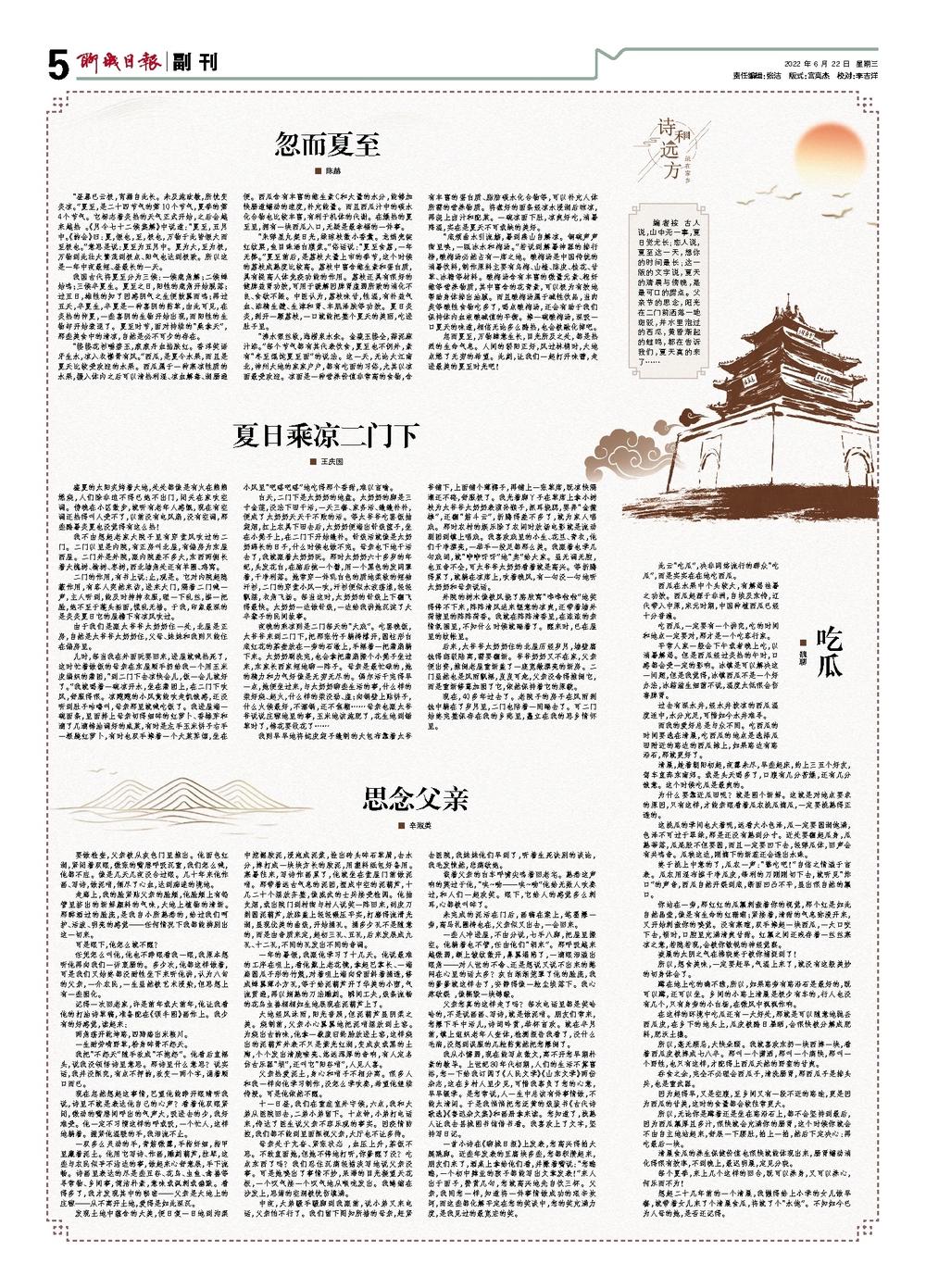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