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黄了
■ 王洪朝
“光棍哪住?我在十固,吃的啥饭?喝的糊涂。还吃点不?俺不俺不”。清晨,在布谷鸟的叫声中醒来。这神奇的候鸟告诉我,割麦插禾的季节到了。
趁着傍晚下班,买上些吃的,驱车到农村老家瞧瞧去,看看老家的麦子收了没有。
一路上,已收的麦子已晒在了公路上,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味儿。未收的麦子在风中摇曳着,夕阳下一片黄澄澄的丰收景象。机械化的操作,再也感觉不到“麦熟一晌,虎口夺粮”那热火朝天的氛围了。
还记得儿时过麦的情形。生产队时,青壮劳力在前面割麦,家庭妇女和孩子们在后面敛麦子。那一个工两毛钱的年代,孩童的我在麦假期间也分得一份撒草腰子的活儿。虽然一晌挣1到2个工分,但欢快得像小鸟,乐得屁颠屁颠的。
包产到户后,自己也每年拿起镰刀成了家庭主力。早早起床,带上草帽、毛巾、水壶,磨刀石、过年腌的灌肠、清明时节腌的咸蛋,帮着大人们轧场、起场、扬场、看场、跺麦垛。在那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抗争的年代,人赶老牛的吆喝声,老牛拉石磙的吱扭声,堆成小山的麦轮,夜晚旷野的虫鸣,眨眼的星星,都成了沉甸甸历史的记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又结婚生子,迫于生计,卖过滕州的羊河牌镰刀,而且在现场还像耍杂耍般用镰刀削铁棍做些演示,砍得火星子飞迸,口中还念叨“省钱不省力,省力不省钱”的词儿。还自编了“大草帽、小草帽,过麦人人离不了”,“大毛巾,小毛巾,人人买得都放心”的顺口溜儿。虽然每年小赚个三五百,但在那个月工资只有百元年代已是很可观了。
后来有了小收割机、小打麦机,虽每人都弄得灰头满脑,个个似包公再世,却省去了好多劳力。再不像以前,过麦就像打仗,全家齐上阵,累得腰酸腿痛,半月才过完麦。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社会的进步使卖镰刀的生意也搁浅了。再后来,有了大型收割机,机子一过,颗粒归仓。
近些年,每年都还是回家过麦,虽帮不上什么忙,但对年老的父母至少也是个心理安慰。也许是在城里待久了,身体有些娇气。每次回来浑身都会痒痒难忍,一抓就起些小疙瘩。咨询医生说是麦芒毒,季节性过敏反应。
到家已近晚上8点,母亲在院子里种的黄瓜已爬满了架杆儿, 几只麦黄知了在老树上吟唱着夏季的风采,展示着自己的歌喉。父母说,麦子熟了,还没有割。有大型机械在,不让我们担心了。
麦子黄了,无非是个理由。孩子想着父母,父母念着孩子。回家看看,一次暂短的晚餐,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足矣!
麦子黄了是丰收的迹象,人老了,也要收割精神的麦田。只是布谷鸟不一定准时提醒,麦黄知了也不一定按时吟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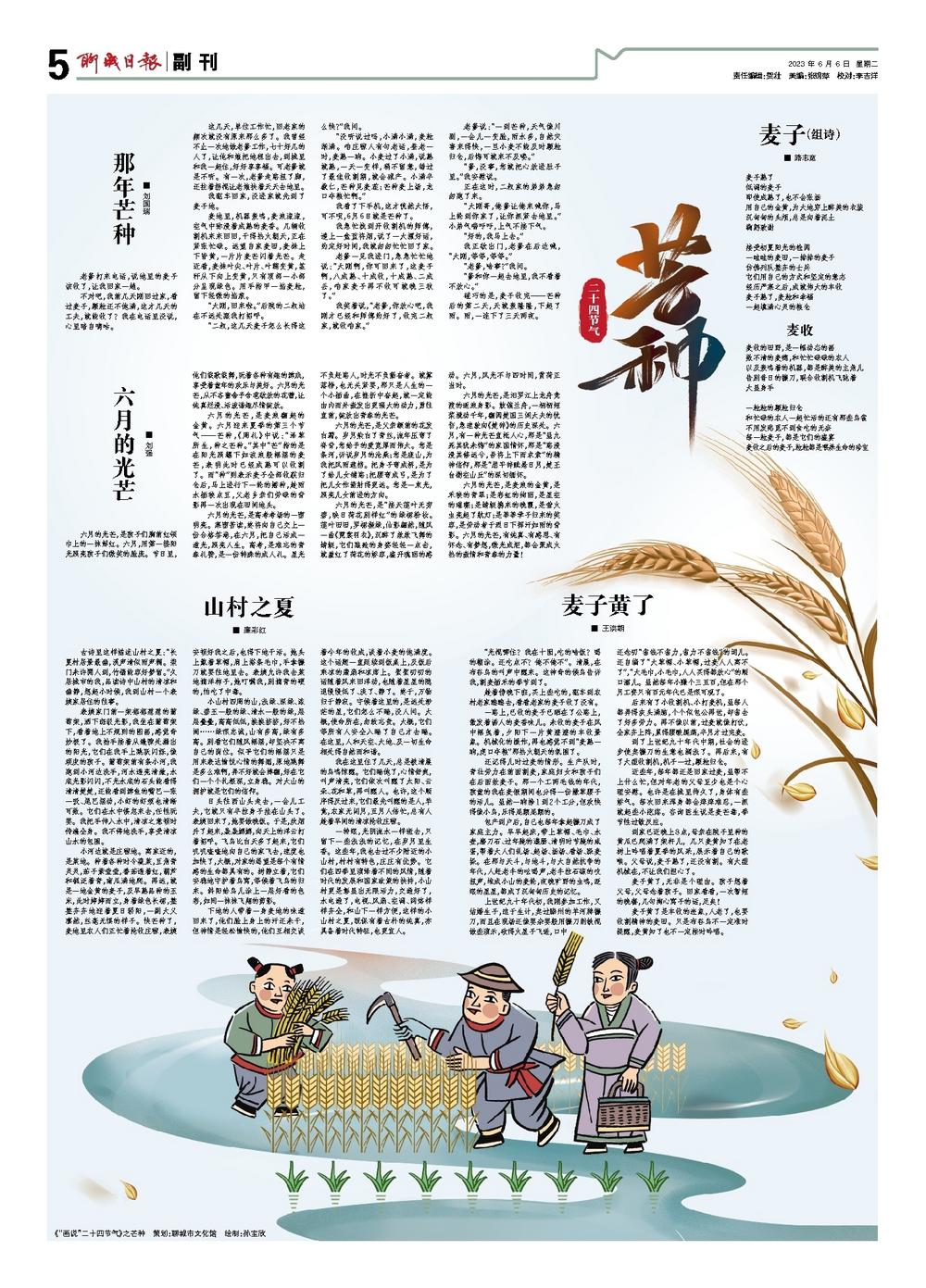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