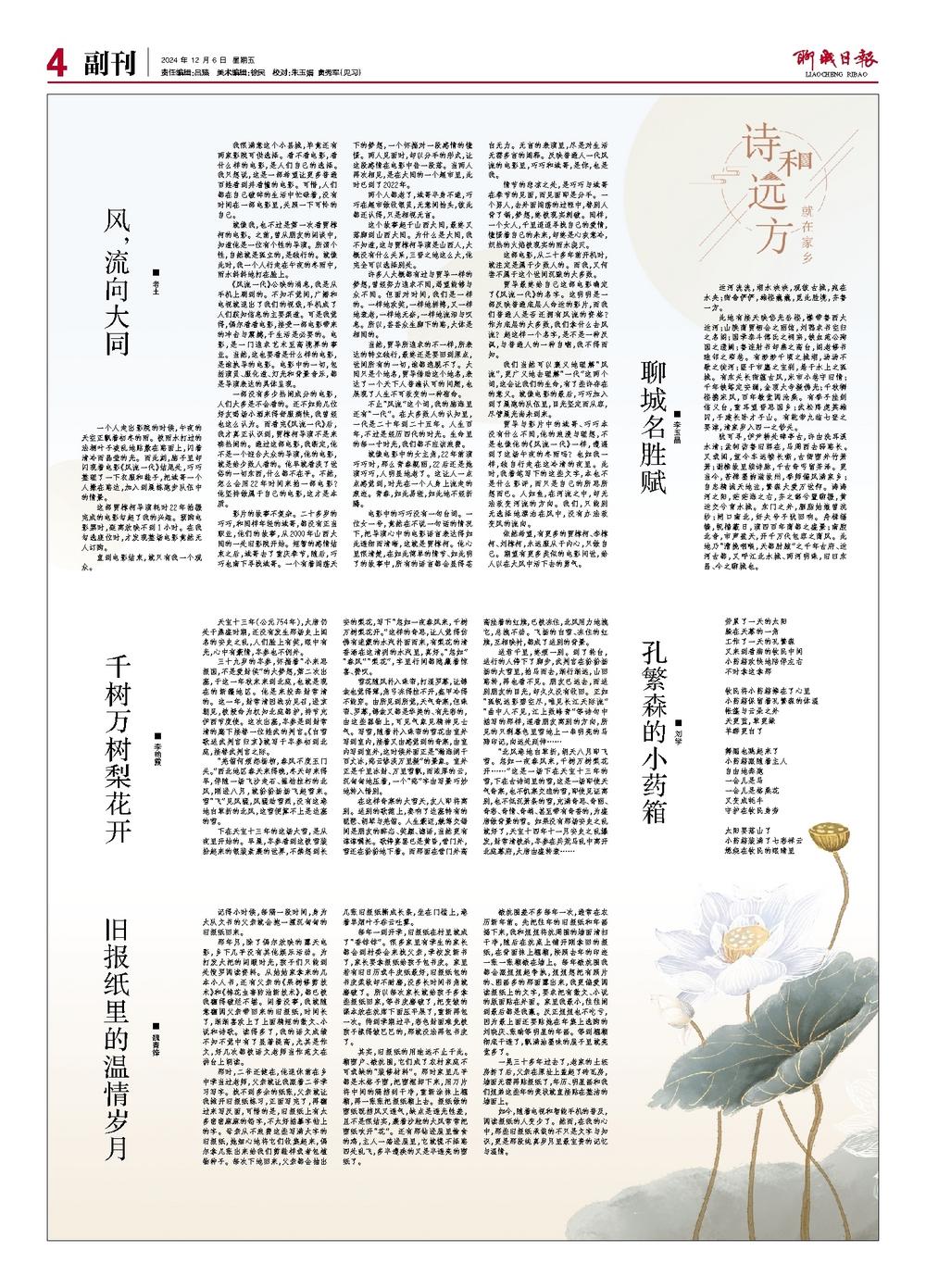旧报纸里的温情岁月
■ 魏青锋
记得小时候,每隔一段时间,身为大队文书的父亲就会抱一摞沉甸甸的旧报纸回来。
那年月,除了偶尔放映的露天电影,乡下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为打发大把的闲暇时光,孩子们只能到处搜罗阅读资料。从姑姑家拿来的几本小人书,还有父亲的《果树修剪技术》和《棉花虫害防治新技术》,都已被我翻得破烂不堪。闲着没事,我就随意翻阅父亲带回来的旧报纸,时间长了,渐渐喜欢上了上面精短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读得多了,我的语文成绩不知不觉中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作文,好几次都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讲台上朗读。
那时,二爷还健在,他退休前在乡中学当过老师,父亲就让我跟着二爷学习写字。找不到多余的纸张,父亲就让我摊开旧报纸练习,正面写完了,再翻过来写反面,可惜的是,旧报纸上有太多密密麻麻的铅字,不太好描摹字帖上的字。母亲从不浪费这些写满大字的旧报纸,她细心地将它们收集起来,偶尔拿几张出来给我们剪鞋样或者包植物种子。每次下地回来,父亲都会抽出几张旧报纸撕成长条,坐在门槛上,卷着旱烟叶子吞云吐雾。
每年一到开学,旧报纸在村里就成了“香饽饽”。很多家里有学生的家长都会到村委会来找父亲,学校发新书了,家长要拿报纸给孩子包书皮。家里若有旧日历或牛皮纸最好,旧报纸包的书皮柔软却不耐磨,没多长时间书角就磨破了。所以每次家长就给孩子多拿些报纸回家,等书皮磨破了,把变皱的课本放在炕席下面压平展了,重新再包一次。待到学期过半,彩色封面难免被孩子揉得皱巴巴的,那就没法再包书皮了。
其实,旧报纸的用途远不止于此。糊窗户、裱炕围,它们成了农村家庭不可或缺的“装修材料”。那时家里几乎都是木格子窗,把窗框卸下来,用刀片将中间的隔挡刮干净,重新涂抹上糨糊,再一张张把报纸糊上去。报纸做的窗纸既挡风又透气,缺点是透光性差,且不是很结实,裹着沙粒的大风常常把窗纸吹开“花”。还有那钻进屋里偷食的鸡,主人一踏进屋里,它就慌不择路四处乱飞,多半遭殃的又是半透亮的窗纸了。
裱炕围差不多每年一次,通常在农历新年前。先把往年的旧报纸和年画揭下来,我和姐姐将炕周围的墙面清扫干净,随后在炕桌上铺开刚拿回的报纸,在背面抹上糨糊,按照去年的印迹一张一张糊裱在墙上。每年裱炕围我都会跟姐姐起争执,姐姐想把有照片的、图画多的那面露出来,我更偏爱阅读报纸上的文字,要求把有散文、小说的版面贴在外面。家里我最小,往往闹到最后都是我赢。反正姐姐也不吃亏,因为最上面还要贴她在年集上选购的刘晓庆、张瑜等明星的年画。等到糨糊彻底干透了,飘满油墨味的屋子里就亮堂多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家的土坯房拆了后,父亲在原址上盖起了砖瓦房,墙面无需再贴报纸了,年历、明星画和我们姐弟这些年的奖状就直接贴在整洁的墙面上。
如今,随着电视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阅读报纸的人变少了。然而,在我的心中,那些旧报纸承载的不只是文字与知识,更是那段纯真岁月里最宝贵的记忆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