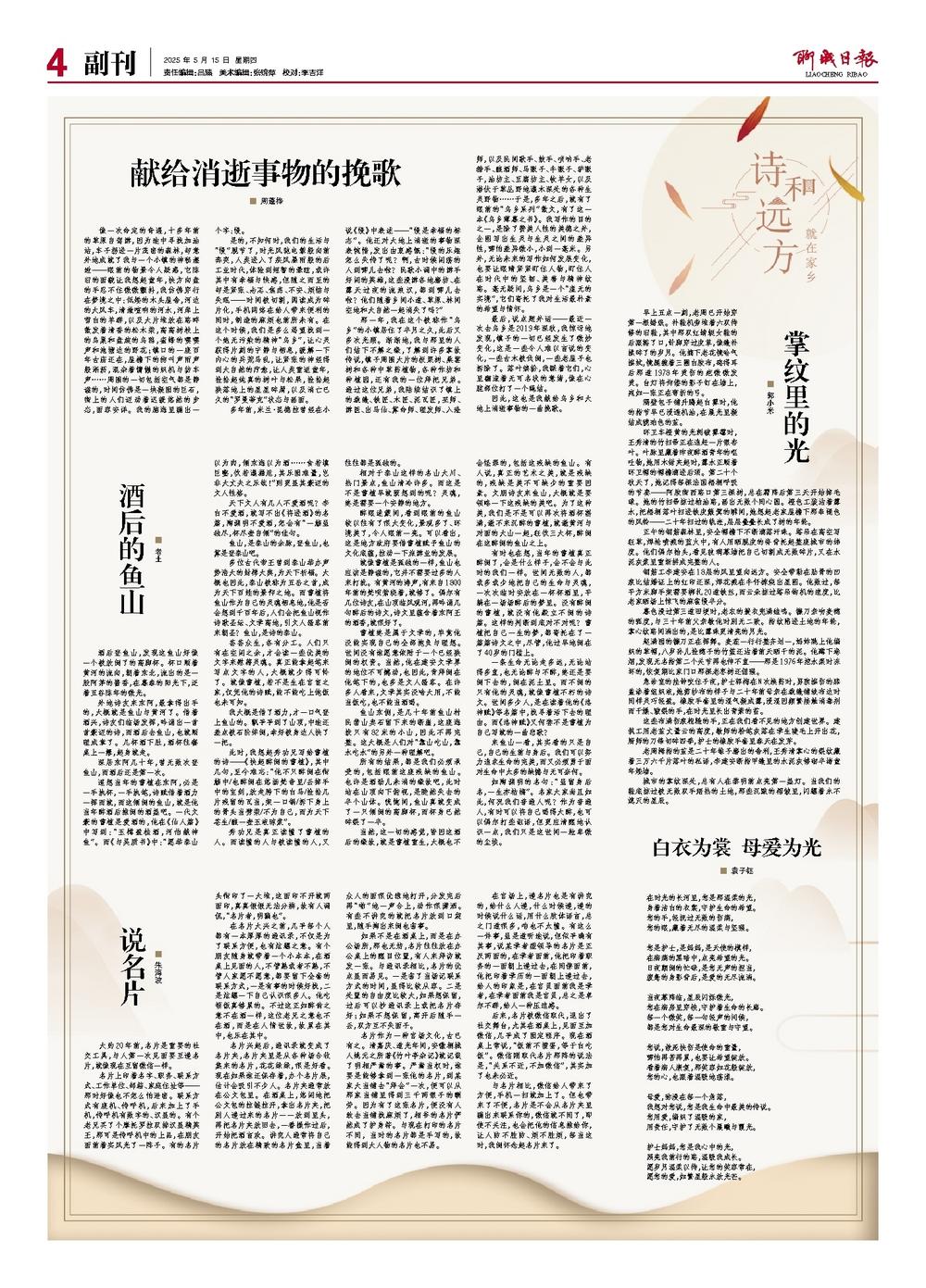献给消逝事物的挽歌
■ 周蓬桦
像一次命定的奇遇,十多年前的草原自驾游,因为途中寻找加油站,车子拐进一片茂密的森林,却意外地成就了我与一个小镇的神秘邂逅——眼前的物景令人疑惑,它陈旧的面貌让我想起童年,扶方向盘的手忍不住微微颤抖,我仿佛穿行在梦境之中:低矮的木头屋舍,河边的大风车,清澈喧响的河水,河岸上雪白的羊群,以及大片堆放在路畔散发着清香的松木柴,高高树枝上的鸟巢和盘旋的乌鸦,蜜蜂的嘤嘤声和池塘边的野花;镇口的一座百年古庙还在,屋檐下的狗叫声雨声般淅沥,混杂着慵懒的织机与纺车声……周围的一切包括空气都是静谧的,时间仿佛是一块凝固的巨石,街上的人们迈动着迟缓悠然的步态,面容安详。我的脑海里蹦出一个字:慢。
是的,不知何时,我们的生活与“慢”脱节了,时光风驰电掣般向前奔突,人类进入了疾风暴雨般的后工业时代,体验到短暂的晕眩,或许其中有幸福与快感,但随之而至的却是紧张、忐忑、焦虑、不安、烦恼与失眠——时间被切割,阅读成为碎片化,手机网络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制造的麻烦也前所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多么渴望找到一个绝无污染的精神“乌乡”,让心灵获得片刻的宁静与栖息,缓解一下内心的兵荒马乱,让紧张的神经得到大自然的疗愈,让人类重返童年,捡拾起纯真的树叶与松果,捡拾起跌落地上的星星碎屑,以及消亡已久的“罗曼蒂克”状态与画面。
多年前,米兰·昆德拉曾经在小说《慢》中表述——“慢是幸福的标志”。他还对大地上消逝的事物深表惋惜,发出由衷感慨:“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那一年,我在这个被称作“乌乡”的小镇居住了半月之久,此后又多次光顾。渐渐地,我与那里的人们结下不解之缘,了解到许多掌故传说,镇子周围大片的板栗树、桑葚树和各种中草药植物,各种作坊和种植园,还有我的一位拜把兄弟。通过这位兄弟,我陆续结识了镇上的裁缝、铁匠、木匠、泥瓦匠,巫师、游医、出马仙、算命师、理发师、入殓师,以及民间歌手、鼓手、唢呐手、老猎手、酿酒师、马贩子、牛贩子、驴贩子,油坊主、豆腐坊主、牧羊女,以及潜伏于草丛野地灌木深处的各种生灵野物……于是,多年之后,就有了眼前的“乌乡系列”散文,有了这一本《乌乡薄暮之书》。我写作的目的之一,是除了赞美人性的美德之外,企图写出生灵与生灵之间的差异性,哪怕差异微小,小到一毫米。另外,无论未来的写作如何发展变化,也要让眼睛紧紧盯住人物,盯住人在时代中的坚韧、美善与精神纹路。毫无疑问,乌乡是一个“虚无的实境”,它们寄托了我对生活最朴素的希望与情怀。
最后,说点题外话——最近一次去乌乡是2019年深秋,我惊讶地发现,镇子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是一些令人难以言说的变化,一些古木被伐倒,一些老屋子也拆除了。落叶缤纷,我踩着它们,心里翻滚着无可名状的意绪,像在心脏部位打了一个绳结。
因此,这也是我献给乌乡和大地上消逝事物的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