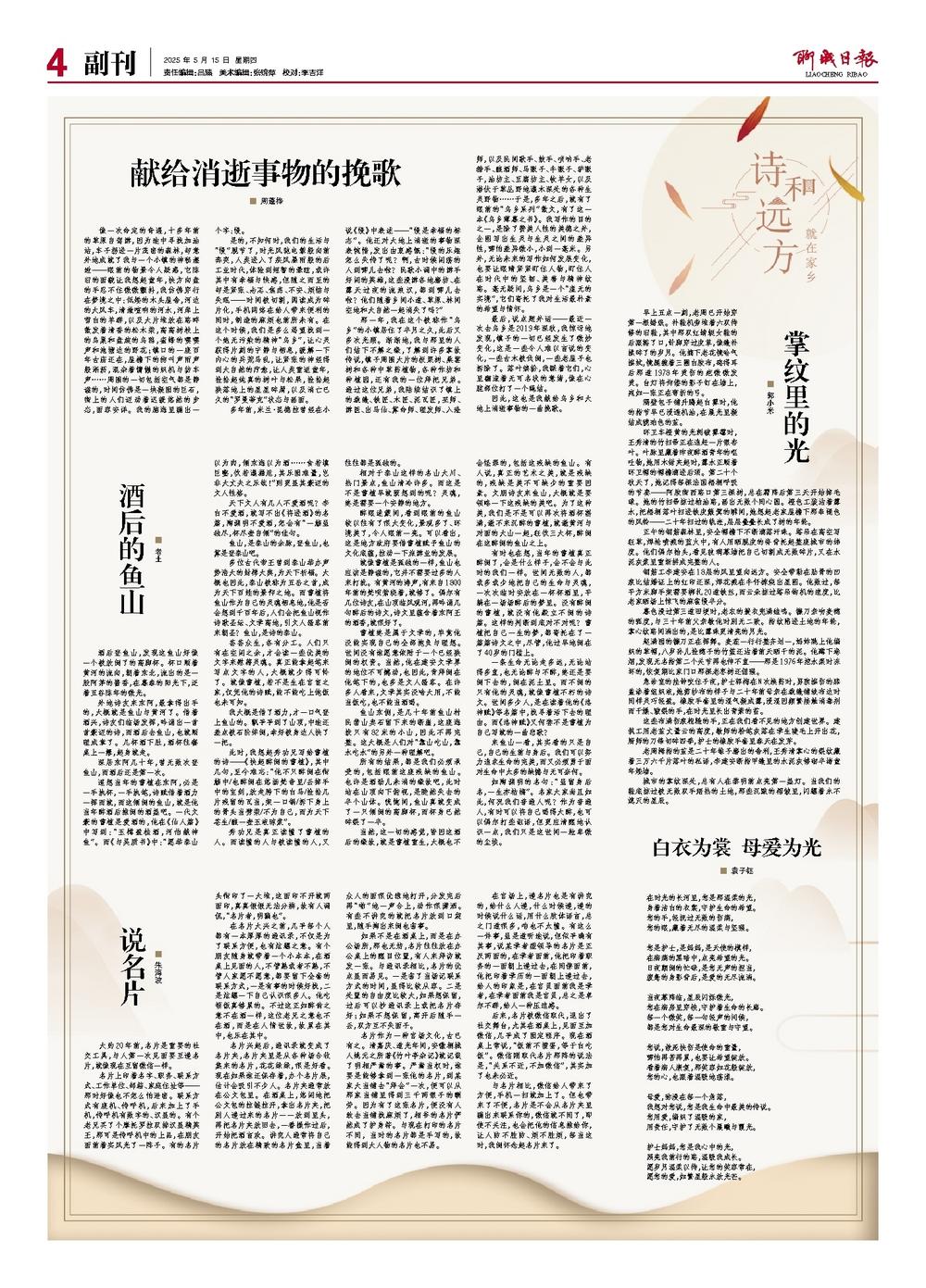说名片
■ 朱海波
大约20年前,名片是重要的社交工具,与人第一次见面要互递名片,就像现在互留微信一样。
名片上印着名字、职务、联系方式、工作单位、邮箱、家庭住址等——那时好像也不怎么怕泄密。联系方式有座机、传呼机,后来加上了手机,传呼机有数字的、汉显的。有个老兄买了个摩托罗拉双排汉显精英王,那可是传呼机中的上品,在朋友面前着实风光了一阵子。有的名片头衔印了一大堆,这面印不开就两面印,真真假假无法分辨,故有人调侃,“名片者,明骗也”。
在名片大兴之前,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厚厚的通讯录,不仅是为了联系方便,也有炫耀之意。有个朋友随身就带着一个小本本,在酒桌上见面的人,不管熟或者不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都要留下全套的联系方式,一是有事的时候好找,二是炫耀一下自己认识很多人。他吃顿饭真够累的。不过这正如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样,这位老兄之意也不在酒,而是在人情世故,故累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名片兴起后,通讯录就变成了名片夹,名片夹里是从各种场合收集来的名片,花花绿绿,很是好看。现在如果谁还保存着,办个名片展,估计会吸引不少人。名片夹通常放在公文包里。在酒桌上,悠闲地把公文包的拉链拉开,拿出名片夹,把别人递过来的名片一一放到里头,再把名片夹放回去,一番操作过后,开始把酒言欢。讲究人通常将自己的名片放在精致的名片盒里,当着众人的面很优雅地打开,分发完后再“啪”地一声合上,动作很潇洒。有些不讲究的就把名片放到口袋里,随手掏出来倒也省事。
如果不是在酒桌上,而是在办公场所,那也无妨,名片往往放在办公桌上的醒目位置,有人来拜访就发一张。与通讯录相比,名片的优点显而易见。一是省了当场记联系方式的时间,显得比较从容。二是处置的自由度比较大,如果想保留,过后可以抄通讯录上或把名片存好;如果不想保留,离开后随手一丢,双方互不失面子。
名片作为一种官场文化,古已有之。清嘉庆、道光年间,安徽桐城人姚元之所著《竹叶亭杂记》就记载了明相严嵩的事。严嵩当权时,谁要是能够拿到一张他的名片,到某家大当铺去“拜会”一次,便可以从那家当铺里得到三千两银子的酬劳。因为有了这张名片,便没有人敢去当铺找麻烦了,相爷的名片俨然成了护身符。与现在打印的名片不同, 当时的名片都是手写的,故能得到大人物的名片也不易。
在官场上,递名片也是有讲究的,给什么人递,什么时候递,递的时候说什么话,用什么肢体语言,总之门道很多,咱也不太懂。有这么一件事,虽是道听途说,但似乎确有其事,说某学者型领导的名片是正反两面的,在学者面前,他把印着职务的一面朝上递过去,在同僚面前,他把印着学历的一面朝上递过去,给人的印象是,在官员面前我是学者,在学者面前我是官员,总之是卓尔不群,给人一种压迫感。
后来,名片被微信取代,退出了社交舞台,尤其在酒桌上,见面互加微信,几乎成了固定程序。现在酒桌上常说,“饭前不掼蛋,等于白吃饭”。微信刚取代名片那阵的说法是,“关系不近,不加微信”,其实加了也未必近。
与名片相比,微信给人带来了方便,手机一扫就加上了。但也带来了不便,名片是不会从名片夹里蹦出来联系你的,微信就不同了,即使不关注,也会把他的信息推给你,让人防不胜防、烦不胜烦,每当这时,我倒怀念起名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