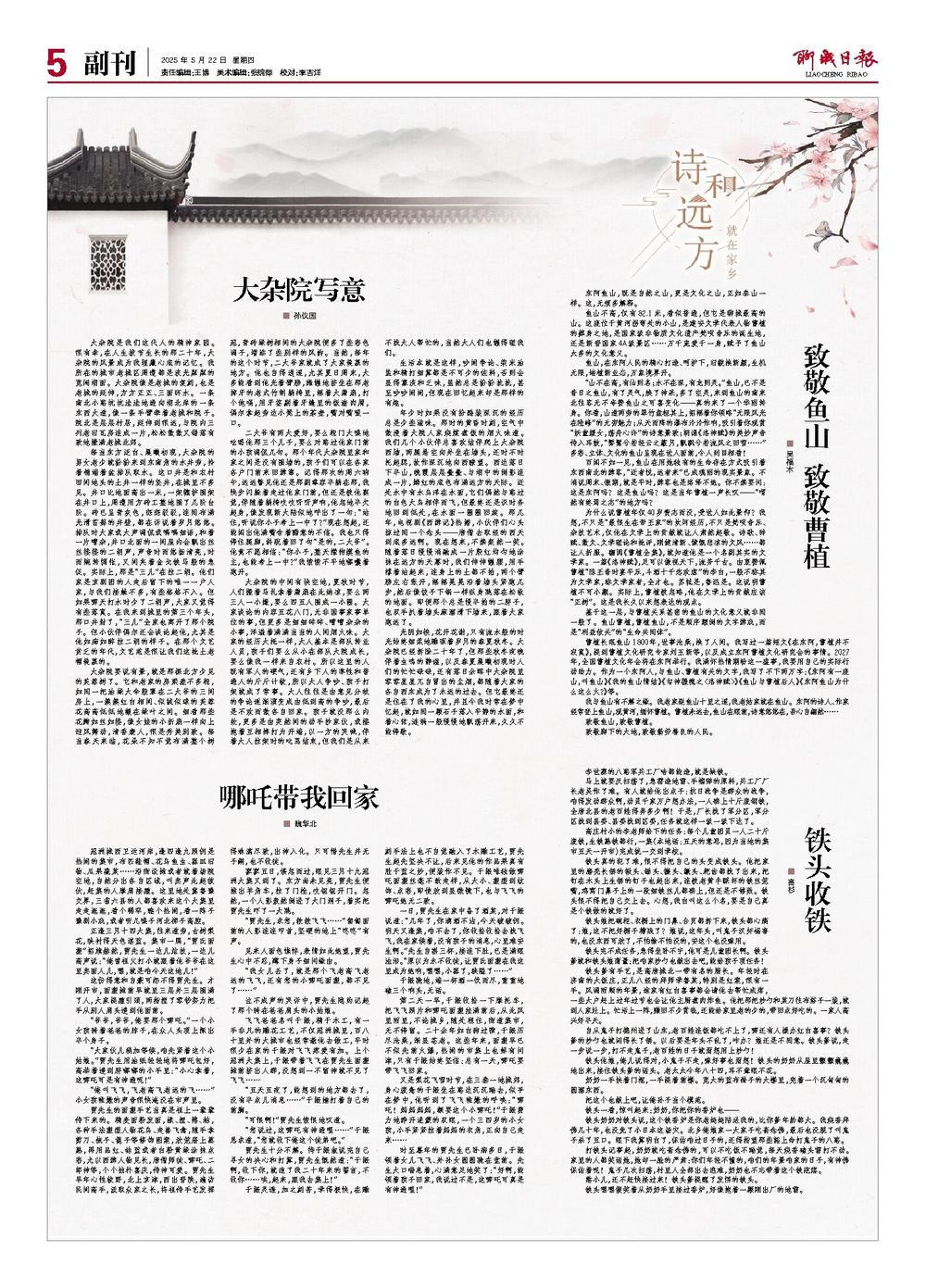哪吒带我回家
■ 魏华北
冠洲城西卫运河岸,逢四逢九照例是热闹的集市,布匹鞋帽、花鸟鱼虫、器皿旧物、瓜果蔬菜……沿街设摊或者就着场院空地,自然分出各自区域,叫卖声此起彼伏,赶集的人摩肩接踵。这里地处冀鲁豫交界,三省六县的人都喜欢来这个大集里走走逛逛,看个稀罕,瞧个热闹,看一阵子豫剧小戏,或者听几嗓子河北梆子高腔。
正逢三月十四大集,往来道旁,古树梨花,映衬得天色湛蓝。集市一隅,“贾氏面塑”招旗赫然,贾先生一边儿炫技,一边儿高声说:“俺曾祖父打小就跟着他爷爷在这里卖面人儿,嘿,就是咱今天这地儿!”
这份得意和自豪可怨不得贾先生。才刚开市,面塑摊前早就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大家提踵引颈,两指捏了零钞努力把手从别人肩头递到他面前。
“爷爷,爷爷,俺要那个哪吒。”一个小女孩骑着爸爸的脖子,在众人头顶上探出半个身子。
“大家伙儿稍加等候,咱先紧着这个小姑娘。”贾先生用油纸轻轻地将哪吒包好,高举着递到胖嘟嘟的小手里:“小心拿着,这哪吒可是有神通呢!”
“俺叫飞飞,飞老高飞老远的飞……”小女孩稚嫩的声音很快淹没在市声里。
贾先生的面塑手艺当真是祖上一辈辈传下来的。精麦面粉发面,揉、捏、搏、粘,各种手法塑型人物花鸟、走兽飞禽,随手拿剪刀、梳子、篦子等修饰图案,放笼屉上蒸熟,再用品红、钴蓝或者白粉黄绿涂抹点彩,尤以西游人物见长,唐僧师徒、哪吒、二郎神等,个个拙朴喜庆,传神可爱。贾先生早年心性较野,北上京津,西出晋陕,遍访民间高手,汲取众家之长,将祖传手艺发挥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只可惜先生并无子嗣,也不收徒。
寥寥五日,倏忽而过,眼见三月十九冠洲大集又到了。东方尚未见亮,贾先生便推出羊角车,拉了门栓,吱钮钮开门。忽然,一个人影轰然倒进了大门洞子,着实把贾先生吓了一大跳。
“贾先生,求您,救救飞飞……”匍匐面前的人影连连叩首,坚硬的地上“咚咚”有声。
见来人面色憔悴,表情如此绝望,贾先生心中不忍,蹲下身子细问缘由。
“我女儿丢了,就是那个飞老高飞老远的飞飞,还有您的小哪吒面塑,都不见了……”
泣不成声的哭诉中,贾先生隐约记起了那个骑在爸爸肩头的小姑娘。
飞飞爸爸名叫于振,精于木工,有一手非凡的雕花工艺,不仅冠洲城里,百八十里外的大城市也经常邀他去做工,平时很少在家的于振对飞飞疼爱有加。上个冠洲大集上,于振带着飞飞在贾先生面塑摊前挤出人群,没想到一不留神就不见了飞飞……
“五天五夜了,能想到的地方都去了,没有半点儿消息……”于振捶打着自己的前胸。
“可恨啊!”贾先生愤恨地叹道。
“您说过,这哪吒有神通哩……”于振恳求道,“您就收下俺这个徒弟吧。”
贾先生十分不解。待于振叙说完自己寻女的决心和打算,贾先生慨然道:“于振啊,收下你,就违了我二十年来的誓言,不收你……唉,起来,跟我去集上!”
于振灵透,加之刻苦,学得极快,在雕刻手法上也不自觉融入了木雕工艺,贾先生起先坚决不让,后来见他的作品果真有胜于蓝之妙,便装作不见。于振唯独做哪吒面塑丝毫不敢走样,从大小、塑型到纹饰、点彩,即使放到显微镜下,也与飞飞的哪吒绝无二致。
一日,贾先生在家中备了酒菜,对于振说道:“几年了,你滴酒不沾,今天破破例。明天又逢集,咱不去了,你收拾收拾去找飞飞,我在家候着,没有孩子的消息,心里难安生啊。”先生自斟三杯,接连下肚,已是满眼浊泪。“原以为永不收徒,让贾氏面塑在我这里成为绝响,嘿嘿,小器了,狭隘了……”
于振跪地,端一杯酒一饮而尽,重重地磕三个响头,无话。
第二天一早,于振收拾一下摩托车,把飞飞照片和哪吒面塑挂满前后,从此风里雨里,不论城乡,随处租住,街道集市,无不停留。二十余年如白驹过隙,于振历尽沧桑,渐显苍老。这些年来,面塑早已不似先前火爆,热闹的市集上也鲜有问津,只有于振始终坚信:总有一天,哪吒要带飞飞回家。
又是梨花飞雪时节,在三秦一地城郊,身心疲惫的于振坐在路边沉沉睡去,似乎在梦中,他听到了飞飞稚嫩的呼唤:“哪吒!妈妈妈妈,额要这个小哪吒!”于振费力地睁开迷蒙的双眼,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小手紧紧拉着妈妈的衣角,正向自己走来……
时至暮年的贾先生已卧病多日,于振领着女儿飞飞、外孙女圆圆跪在堂前。先生大口喘息着,心满意足地笑了:“好啊,能领着孩子回家,我说过不是,这哪吒可真是有神通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