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分情结
◇ 高明久
初中毕业那年,我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驮起被子回到了家乡,脱下学生装,开始下地干活。
父亲告诉我,家后小坑边槐树上的钟声一响就要上工,在那里听队长派活。
第一天的劳动过去了。吃完晚饭,我正想坐下看书,父亲递给我一个小本:“这是记工本,一会得去草屋(生产队的牛棚)记工分。”
乡亲们都在草屋等记工员记工。轮到我了,记工员广玉见我第一次记工,便对我说:“三叔(广玉小我一辈,我在兄弟间排行老三),我给你说说记工的原则。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分整劳力和半劳力,男的18—60岁、女的18—45岁为整劳力,小孩、老人和残疾人是半劳力。整劳力一天记一个工,早晨2分,上午、下午各4分。半劳力减半记。”
我看了看,记工本上有年、月、日,早晨、上午、下午,劳动内容摘要,记工员盖章。
有一天,我和广玉合打畦田,聊起了工分的事。“工分是你的劳动报酬,是粮食分配、秋后算账、年终决算的依据。”广玉说,但我懵懵懂懂。
麦收后,家家户户都带着布袋去场里分粮食。队长四叔先组织有眼力的人估量斤数,然后把百分之七十按人头分下去,百分之三十放进仓库里待秋后算账时找补。
秋后算账,有“人七劳三”和“人六劳四”两种分配方案。至于按照哪个方案执行,生产队里召开群众大会征求意见。由于每家的人口组成、年龄大小、劳力多少不同,就出现了余粮户和缺粮户,队员年年围绕两种分配方案争执不休。劳力多的余粮户愿意采用“人六劳四”分配,缺粮户则赞成“人七劳三”。吵归吵,争归争,最后还是由队长决定。我在家的几年里,四叔多数定的是“人七劳三”。
年终决算,就是把分得的粮食按国家规定的平价价格计算出金额。会计汇总各家各户的工分,每个工按一毛钱工值,计算出每家的工分总值,工分总值减去分得粮食的钱额,就出现了余粮户和缺粮户。余粮户分钱,缺粮户交钱。那些“一头沉”的户(即在外工作的干部、工人、教师,只有家属、孩子或者父母在家的),可以拿钱买工分。
我慢慢明白了“工分工分,老农民的命根”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因为工分直接决定着各家的粮食分配、各户的贫富程度以及各户的幸福指数。
为了挣工分,上午放了工后,我就挎着篮子去割草,再把草交给队里喂牛,以草换工分。碰上草多的时候,一个中午能挣整劳力一上午的工分。在冬天,我就和广勤看仓库,睡在半阴半阳的窝棚里。麦收时节的晚上,我就和二堂、清瑞、广勤去看场,以此来弥补我家工分不足的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那段挣工分的岁月,我至今难以忘怀。割草的草友、看仓库的伙伴、打畦田的小伙计,也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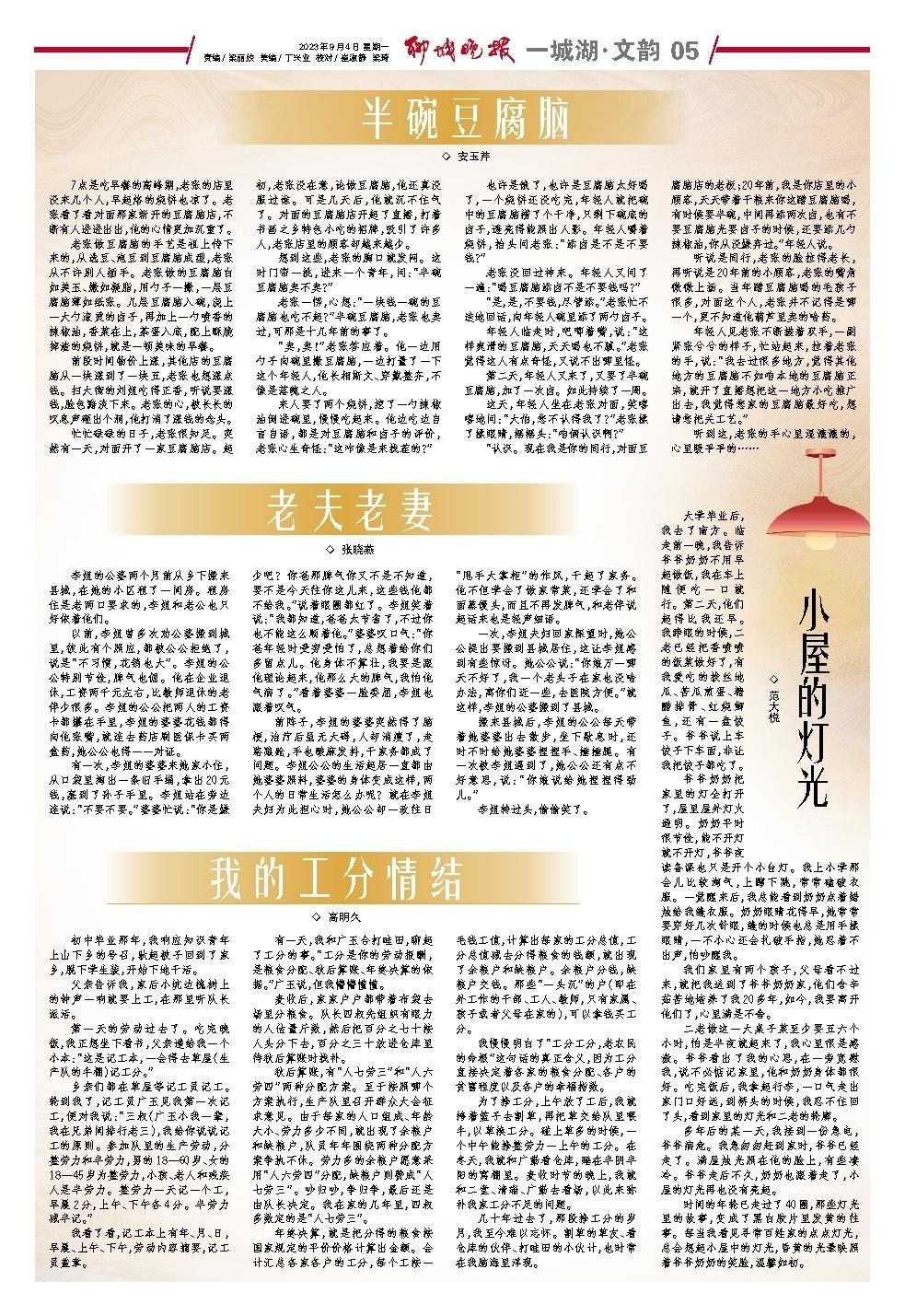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